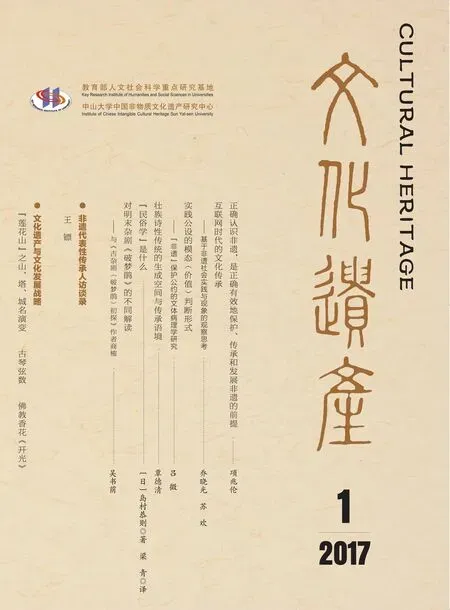“琴棋書畫雜考”之二
——古琴弦數考略
黎國韜 周佩文
?
“琴棋書畫雜考”之二
——古琴弦數考略
黎國韜 周佩文
琴是中國古代流傳最為廣泛的樂器之一,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文物資料,中國歷史上至少出現過“無弦、一弦、兩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十弦、十二弦、十三弦、十五弦、二十弦、二十五弦、二十七弦”等十四種弦數的古琴形制,其中又以五弦琴制和七弦琴制流行較廣。特別是七弦琴,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使用的普遍性上雖略遜五弦琴一籌,但到了唐代,古琴演奏便完全成為七弦琴的天下,并一直影響、沿用至今。眾多古琴弦制的存在,使我們從一個側面認識到古琴發展歷史的復雜性,對于糾正過往音樂史研究中的一些偏失亦有一定幫助。
古琴 琴弦 弦數 五弦琴 七弦琴
琴是中國古代流傳最為廣泛的樂器之一。漢魏以來,琴、棋、書、畫“四藝”逐漸成為中國士人修身養性的重要途徑,而琴更居首位焉。①案,將琴、棋、書、畫四藝并稱,大約始于唐人。如開元年間何延之的《蘭亭始末記》稱:“[釋]辯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奕[弈]書畫,皆臻其妙。”(見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三百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2頁)但實際上,南朝時期這四藝已經成為士人們普遍喜愛和修習的對象。因此,它無疑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對象。在歷史上,人們習稱古琴為“七弦”,②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清人車萬育的《聲律啟蒙》寫到:“塵慮縈心,懶撫七弦綠綺;霜華滿鬢,羞看百煉青銅。”(岳麓書社2002年,第2頁)所謂“綠弦”,據說就是漢代卓文君所用琴的名字。這是因為用于演奏的古琴多數安裝有七條琴弦。③案,古代的琴弦一般是絲弦,近代往往用鋼絲尼龍弦,因溢出本文討論主題,不贅。然而,七弦琴制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才逐漸確立的;在此之前,琴弦的數量存在著多種形制;在此之后,用七弦以外弦數演奏的古琴亦偶見記載。可惜對于這類較為特殊的音樂文化現象,歷來關注者甚少,④案,宋人陳旸的《樂書》(卷一百十九、一百二十)雖曾列出幾種不同弦數的古琴,但尚不完備,敘述亦有失誤,所以這類問題的研究空間還比較大。對其作出專文研究者更幾乎沒有,這無疑大大影響了人們對古琴歷史發展真相的了解。有鑒于此,筆者擬用搜集到的文獻史料和文物史料作為基本依據,對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古琴弦制一一展開考述,進而分析七弦琴制出現和確立的具體時間,以祈有所補闕,也希望能為古琴史、音樂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點幫助。
一、少于七弦之制
在古代,有不少琴所安弦數是少于七條的,甚至出現過一條弦也沒有的“無弦琴”,比如《宋書·隱逸傳》記載:
(陶)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沈約:《宋書》卷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88頁。
對此,《晉書·陶潛傳》也有相近記載:“(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房玄齡等:《晉書》卷九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63頁。所謂“素琴”,當指沒有髹漆、沒有紋飾之琴;所謂“不具弦徽”,也就是既未標識出琴徽,*案,琴徽是琴面上的圓形標志,據繆天瑞先生等主編《中國音樂詞典》“琴徽”條介紹:“琴徽:琴弦音位標志,又稱徽或暉。在琴面鑲嵌有十三個圓形標志,以金、玉或貝等制成。其位置根據弦長的整數比,即發出泛音的地方,從琴頭開始,依次為第一徽、第二徽……直至琴尾的第十三徽。……琴徽是琴曲演奏藝術高度發展的產物,有了琴徽不僅便于奏出泛音(泛音是以左手輕觸徽位,發出輕盈虛飄的樂音),同時也便于根據徽位及其間的‘徽分’(相鄰兩徽間均分為十等份,稱徽分),在琴譜中寫出音位的高低變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第307頁)可作參考。也未安裝好琴弦;正因為“無弦”,所以有“何勞弦上聲”之說。如所周知,東晉田園詩人陶潛(字淵明)喜歡以琴書自娛,其《答龐參軍》詩就寫道:“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頁。其《歸去來兮辭》又寫道:“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卷五,第391頁。俱可為證。至于為什么只蓄一張無弦無徽的素琴,或與陶淵明黜落浮華、得趣忘聲的審美思想有關。*案,可參見李萬堡先生《“無弦琴”的哲學解構》一文(《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3期)所述,不贅。
如果琴面上僅僅安裝一條琴弦,那么就可以稱之為“一弦琴”,這也是古代曾經有過的形制,據《晉書·隱逸傳》記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房玄齡等:《晉書》卷九十四,第2426頁。
孫登是三國、西晉時期“隱士琴”的代表人物,約與阮籍、嵇康等同時。從上引的記載來看,古代確實出現過一弦琴,時間比無弦琴略早,它與無弦琴最大的區別在于可以用于實際演奏,比如宋人朱長文的《琴史》記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有道而隱者也。好讀《易》、鼓琴,性無恚怒。阮嗣宗、嵇叔夜嘗從之游。……叔夜善彈琴,至見登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乃嘆服。*朱長文:《琴史》卷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83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2-33頁。案,朱長文雖為趙宋時人,但他出身于宮廷琴待詔世家,《琴史》所錄的琴家材料多典核有據。
由此可見,一弦琴可以用于實際演奏。另據《藝文類聚》引《馬明生別傳》稱:“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幾,彈琴有一弦,五音并奏。”*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2頁。這固然只是一則仙話,但也是一弦琴可用于演奏的曲折反映。*案,《新唐書·南蠻下》記載:“(驃國樂)有獨弦匏琴,以班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弦無軫,以弦系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弦應太蔟。”(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313頁)匏琴的形制固然與古琴有較大區別,卻可說明系一弦便可用于演奏。近代琴曲演奏名家顧梅羹先生在其《琴學備要》第二篇《指法》一章一節《一弦單彈指法譜字》還指出:“右手彈弦以大、食、中、名為用,只有小指禁而不用。……彈入的名稱曰‘擘、抹、勾、打’,彈出的名稱曰‘托、挑、剔、摘’,這八法又因單彈一弦、雙彈兩弦、連彈數弦的用處各有不同,所以又有‘涓、輪、鎖、鼓、潑剌、滾拂、索鈴、打圓’種種辨別。”*顧梅羹:《琴學備要》上冊,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頁。既然“單彈一弦”便有八種指法,則古人用一條琴弦彈出簡單的曲調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案,到北宋后期,祭祀儀式中還安排過多具一弦琴的演奏,亦為明證,詳下文所述。
如果琴面上安裝兩條琴弦,那么就可以稱之為“兩弦琴”,這種琴制出現的時代較晚,據宋人陳旸《樂書》及《宋史·樂志》分別記載:
圣朝初制兩儀琴,琴有二弦,弦各六柱,合為十二,其聲洪迅而莊重,亦一時之制也。*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09頁。
(仁宗景祐)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器。*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54頁。
由此可見,兩弦琴又稱為“兩儀琴”,特點是演奏時聲音“洪迅而莊重”,往往用于雅樂的演奏,其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北宋仁宗景祐年間。《樂書》在文字記載之前還畫出了兩弦琴的具體圖像,琴面上清晰顯示出十一個徽位,這與普通七弦古琴的十三徽位有所不同。圖上又有小字注云:“二弦,每弦各有六柱。”這種弦下設柱的做法就更為特別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傳統古琴基本上都是有弦無柱的,但另一種重要弦樂器“瑟”則每弦下面均設柱以承托之。由此推測,兩儀琴當是吸取了琴、瑟兩種形制而創成的。上引《樂書》說它“亦一時之制也”,可見這種琴制主要流行于宋代,后人用之、知之者甚少。
比兩弦琴多一條弦的就是“三弦琴”,這種形制的古琴大約從北宋后期才開始出現,比兩弦琴出現的時間更晚,據《宋史·樂志四》記載:
(大觀四年)八月,帝親制《大晟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為八論:……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魏)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圣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九,第3003-3010頁。
(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植建鼓、鞞鼓、應鼓于四隅,……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并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并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二十九,第3013-3014頁。
由此可見,北宋皇帝親自祭祀宗廟、太社、太稷時須登歌奏樂,所用的樂器中就有“三弦琴”,共一十八張。由于大觀、政和都是北宋晚期徽宗的年號,劉昺、魏漢津則為“大晟樂”的主要倡儀者,所以三弦琴的出現當與北宋后期大晟府的建立有密切聯系。此外,三弦琴與一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等并列共用,所以肯定是橫置幾上或斜置膝上演奏的古琴,而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民族彈撥樂器“三弦”,后者形似直項琵琶,古人又稱之為“弦子”或“弦鼗”,切切不可混淆。從古籍記載來看,除宋代以外也極少有人使用三弦古琴演奏,所以知之者亦不多。
四弦的古琴未見文獻記載,但有一件銅鏡文物的圖像疑與此器有關。鏡為東漢后期物,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區有銘文,《故宮銅鏡圖典》一書釋為:
呂氏作鏡流信德,刻畫□□□□ □□留除治熟,青龍白虎相紋錯,東公西母仙侍藥,朱鳥玄武□旁側,昌女□□□□琴,□□里具雨后伏,明□□ □□宜文章□□□□□□□□□□□。*丁孟主編:《故宮銅鏡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89頁;原文標點有誤,徑改。
若依此釋文,則銅鏡上區所鑄圖像中刻畫一人所鼓的樂器即為“琴”,此“琴”面上正鑄為四條弦式,似為目前僅見的“四弦琴”之制。不過,鏡銘中上“玨”下“乂”的字若釋為“琴”,則有三個疑問:其一,古“琴”字有作上“玨”下“人”、上“玨”下“∧”者,卻未見下作“乂”者。其二,若釋為“琴”字,則與其前后的“德、熟、錯、藥、側、伏”諸字不能押韻,有違漢代鏡銘押韻的習慣。其三,漢代銅鏡中常見“伯牙鼓琴”的圖像,所鼓之琴不般不刻畫琴弦,形制也與本鏡的“琴”存在較大差異。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此字當釋為“瑟”,這樣一來,不但可與前后諸句的末字押韻,且銘文提到的“昌女鼓瑟”亦與“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的傳說相合。*司馬遷撰、三家注:《史記》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96頁。退一步講,即使銅鏡圖像上的樂器確實為琴而非瑟,也不排除鑄工刻畫與實際用器弦數存在差異的可能,因為畫像往往表達意義即可,未必完全求實。約而言之,古代是否出現過四弦琴制仍當存疑俟考。
四弦琴雖不見確切記錄,五弦琴則出現很早,而且一度十分流行。據《禮記·樂記》稱:“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卷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95頁。這當然有傳說附會的嫌疑,且《樂記》成書的年代也眾說紛紜、未可遽定,但《禮記》的成書在石渠閣會議之前(前51年),*據《漢書·儒林傳》載:“(戴)圣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參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八十八,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615頁)所以五弦琴的出現不會晚于此時,比起無弦、一弦、兩弦、三弦來說都要早得多。另據《史記·樂書》記載:
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司馬遷撰、三家注:《史記》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236-1237頁。
太史公在論及古琴時只提到宮、商、角、徵、羽五音,所以應是就五弦之琴而言,這說明至遲西漢武帝時期已有這種琴制存在了。至于《爾雅·釋樂》稱:“大琴謂之離。”郭注引《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五弦。”*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頁。《廣雅》的成書是三國時期,這也佐證了五弦琴出現之早。*案,近代出土的上古至西漢古琴中,尚沒有發現五弦琴。至于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曾出土的一件“五弦器”,過去一度被稱為“五弦琴”,但據學者研究指出,這件“五弦器”實為“均鐘”,是一種為編鐘調律的音高標準器,所以也不是五弦琴(參見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頁)。關于此器,尚有為筑、為箏等說法,不贅。在中國古琴發展史上,五弦琴是除七弦琴外流行最廣的一種琴制,在某些時代,其影響力甚至更在七弦琴之上,所以特別值得注意。有關問題下文尚有言及,茲不贅。
二、多于七弦之制
以上談到的無弦琴、一弦琴、兩弦琴、三弦琴、五弦琴都少于七弦,接下來探討一下多于七弦的琴制。
首先看九弦琴,據《古今注》稱:“后漢蔡邕益琴為九弦,后還用七弦。”*崔豹:《古今注》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頁。《古今注》類似小說家言,又沒有其他較為可靠的旁證,所以只能暫時存疑。但到了北宋,則明確出現了九弦琴制,有陳旸《樂書》所載為證:
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為散操;東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雅琴之制自漢始也。圣朝太宗皇帝因太樂雅琴更加二弦,召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弦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制《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來燕樂半字譜。……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弦去四清聲,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07-508頁。
由此可見,北宋太宗在古代七弦“雅琴”的基礎上增加了兩條弦,于是“應時而造”出了九弦琴。另據《宋史·樂志》記載:
姜夔《樂議》分琴為三準:……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轉弦合調圖。……
《九弦琴圖說》曰:“弦有七、有九,實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為散聲也。”*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第3342-3343頁。
由此可見,南宋詞學名家姜夔對于九弦琴也有所研究,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該琴制在兩宋時期是比較流行的。須要稍作澄清的是,近人章華英先生《古琴》一書提到過四件出土的古琴實物(制作時間為春秋至西漢時期),并將1980年湖南長沙五里牌戰國楚墓出土的那一件“暫名”為“九弦琴”,*章華英:《古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頁。這一說法似乎值得商榷。音樂考古學家李純一先生早就指出過,長沙市五里牌出土的這張古琴,其龍齦和雁足上有弦勒痕跡,所以是實用樂器;但從龍齦上九道不明顯的弦痕來看,它有可能為九弦,也有可能略多于九弦,或略少于九弦,但不會是五弦。*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頁。因此,五里牌楚墓出土古琴的弦數目前還不能確定,所以北宋之前是否真的出現過九弦琴,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其次看十弦琴,這種形制在古代文獻史料和近代考古實物中都可找到。比如宋人陳旸的《樂書》就提到這種古琴:
蓋五弦之琴,小琴之制也;兩倍之而為十弦,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弦,大琴之制也。*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06頁。
由此可見,古人曾將五弦琴稱為“小琴”,十弦琴稱為“中琴”,二十弦琴則稱為“大琴”。另外,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張古琴也是十弦琴,音樂考古學家李純一先生曾論及此琴云:“從上古至西漢的出土古琴形制來看,卻與桓譚所述頗不相符。比如湖北隨縣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為實用樂器,琴面靠近琴額處橫設扇形岳山,沿岳山外側鉆有一排十個弦孔,直通軫池,所以這是一張十弦琴。”*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第448頁。這張十弦琴也是目前存世的所有古琴當中最為古老的一張。除曾侯乙墓外,廣州西漢南越王墓葬之中可能也有十弦琴,張榮芳、黃淼章二先生所撰《南越國史》曾指出:“南越的琴曲如何,目前尚缺乏資料,南越古琴則見于廣州的南越王墓東耳室中,出土時琴的木胎已朽,僅有銅琴軫37個,發掘報告的編寫者根據出土情況,認為應有‘七弦琴’一件及‘至少十弦琴三件或五弦琴六件’,這個結論是對的。”*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頁。可惜因為木質的朽壞,已經很難復原,所以這三十七個琴軫到底該如何分配就不得而知了。
再次看十二弦琴,前引《宋史·樂志》已提到,十二弦琴和兩弦琴一樣,在北宋仁宗景祐年間才開始出現。另據宋人陳旸《樂書》記載:“圣朝嘗為十二弦琴,應十有二律,倍、應之聲靡不悉備,蓋亦不失先王制作之實也。然古人造曲之意,感物以形于聲,因一聲而動于物。伯牙《流水》之奏,士野《清徵》之音,夫心往形留,聲和意適,德幽而調逸,神契而感通,則古人之意明矣。”*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08頁。俱可證十二弦琴是北宋時期新出現的琴制。而《樂書》在文字記載之前同樣畫出了十二弦琴的圖像,琴面上只有十個徽位,比兩儀琴少一個,比七弦琴少三個,也是甚為特殊的。
再次看十三弦琴,據陳旸《樂書》記載:“至于弦數,先儒謂伏犠、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全之為二十七,半之為十三,皆出于七弦倍差,溺于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10頁。既稱“先儒”,可見在陳旸之前便已有十三弦的“頌琴”。在《樂書》卷一百四十一《樂圖論》中畫有兩把十三弦琴,圖上有小字注云:“十三弦,柱如筍。”圖后又有云:
古之善琴者八十余家,各因其器而名之,頌琴居其一焉。其弦十有三,其形象箏,移柱應律,宮懸用之合頌聲也。*陳旸:《樂書》卷一百四十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647頁。
由此可見,十三弦頌琴可能是吸取了古箏設柱之形制而新創出來的,但它肯定不能等同于箏,否則陳旸不會說“其形象箏”;而從《樂書》所繪頌琴的樣式來看,其外貌也近琴而與箏差異較大。另據《舊五代史·樂志》記載:
周顯德五年,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于殿庭。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設而不擊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世宗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詳其制,又命樞密使王樸考正其聲。樸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準。其狀如琴而巨,凡設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為宮之義。*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923-1924頁。
后周顯德年間,樞密使王樸曾用“累黍之法”,造出十三弦律準以厘定樂律,這在古代音樂史上是一件很有影響的事情。但這件律準所定的樂律明顯與古樂不符,所以在宋仁宗景祐二年二月,集賢校理李照就指出:“樸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樸創意造律,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第2948頁。由此引發了北宋時期多次律制的改革。不過,從“其狀如琴而巨”這句記載來看,王樸的律準有可能是模仿十三弦頌琴之制創造出來的,所以頌琴的出現或在五代以前。*案,《西京雜記》曾提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劉歆撰、葛洪輯《西京雜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頁)當然,這屬于小說家言,漢高祖劉邦的時候還沒出現琴徽,但劉歆或葛洪的時代或者出現過十三弦琴,俟考。
至此還須提及20世紀70年代后期江西貴溪仙水巖崖墓出土的兩件古越族撥弦樂器,它們一度也被認為是“十三弦琴”。*如吳釗、劉東升編著《中國音樂史略》(廣州: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版)圖版14,就將其中一件定名為“越十三弦琴”。但音樂考古學家王子初先生卻認為:“從貴溪出土的這兩件木質樂器的面板上無徽而且是13弦看,非琴是明顯的;瑟雖不見徽位,也一弦一柱,但通常都是25弦,所以貴溪出土的樂器也不是瑟;……貴溪出土的樂器13弦并帶柱,應是13弦箏。據貴溪縣文管所的工作人員介紹,他們曾在貴溪崖墓中采集到1件箏的‘碼子’,也即箏的柱了。……它是否就是這兩件古箏上散落下來的柱,尚需進一步研究。”*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第242-243頁。王氏所言不無道理,但他根據“沒有徽”和“十三弦”而判斷這兩件樂器“非琴”,則不夠準確:一則琴徽的出現時間很晚,早期古琴沒有徽是很正常的現象,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就沒有徽;二則史料表明,古代也存在過十三弦的頌琴,不能單純依據弦數多少來判斷某件樂器是琴還是箏。總之,貴溪出土的這兩件樂器的性質還須深入研究再下定論。*案,十三弦琴出現的具體時間暫難考定,但考慮到“全之為二十七,半之為十三”,所以其出現當在二十七弦大琴之后,二十七弦之制詳下文所述,不贅。
再次看十五弦琴。據宋人陳旸《樂書》記載:“古者大琴二十弦,次者十五弦,其弦雖多少不同,要之本于五聲一也。蓋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07頁。《樂書》既說“古者”而不稱“圣朝”,則十五弦之制理應出現在北宋以前,但具體時間尚待考證,也未見考古出土實物。此外,《樂書》畫出了十五弦琴的圖像,并直稱之為“次大琴”,琴面上有十三個徽位,與五弦琴、七弦琴無異,可見宋人仍在使用。至于柳世隆(442-491)則為南朝人,仕齊位至司空,據《南齊書·柳世隆傳》記載:“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52頁。但他與十五弦琴的出現有什么聯系,則無從考證。
再次看二十弦琴。前引《樂書》曾提到:“蓋五弦之琴,小琴之制也;兩倍之而為十弦,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弦,大琴之制也。”可見當時有稱二十弦琴為“大琴”者。陳氏接著又說:“《明堂位》曰:‘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以四代推之,二琴之制始于有虞氏明矣。”*陳旸:《樂書》卷一百十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211冊,第506頁。則二十弦大琴的出現即使不在虞舜時代,似乎也不會晚于《禮記》或《爾雅》的成書的年代。但郭璞注《爾雅》時明明說:“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五,第155頁。由此可見,陳旸所說的二十弦大琴與古代的二十七弦大琴在弦制上并不吻合,所以有可能仍是宋人新弄出來的形制。
再次看二十五弦琴,這種琴制出現最晚,而且不見于中國古籍記載,倒是在日本曾有流傳。據日本音樂史家林謙三先生《東亞樂器考》稱:
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西都(京都)游里祇園街有歌妓叫千賀,從長崎上京來的客人得到傳授,懂得二十五弦的奏法;嗣后攜此樂器侍酒席彈奏,一時流行于風流好事的人士之間。……《琴學獨稽古》學記有這一段奇緣的文字。與書中所圖的二十五弦一樣的樂器,時常在千賀流傳嬌名的京都,出現于古物肆及其他人家。我家就藏有二張大同小異的,其一長96厘米,另一長95.5厘米,俱是桐制的。弦是第一弦最長,第二弦以下每二條同長,而以次遞短。因之,第一弦之外每二弦調為同音,二十五弦的效果同十三弦。其調律的方法,是把10厘米長的轉子插在并列于槽側面(磯)的軫端來松緊弦。……然而二十五弦,在樂器學上可以叫做琴而不能叫做瑟。瑟是和箏一樣,用柱來支弦的,二十五弦沒有柱,這一點倒還近于琴。……恐系來住在長崎的清朝客人所傳播的樂器,不知今日中國尚有這樂器的原型存在與否。……而二十五弦是清朝人折衷各種樂器而造成的,幾乎沒有可以置疑的余地。*林謙三著、錢稻孫譯:《東亞樂器考》,廣州:人民音樂出版社1962年,第153-156頁。
林謙三的敘述非常具體,而且在《東亞樂器考》中錄有《琴學獨稽古》所刊的“二十五弦琴圖”,可見日本江戶時代后期確實流行過這種琴制。林謙三還提到他家中所藏的兩張二十五弦琴,琴長95.5-96厘米,約當漢尺4尺有余,約當宋尺3尺有余。琴的弦數雖多,但不用柱而用軫,故林氏認為應稱琴而非瑟,這也很正確。其獨特之處在于,一般古琴用以調弦的軫是位于琴面板底下,而二十五弦琴則位于琴身側面;林氏認為這種做法借鑒了中國古代帶側軫的箏的形制,其說可通。此外,林氏認定這種琴制乃從清朝傳入日本,筆者亦表示贊同,問題是為什么中國古籍之中沒有記載過這種琴制呢?筆者的推測是,二十五弦可能是清代民間樂人根據古琴、古箏形制而新創的,因沒有得到上層文士的認可,也僅限于民間小范圍流傳,所以就默默無聞了。
至此還須提及20世紀30年代長沙東門外戰國晚期楚墓出土的一張“楚瑟”,商承祚先生《長沙古物聞見記》對此有詳細記錄: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東門外楚墓,作長扁匣形,與《三禮圖》所繪者近似。……版當日扣入瑟底,器干收縮不能復合。中岳弦孔七,兩旁(岳)各九,共二十五弦,岳面弦痕明顯可辨,中弦粗,兩旁弦細,尾里孔尚附弦緒十之八。結后以牛角丁橫貫之,外引至岳,穿入首孔,分作四組,由端際上繞,再納入四方孔,然后用木枘之,余緒下垂,容于版孔。調弦之緩急,則以柱承弦,可以移易。*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續記》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4-67頁。
由此可見,這是一張二十五弦的古瑟。*案,有的書著錄此瑟為二十三弦,疑誤。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琴學名家查阜西先生于北京目睹此器后,卻根據“宣聲”指法在“楚瑟”面板上留下的指痕判斷,*案,宣聲是指用手指按撥琴弦,使弦與琴面接觸并發出聲響,所以指痕得以保留在琴面上;而瑟弦下面有柱承托,按壓瑟弦時不與瑟的面板接觸,所以一般不會留下指痕。這張二十五弦的樂器應為古琴而非古瑟,其說不無道理。*案,有關查氏判斷這件“楚瑟”為琴的過程及相關細節,參見謝孝蘋先生《中國古琴流傳日本考》一文(載中外關系史學會編《中外關系史論叢》第2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頁)所述,茲不贅。不過,從《長沙古物聞見記》的描述和其他書籍所繪該樂器的圖形來看,*參見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圖二五五,第429頁。它的首尾皆設岳山,尾岳分為三排,樂器尾端有四個方首枘(已佚失),這些都是典型的古瑟形制,與古琴形制差別很大。因此,我們無法承認這是一張二十五弦的古琴,其面板上的宣聲指痕,可能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俟考。
最后看二十七弦琴。早在《爾雅·釋樂》中就提到:“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郭璞注曰:“(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五,第154-155頁。《爾雅》的成書年代雖然有多種說法,但不會晚于西漢,而《禮記·明堂位》又說:“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卷三十一,第851頁。由此可見,大琴之制在西漢時期甚至更早即已有之。至于將大琴的弦數明確為二十七條,則以郭璞之注解為最早,這表明至遲東晉以前也已經有二十七弦琴的存在了。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先生曾指出:“琴和瑟這兩個字之間的交替關系可能只容許得出一種結論,也就是說,最初只有一個字,……它既非后來的琴字,亦非后來的瑟字,而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弦樂器。……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樂器兩種形式之間的差異日益增大,以至于需要重新予以便于甄別的命名,因此就增加了表音的部首。這樣,兩種樂器的命名(造字)就完成了。”*高羅佩著、宋慧文等譯:《琴道》第一章,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版,第14-15頁。也就是說,琴、瑟本來是同源的古老樂器,其后才逐漸分化為二,此說甚有道理。由于古瑟的弦數很多,一般是五十弦或二十五弦,這就表明與瑟同源的早期古琴很可能有過使用較多弦數的發展階段。另從《樂書》著錄的二十弦大琴和日本流傳的二十五弦琴來看,把古琴制作成二十七弦也并沒有太大的技術難度。以上均佐證,二十弦以上的“大琴”應是早期琴史上真實出現過的形制。
三、七弦琴制及其確立
以上探討了十三種不同弦數古琴的基本情況,接下來想具體談談七弦琴制。早在先秦時期,七弦琴已經出現了。公元1993年,在湖北荊門市沙洋區四方鄉郭店村戰國中期1號楚墓中就出土過一張七弦琴,琴面橫設岳山,岳山外側有七個弦孔,孔距1.3厘米。此琴為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七弦琴實物標本,整體形制與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存在較明顯的同源關系。*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第241頁。換言之,七弦琴的產生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
另一張更為著名的七弦琴是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西漢早期古琴,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其形制與長沙五里牌楚墓所出古琴(見前述)十分相近;雖然琴弦已經腐朽脫落,但軫池內有七個八棱斜柱形角質軫,高1.5厘米,大端直徑1厘米,小端直徑0.8厘米,足以說明這是一張七弦琴;雁足頸上纏繞著殘弦,裹以絲織物,以防弦的滑脫;面板的弦路上有七道明顯凹痕,似是七根琴弦長期被重物壓在琴面所致。*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第451-452頁。
除出土文物之外,專門談到七弦琴制的古代文獻也有不少,而且時代較早。比如桓譚在《新論·琴道》寫到:
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琴長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寸,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隱長四寸五分,隱以前長八分。五弦,第一弦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少宮、少商;下徵七弦,總會樞要,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八音之中,惟絲最密,而琴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后漢文》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52頁。
桓譚是兩漢之交的人物,新莽時曾任樂部大夫,后漢光武帝時曾以鼓琴為給事中。此外,《說文》有云:“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時加二弦。”*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33-634頁。《風俗通義》又云:“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為君,小弦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第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本,第236頁。而《廣雅·釋樂》則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八,蘇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頁。以上所列大致是東漢至三國的文獻史料,表明這一時期人們對七弦琴的形制已經頗為關注。當然,說第六、第七弦為周文王、周武王所增,這恐怕只是傳說,目前沒有確切的證據。
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七弦琴依然得到一眾琴家的關注,我們可以舉嵇康、陶潛、王僧孺等人的詩文作品為例予以證明:
嵇康《酒會詩》:樂哉苑中游,周覽無窮已。……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九》,第486頁。
陶淵明《自祭文》:……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耕載耔,廼育廼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卷七,第462頁。
王僧孺《何生姬人有怨》:寒樹棲羈雌,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寶琴徒七弦,蘭燈空百枝。……*徐陵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2頁。
以上三篇作品都提到了“七弦琴”。其中《酒會詩》的作者嵇康是“竹林七賢”之一,琴、詩之學皆稱精絕,因不滿司馬氏之政,并遭鐘會誣陷,遂被殺害。*案,嵇康卒于公元263年,當時西晉尚未正式建立,但跟從嵇康學琴者很多,他所說的“七弦”琴制在西晉時期必定有較為廣泛的流傳。《三國志》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于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06頁。可見他在琴藝上的造詣。而陶潛之愛好古琴,亦已見前文所述。至于梁人王僧孺,是東海郯人,曾為齊竟陵王蕭子良西邸文士,入梁后官至御史中丞、少府卿等職,《梁書》(卷三十三)有傳。他作有“琴歌”《湘夫人》一首,收錄在宋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琴曲歌辭》之中,可見僧孺也是一位善琴之士。
以上種種情況說明,當時琴家對于七弦琴制是非常了解的,也常用于實際演奏。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七弦琴的勢力似乎仍然比不上五弦琴,以下先看兩首相關的詩歌作品:
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第十三章):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83頁。
謝安《與王胡之詩》(第六章):朝樂朗日,嘯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鳴琴。五弦清激,南風披襟。醇醪淬慮,微言洗心。幽暢者誰?在我賞音。*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十三》,第906頁。
這兩首詩都提到了“五弦”,結合前引《酒會詩》可知,琴家嵇康既能彈奏七弦琴,亦能彈奏五弦琴。至于謝安,不但是東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而且善于彈琴,據《南史·柳惲傳》記載:“(蕭)子良嘗置酒后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柳)惲,惲彈琴為雅弄。”*李延壽:《南史》卷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987-988頁。謝安的“鳴琴”能夠流傳至南齊而且受人寶重,足見他在琴學上有一定的造詣。約而言之,從琴家對于古琴弦數的記述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五弦琴的勢力應當不在七弦琴之下。
更為重要的證據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古琴實物雖未見傳世,*案,目前有幾張古琴號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器物,但未獲得學界認可,不贅;此外,日本正倉院所藏“金銀平文琴”是一件很特殊的寶物,但爭議仍很多,也不在此討論了。但相關的圖像史料卻尚存十余種,主要是畫像磚、畫像石、繪畫、漆畫、銅鏡等,其中有兩件能夠比較清晰地反映出時人所彈古琴的弦數。第一件是南京西善橋南朝齊、梁墓葬中出土的一幅畫像磚,命名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現藏南京博物院;磚上繪有榮啟期和竹林七賢等八個人物,其中榮啟期與嵇康均在彈琴。筆者曾經近距離認真審度過這件文物,所繪榮、嵇二人彈奏的古琴都是五弦形制。第二件是山西大同雁北師院宋紹祖墓出土的北魏太和元年(477)石槨,石槨正壁刻有彈琴、奏阮的人物圖像,學者認為“可能受到了南朝的影響”;而所彈的古琴也比較清晰可辨是五弦形制。*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圖150,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頁。由于畫像磚、畫像石的作者往往是一般工匠,這就反映出五條弦數古琴形制之深入人心;*案,畫像石的面積較大,足以清晰繪出古琴的具體弦數;而前述東漢銅鏡的直徑只有十幾厘米,不可能將樂器弦數都刻畫出來,所以二者不能一概而論。同時也說明,七弦琴的影響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能仍遜五弦琴一籌。
只有到了唐代,七弦琴才開始在各種弦數古琴的使用中占據絕對的優勢。這一說法有一項有力的證據予以支持,也就是從傳世唐琴的弦數來看,基本上全是七弦的形制。近代古琴鑒定名家鄭珉中先生曾在《唐宋元明琴器流變》一文中指出:“楊時百(楊宗稷)1928年《琴學叢書》中肯定的這四張唐琴就成為盛唐、中唐、晚唐琴的標準器,同時也是雷氏琴中宮琴、野斫的典型。根據這個典型,計發現盛唐琴二張,中唐琴六張,晚唐琴七八張,其中宮琴四張,野斫十二張。”*鄭珉中:《蠡測偶錄集:古琴研究及其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頁。此外,鄭氏在《唐琴辨》一文中又指出:“在傳世古琴中已經肯定為唐代制作的計有伏羲式6張,魏揚英式、李疑式各3張,師曠式2張,子期式、仲尼式、神農式各1張,共7種17張。這其中有盛唐、中唐、晚唐三個歷史時期制作的雷琴和宮琴。”(鄭珉中《蠡測偶錄集:古琴研究及其他》,第117頁)這十余張古琴為唐琴的鑒定結論現已被學界認可,而它們無一例外都是七弦琴。與此同時,五弦或者其他弦數的唐琴一張也沒有留傳下來,由此比較有力地證明,七弦琴占絕對優勢的時代已經來臨。
此外,唐人詩句中有多處提到“七弦”,并以此作為古琴的代稱,這也是上述觀點的一項佐證。茲舉數例如次:
常建《江上琴興》: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殷璠編《河岳英靈集》卷上,收入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陜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頁。
劉長卿《聽彈琴》:泠泠七絲(一作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清官修:《全唐詩》卷一百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481頁。
白居易《船夜援琴》:鳥棲魚不動,月照夜江深。身外都無事,舟中只有琴。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即聲淡,其間無古今。*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29頁。
趙摶《琴歌》:綠琴制自桐孫枝,十年窗下無人知。……七弦脆斷蟲絲朽,辨別不曾逢好手。……*清官修:《全唐詩》卷七百七十一,第8752頁。
李建樞《謝人惠琴材》:風撼桐絲帶月明,羽人乘醉截秋聲。七弦妙制饒仙品,三尺良材稱道情。……*清官修:《全唐詩》卷七百七十五,第8782頁。
從上舉諸例不難看出,唐人已習慣于用“七弦”指稱古琴,這是七弦琴制確然獨立的又一證據。那么唐詩中有沒有提及“五弦”的呢?有倒是有,但似乎與古琴沒有必然聯系,比如白居易《五弦》詩云:“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胸撫。大聲粗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二,第34頁。這種當胸、抱撫的樂器近于琵琶、阮咸一類,顯然不是古琴。又如白居易《五弦彈》詩有云:“五弦彈,五弦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弦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弦不如五。”*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三,第70頁。既云“古琴有弦人不撫”,這種“五弦”顯然也不是古琴。唐人詩歌既用“五弦”指稱古琴以外的另一種樂器,則當時古琴僅安五條弦的情況當是甚少的。
因此,唐代確實已經成為七弦琴的天下。雖然宋人在古琴弦數上或創新、或復古,弄出一弦、兩弦、三弦、九弦、十二弦、十五弦、二十弦等多種形制,卻很難影響七弦獨尊的既定格局;*案,雖然宋代朝廷祭祀儀式中有多種弦數古琴并用的情況,但宋代以后這些非七弦形制的琴就逐漸消亡了;另外,自宋至清的琴學著作和琴曲譜錄絕大多數都約定俗成地將古琴視為七弦琴,可見自唐以來七弦獨尊的格局并沒有太大改變。直至今天,人們在學習、演奏古琴的時候,也一無例外地在使用七弦琴;而這也導致某些人誤認為古琴從一開始就是七弦的形制,所以筆者對此略作辨析如上。
小 結
通過以上考述可知,中國歷史上的古琴弦數至少出現過十四種形制,即無弦琴、一弦琴、兩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十弦琴、十二弦琴、十三弦琴、十五弦琴、二十弦琴、二十五弦琴、二十七弦琴。如果單從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來看,只有二十五弦未見著錄。其余見錄的十三種弦制,似乎以五弦琴的出現為最早,據《樂記》稱在虞舜時期就有了;其次是七弦琴,據很多文獻說是周文王、周武王時代出現的;其后又有多種弦數古琴的出現,到北宋后期基本臻于齊備。諸種形制當中,流傳最廣泛的無疑是五弦琴和七弦琴;唐代及以后,七弦琴更在演奏中占據了絕對優勢。
不過,近代考古出土的古琴實物卻增加了這一發展序列的復雜性。因為現存最早的古琴實物既不是五弦琴,也不是七弦琴,而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其次才是七弦琴,均屬先秦之物,這就與文獻記載的次序頗為抵牾了。由于文獻記載較多傳聞成份,而出土古琴實物的數量又極其有限,所以目前尚難就上古時期何種弦數古琴出現時間最早這一問題作出判斷。所幸的是,中古以來的情況則要清晰得多;因為出土的南朝畫像磚和畫像石使我們得知,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五弦琴和七弦琴并行,但五弦琴的勢力要稍占優勢;而存世的唐琴樣式又使我們得知,唐朝確乎是七弦琴的天下。
此外,宋代是古琴弦制頗有發展的時代,出現過兩弦、三弦、九弦、十二弦、十五弦、二十弦等多種樣式,這就進一步增加了琴弦發展歷史的復雜性。特別是陳旸巨著《樂書》中關于古琴弦數的記載,有的地方為宋以前古籍所無(如關于十三弦“頌琴”的記載),有的地方又與宋以前古籍頗存分歧(如關于“大琴”弦數的問題),這都有待未來作更深入的探索。不過,從前引《宋史·樂志》“(魏)漢津誦其師之說”的內容來看,宋琴的一些新弦制頗有可能是“托古改制”而產生的“假古董”,其出現亦難以撼動七弦琴獨霸琴壇的局面。
總而言之,以上研究至少說明了四點情況:其一,古琴形制包括材質、音箱、琴弦、構件(如岳山、雁足、琴軫、龍齦、鳳嗉)等多個方面,其中弦數的發展變化至為復雜,過往的琴史著作對此缺乏專門的資料搜集和研究,本文的考述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個空白。其二,弦數的五花八門、記載與文物的相互抵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古琴發展歷史的復雜性,即使是七弦琴制的確立和流行,也決非一蹴而就的過程,這就提醒琴史研究者對此“復雜性”應有更加充分的認識。其三,魏晉南北朝時期有無弦琴、一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二十七弦琴等并行于世,兩宋時期有一弦琴、兩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十二弦琴、十五弦琴、二十弦琴等并行于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兩個時期是琴藝和琴制發展的興盛時期,未來的琴史研究應該對這兩個時期多加關注。*案,關于宋代古琴,已有章華英先生頗具份量的《宋代古琴音樂研究》一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正式出版;但對于魏晉南北朝古琴歷史的研究則仍然比較薄弱,根據筆者掌握的史料,魏晉南北朝時期琴家有姓名流傳下來的接近二百位,有一定可靠史料可供考索者約有一百三、四十位,已遠遠多于朱長文《琴史》、蔣克謙《琴書大全》、周慶云《琴史補》、查阜西《歷代琴人傳》等書的著錄,所以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其四,研究表明,古往今來琴弦數量一直允許有多種形制存在,最后以七弦占優,是一個歷史發展和歷史選擇的過程,其它弦數的古琴也并沒有因此便完全銷聲匿跡;但現行的某些琴學著作卻將弦數不是七弦的早期古琴(特別是一些出土的古琴)統稱為“類古琴”,未免有割裂歷史聯系和歷史發展之嫌,這仿佛是將古人居住的房屋統稱為“類房屋”,似乎沒有多大必要。
當然,除了琴弦以外,琴的材質、音箱、構件等都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因論文篇幅所限,暫時無法討論。即使是琴弦方面,也尚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比如古琴弦數的多少和彈琴手法、琴曲藝術表現力等是否存在某些聯系呢?對此,李純一先生曾經指出:“弦數較少當是為去掉那些不大理想的高端弦,以使音色較為統一和音量較為均衡。……弦數由較多變為較少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這要看它是屬于哪種情況而定。如果一琴僅能奏散音,或者能兼奏少數按音和泛音,那么減少弦數就等于降低性能,也就意味著退步;而如果能兼奏較多音質較好的按音和泛音,舍棄那些不大理想的高端弦,當然是一種進步。”*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第452頁。這一看法頗有道理,但似乎尚有深究的余地。同樣是因論文篇幅所限,筆者擬另文再作探討。所述不當之處,謹祈方家教正。
[附識]近十年來,由于兼職“非遺”專業的教學與調研,陸續草成“琴棋書畫雜考”系列論文十余首,其中第一篇《魏晉南北朝琴藝傳承考述》已刊載于《文化遺產》2015年1期,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二篇,主要探討歷代古琴的弦數制度。動筆至今已八易其稿,感謝田煒兄在東漢銅鏡銘文釋讀上的幫助,從而初步廓清了四弦琴的疑問。
[責任編輯]羅曼莉
黎國韜(1973-),廣東廣州人,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為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周佩文(1973-),廣東開平人,文學碩士,《南方都市報》資深編輯。(廣東廣州,100875)
G122
A
1674-0890(2017)01-1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