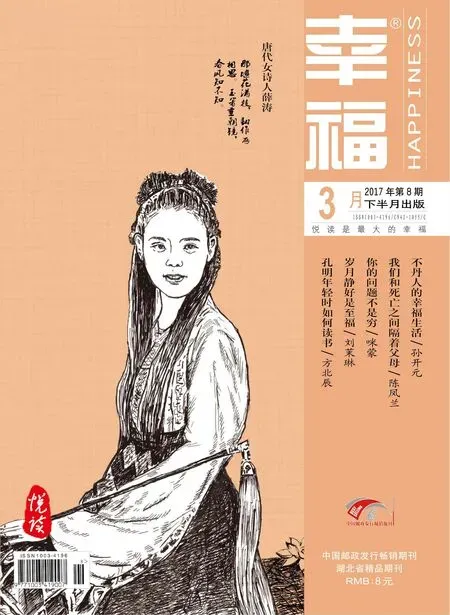歲月靜好是至福
文/劉茉琳
歲月靜好是至福
文/劉茉琳
今日接到閨蜜電話,告知一位中學好友突然離世,他是家中獨子,上有老父母;下有嬌妻稚兒,小兒尚不足半歲。這樣的消息太殘酷。
再看李漁句:“勸人行樂,當以死亡怵之。”真當頭棒喝!
平日說“人生苦短”似一句玩笑,今日方知真正的短是這樣驟然而止,真正的苦是無法言說的悲與痛。
記得大學畢業前夕,一位摯友的父親遽然離世。對那位摯友打擊極大,父親沒有看到她繼續深造收獲好的工作,沒有能陪伴她穿上嫁衣走上紅毯,對她自然是一輩子的傷痛。
這件事情當時把我也嚇壞了,我有大半天的時間都無法說話,真的是被嚇壞了。我們的生活太平和,突然間近距離地感受到死別,你才知道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安慰,沒有,這就是悲劇,無法安慰。
這些突如其來的悲劇,會撕裂所有貌似圓滿的人生,不管你是襁褓中的嬰兒,還是中年的妻子,又或者年少的女兒,年邁的父母,這種撕裂永無愈合的可能。所做的,只能是等待,等待時間,等待生活的細流慢慢掩蓋,卻永遠無法治愈。
《閑情偶寄》“頤養部”開篇第一句:“傷哉!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彼夭折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歲之虛名,并無一歲二歲享生人應有之福之實際乎。”
人生真正追歡取樂總是有限光陰,亂世走來的人們則更懂得人生之福氣所在,喜樂所系,平安之重。
年少時讀杜甫,只記得“霜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直到這優美詩句變成了中秋節的例牌廣告詞,年歲漸長才懂這后面兩句“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是怎樣悲傷的處境,而“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又是怎樣心痛的領悟。
李漁也是從亂世走來的人,明清易代,戰亂匪禍經年,家業幾乎全毀于戰火不說,精神上也承受了巨大打擊,而縱觀他一生,父親離世也是他一生生命軌跡的拐點,所以,他引圣人語“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是有很深的個人體會的。
同樣,身處亂世的張愛玲胡蘭成才會在交付人生的婚書上祈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那一份今生今世的歡愉仿佛是偷來的,才演繹了生生世世的傳奇。傾城之戀成全的愛情是不是圓滿我們不知道,但當年香港轟炸之慘烈會不會也如畢加索筆下的《格爾尼卡》呢?
和平盛世的我們生活太安穩,已經不記得握在手里的幸福,已經看不見眼前的喜樂。
我們是不是總要那些不幸的事情在身邊發生了才能提醒自己的幸運呢?
是不是總要等到幸福清零的一刻才知道曾經擁有過呢?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就是平安,才會有真正的喜樂。這是人生圓滿的背景,如果你正擁有,用心珍惜就好。
這是第一次在文章里寫到那位摯友失去父親的事,對于她是無法面對的傷痛,我亦陪著她從不敢觸碰。記得她說過,有時候她會夢到自己的父親在一條河的對岸生活,在那里一直看著她,愛著她。
如果真有這樣一條河,我希望,我那位同學的孩子也能感到自己的父親一直在看著他們,愛著他們。
摘自金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