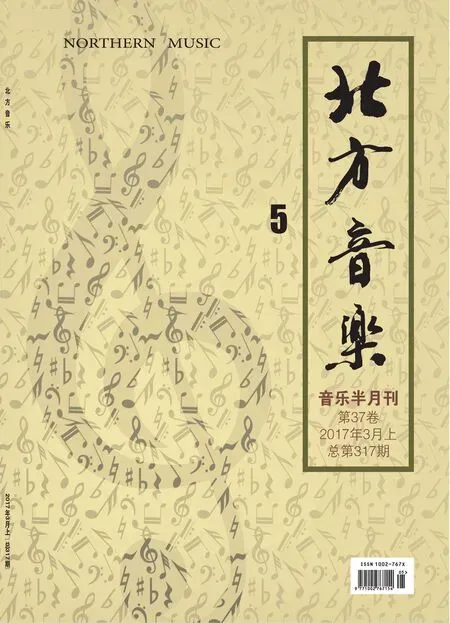簡論圣母院樂派興起之歷史條件
趙明瑋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簡論圣母院樂派興起之歷史條件
趙明瑋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本文從文化學的宏觀視野入手,深入討論了圣母院樂派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條件。并指出,圣母院樂派的興起以基督教的發展為背景,但在繼承發揚舊傳統與宣揚宗教之時,客觀上為開啟中世紀晚期以至文藝復興音樂藝術發展新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方音樂史;圣母院樂派;宗教音樂
“中世紀”一詞歷來在學術界以外都定義模糊,在大眾文化里,中世紀是神秘、血腥與蠻荒的混合物。“十字軍”、“巫術”、“騎士”等成為了中世紀的標簽。然而,“中世紀”卻依然出現了輝煌燦爛的文化遺產。在這段時期里,不僅古希臘與羅馬的典籍得以保存和研究,同樣也出現了極其重要的新著作,如神學、哲學領域有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文學方面有但丁的《神曲》等。而大學及其教育系統的建立、議會制的創建以及司法審判的定型都是中世紀的重要貢獻。
音樂,作為“七藝“之一,不僅是禮拜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儀式經文的組織、強化與揭示功能更是成為了后代西方藝術發展的重要靈感與動力。美國學者杰羅姆-尤金在其《歐洲中世紀音樂》一書中提到,“這是一個發酵與融合的時期,追求與禁錮、創新與泥古、學術與妄想都大行其道。”圣母院樂派就是這樣一個時期的產物。在《新牛津音樂史》中,該時期被認為開啟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復調音樂傳統,其復調寫作技法的精妙與宏大,作品效果的創新與震撼都持續影響著其后數百年的音樂發展。接下來我將著重從歷史與音樂方面論述圣母院樂派產生的原因。
公元十二、十三世紀的西歐在整個中世紀最富于創新。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基督教發起了著名的十字軍東征,占領了耶路撒冷;在學術與藝術領域,建立著名大學,沉重的羅馬風格為精巧的哥特風格所取代。整個社會因為蠻族已皈依基督教而不再受到外來力量的侵擾,內部環境因教皇權力的至高無上而大大減少了分封王侯之間的戰爭。可以這樣說,自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從未像這樣平衡與穩定過。
作為法蘭西王國首都的巴黎在當時綜合體現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中最為突出的兩點即是巴黎大學的建立與圣母院的建造,而后者更是當時全歐洲最為雄心勃勃的建筑計劃。若對比圣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兩位中世紀最為重要的教父,可以清楚的發現,充盈前者著作中那種對異教徒的強力批判與攻擊口吻在后者的筆端卻化為精妙與深邃的理性和邏輯辯駁。在建筑領域,圣母院的修建也表明了哥特風格對于羅馬風格的全面取代。郎格認為:“(哥特風格)試圖營造出一種建筑的動態,讓巨大豐富的表現力在其中充分展現,而這一理念的實現勢必讓古老風格中那些靜止與分離的空間感逐漸消失。換言之,羅馬風格中那些厚重與肅穆的建筑空間讓位給了哥特風格——其令人目眩的動態與高度仿佛讓石材失去了重量。”
就像其他領域一樣,兼顧宗教禮拜功能與“七藝”之一的音樂也同樣經歷了相似的變化與發展。從舊約時代開始,宗教崇拜與音樂之間的關系與互相影響就持續不斷,早期的教父們堅信參與其中的信眾能感受到更強大的感染力。圣奧古斯丁在其《懺悔錄》中寫到:“那些聲音涌入我的耳朵,使其真意滲入我心,而信心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以致淚流滿面。這讓我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 然而,12世紀的巴黎已非700年前的圣奧古斯丁時代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單聲部圣詠已經逐漸失去了對教會和信眾的感染力。
目前,已知的最早多聲部文獻來自于9世紀,如在《音樂手冊》(Musica Enchiriadis)與《溫切斯特附歌集》(Winchester Tropers)中,出現了在素歌的主題下方純四度和純五度上以音對音形式添加的第二聲部,以起到伴奏與潤色的效果。這樣的早期復調手法從11世紀開始有了更多的變化。在阿奎丹復調與加里斯都手本(Codex Calixtinus)的例子中,奧爾加農的聲部開始逐漸獨立于素歌主題并富于變化,甚至有時取代了定旋律(Cantus Firmus)在圣詠中所固有的主導地位。聲部之間的對位關系也不再嚴格按照純四、五度和音的模式進行,而開始出現其他對位變化。這種演唱方式逐漸形成了“花式奧爾加農”(Florid Organum)風格,而正是從這樣的風格中,逐漸演化出更加復雜與精妙的克勞蘇拉(Clausulae)與康都克特(Conductus)風格,以及經文歌(motet)——后者為圣母院樂派最重要的創新之一。記譜法的日趨完善也為圣母院樂派的興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9世紀出現紐姆譜,11世紀早期,阿萊左的圭多(Guido d’Arezzo)提出了更完善的形式。直到13世紀早期列奧寧編著《奧爾加農大全》(Magnus liber organi),首次以全新記譜法創作教會整年所需要的各種禮拜音樂,讓之前只存在于即興與口授方式的復調音樂第一次以創作與記譜的方式出現在了音樂史中。
關于圣母院樂派最直觀與早期的記錄來自于1275年被冠以“匿名者第四”的手稿文獻,其中寫到:“列奧寧大師應為當世最偉大的奧爾加農作曲家,它所編輯創作的《大全》大大提高與升華了升階經(Gradual)與應答圣詠(Antiphonarium)在禮拜儀式中的感染力。而佩羅坦大師則在迪斯康(Discant)與四部奧爾加農的寫作上體現出極為豐富的色彩與和聲的藝術。”這一點上它與圣母院建筑本身宏大與玄妙的裝飾功能遙相呼應。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世紀無論思想、建筑還是音樂,其最初的發展動機幾乎都是出于純宗教的,也即是為了讓信仰的力量更大更深入地遍及整個社會與人心。圣母院樂派的興起也不出其二,但它在繼承發揚舊傳統與宣揚宗教之時,卻有意無意的開啟了藝術的新局面。從這里不僅出現了最早的署名作曲家,如列奧寧與佩羅坦,也讓音樂逐漸開始從禮拜圣詠中獨立出來并開始多樣性的發展。正如郎格所說,“這是一種根植于古代傳統與意識形態而極富創新、直指未來的藝術,其表現手法與感染力如此新穎,但當我們仔細剖析時,卻又發現了古老的信條與法則。”
[1]朗格,保羅-亨利.西方文明中的音樂[M].紐約:W.諾頓出版社,1941.
[2]尤金,杰瑞米.歐洲中世紀音樂[M].新澤西:普倫提斯殿堂出版社,1989.
J60
A
趙明瑋,男,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桑頓音樂學院音樂表演碩士,現為四川音樂學院管弦系大提琴教師、交響樂團大提琴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