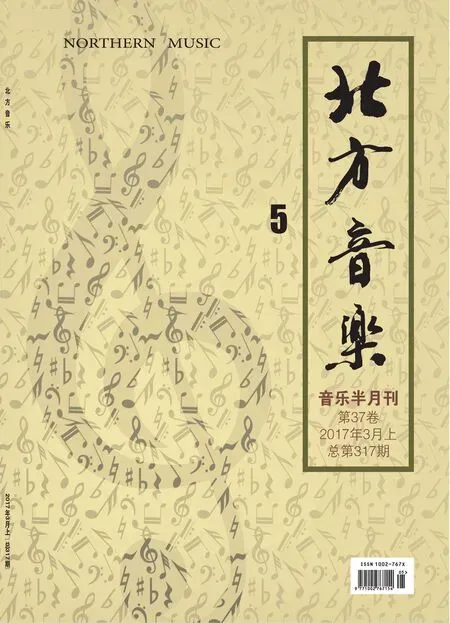簡析真實主義歌劇的演變由來及特點表現
高媛媛
(河南經貿職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簡析真實主義歌劇的演變由來及特點表現
高媛媛
(河南經貿職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真實主義歌劇是飽含人文關懷的人本主義回歸,雖核心力量作用于“人性”,但并不以“人物”為出發點。宏觀的社會背景渲染,為的是透視折射出生活在當下社會中真實的人物悲劇。釀成悲劇苦果的原因,不歸咎于命運蹉跎,而是拜黑暗社會親手所賜。沒有懸念,沒有驚喜,樸實的音樂語言在平鋪直敘中披露了一切真實的因果關聯。歐洲歌劇在經歷了百年發展之后,迎來了別具特色的真實主義創作時期。較之古典與浪漫主義時期創作手法的單調及題材選擇的局限,真實主義歌劇另辟蹊徑,以獨到的創作簡介與藝術構思,完成了一次自主覺醒之后的徹底超越。
真實主義歌劇;浪漫主義時期;威爾第;演變發展;特點
在威爾第創作歷程的后期,其自身對于歌劇題材的認識發生了轉變。一者是出自于內心對文化變遷的萌動;再者也得益于新生代劇作家文化視角轉變的提醒。在威爾第個人劇創風格的扭轉中,一個叫做真實主義的歌劇時代悄然來臨。它的出現并沒有徹底否定浪漫主義殘存的余溫,但其自身所營造出的氣場卻又特立獨行,獨樹一幟。它的出現延續了浪漫主義藝術的生命,同時也為一個屬于人類歌劇史最輝煌的大時代完美收官。
一、從浪漫主義向真實主義歌劇的過渡演變
威爾第是浪漫主義時代的巨匠,也是開啟真實主義大門的領路人。在他初入創作領域的19世紀40年代,羅西尼早已封筆,貝利尼剛剛撒手人寰,多尼采蒂已近暮年。正直歌劇界青黃不接之際,威爾第的《一日之王》橫空出世,開始嶄露頭角。他早期的創作多是受制于委約人的要求,根據買主或歌手的興趣進行創作,作品風格趨向于貴族生活的審美趣味。在成名之后,威爾第有了獨立創作的空間,告別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朝著理想的藝術面貌挺進。與瓦格納的宗教色彩與史詩性題材不同,威爾第更愿意誠摯地表現生活經歷中的所見所聞,成為向莎士比亞致敬的真實主義作曲家。
威爾第歌劇創作的題材并沒有與同時代的大多數作曲家一道攜手挽肩。在大家都傾倒于瓦格納的大氣磅礴之中時,威爾第更加青睞于看似平庸,卻非同一般的社會現實。《茶花女》的題詞描述的是小仲馬與上流社會的高級妓女瑪麗·杜普萊西之間的愛情往事,當輿論的壓力正在大肆批判這部文學作品的離經叛道時,威爾第卻情有獨鐘,僅用了四年的時間,就將這部作品原封不動地移植成了歌劇。這不僅僅是歌劇題材的突破,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中,將一名風塵女子作為戲劇主角,并在戲劇演繹中將其塑造成為忘我犧牲的圣女化身,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膽大妄為”。但威爾第真的做到了,并“揚言”:“這是一個時代的主題”。[2]
作為莎士比亞戲劇忠實的迷戀者,威爾第繼承了偶像悲喜劇的文學風格,這在《弄臣》與《茶花女》中表現得尤為精彩。當正劇的莊嚴肅穆;喜劇的滑稽詼諧;悲劇的感動痛楚三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戲劇的張力不僅被拉伸到極點,還會使每一位觀眾感受到其中似曾相識的人生片段。這就是真實主義歌劇的深刻性,也是那些傳奇般不食人間煙火的浪漫歌劇題材所不具備的審美力道。
從另一角度而言,歌劇藝術的頓悟并非閉門造車過程中的自省,它往往與文學領域劇作家們的敏銳嗅覺同步契合。在真實主義歌劇的道路上,我們同樣能夠感受到來自于文學界由浪漫主義向真實主義的轉變力道。受法國文學界“自然主義”的影響,意大利文學在19世紀70年代出現了真實主義的端倪。作為批判現實主義的延伸,意大利真實主義文學對于現實揭示的力度、深度以及決心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喬萬尼·維加爾和路易吉·卡普安納的領導下,意大利文學界掀起了對法國福樓拜與左拉等大師的文學崇拜。卡普安納的小說《吉雅琴塔》率先點燃了意大利真實主義文學的火炬,他甚至借此來向左拉致敬。身為文學理論家的卡普安納,在其《談藝術》、《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意大利戲劇》等著作中,逐漸形成了具有意大利獨立人文觀的真實主義文學見解。受其影響,文學大師維爾加從早年的《一個修女的故事》和《山地的燒炭黨人》等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抽離出來,創作出了具有深刻真實主義情懷的《奈達》、《田野生活》、《鄉村故事》等作品。
對于后輩的真實主義歌劇作曲家來說,主要繼承的仍是威爾第的衣缽,雖有所變革,但并未像瓦格納一般激進。我們在靜靜地聆聽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和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時,并不會覺得與威爾第的《弄臣》與《納布科》之間有多么大相徑庭,反而有一脈相承的親切之感。可見,真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差別,并沒有在技法上分道揚鑣,而主要集中于戲劇題材、美學特征與內涵所影射的寓意之中。
二、真實主義歌劇由內而外的藝術顛覆
前有威爾第承上啟下的開疆拓土,中有比才在法國歌劇藝術領域中的遙相呼應,后又普契尼的繼往開來。真實主義歌劇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變遷是一種對于保守封閉了百年的創作線路徹底的顛覆。這些大師的作品,從題材選擇到戲劇構思、寓意闡釋、審美訴求,都在潛移默化之中娓娓道來,由內而外的轉變與中國古典哲理中的“相由心生”如出一轍。
威爾第的《弄臣》于個人而言,首開了真實主義的先河。故事情節構建在一個極為深刻的反諷上,劇中的男主角里格來托作為一名宮廷弄臣,地位卑賤卻媚主阿諛、作惡多端,喪失人性的他卻又有著對女兒百般呵護的慈父形象。他的女兒吉爾達終究沒有逃脫公爵的魔爪,惱羞成怒的里格來托精心策劃了刺殺公爵的行動,誓為女兒報仇,可結局卻弄巧成拙,殺死了自己的女兒。這樣的戲劇題材并沒有流俗于司空見慣的報應循環,而演繹成了善無善報,惡無惡果的天理不容。可惡的公爵和格里萊托依然活著,但善良可愛的吉爾達卻成為兩個惡人角力的犧牲品。雖看上去于情于理都難以讓人釋懷,但仔細想來,這不正是現實中屢屢發生的人間災難么。當里格來托以宣敘調吟唱著殺死公爵后的洋洋自得時,遠處卻傳來公爵熟悉的《女人善變》歌聲,這對舞臺上的里格來托來說,無異于當頭棒喝,也給予臺下的觀眾一個可怕的暗示。麻袋里死去的絕非公爵,第一幕的詛咒在全劇的最后應驗。對于里格來托來說,這絕非僅是一種悲劇,而是莫大的嘲諷與羞辱。也許此時他所承受的報應遠比死亡來的激烈百倍。
在意大利歌劇發展的如火如荼之時,比鄰的法國也誕生了一位極具天賦的歌劇作曲家比才。在19世紀70年代,30多歲的他便創作出了不朽的《卡門》。僅憑這一部作品,比才在歌劇界的地位就可比肩前輩瓦格納,并為法國音樂創作指引了前進的方向。《卡門》取材于本土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說,以現實生活為憑,刻畫了許多鮮活的藝術形象。在宗教神話與宏大的史詩性作品占領舞臺的時代,比才憑借著年輕人的革新精神,走出了一條不同尋常的創作道路。
《卡門》一劇中的人物有平凡的煙廠女工,下等的軍人班長,齷齪的走私犯以及西班牙特有的斗牛士。這些人物都是游走于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他們的七情六欲,人生悲喜從來沒有人愿意書寫在高雅的歌劇舞臺上。而這些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內心糾葛,情感放縱等細微的精神表征,都被敏感的比才以生動的歌唱與表演刻畫出來。戲劇的撲朔迷離,陰差陽錯,擺脫了古典主義歌劇中以歌為主,劇情平庸的怪圈。多回目的場景變化,將卡門的放蕩不羈、移情別戀與唐·豪塞的瘋狂癡情、心灰意冷詮釋得淋漓盡致。戲劇的張力層層深入,最終激化到頂點,在斗牛士埃斯卡米里奧的歡呼聲中,卡門被無情的殺死。對于結局而言,并沒有所謂的另“親者痛,仇者快”。也沒有將壞人繩之以法,有情人終成眷屬。殘破的結尾印證了每一個人物不完整的人生,而真實主義正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得到升華。后世在對《卡門》的評價中,并沒有否定這部作品所蘊含的浪漫氣息,畢竟身處藝術氛圍的大環境之中,戲劇的真情實感并沒有冷落了世間的人情味兒。比才并未掩飾內心對生活的歌頌,對真愛的贊美,讓我們看到每個人性背后皆存在著的善與惡。
普契尼作為真實主義歌劇的核心人物和浪漫時代的終結者,繼承并將威爾第的歌劇理想發揚光大。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真實主義創作的暴力與真切,感受到他對于法國深情音樂歌劇的借鑒,折射出德彪西抽象的音樂邏輯感。在新舊交替,即將告別19世紀精彩紛呈的藝術殿堂時,普契尼以別具匠心的旋律色彩,趣味性極強的和聲,規整嚴謹的配器組織,向過往的百年致敬,并開啟了新的歌劇空間。在世紀拐點到來之際,歐洲的音樂藝術早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宮廷貴族所獨享的文化盛宴。普通民眾對于高雅藝術的需求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滿足,而大眾的世俗化審美訴求也得到了真實主義劇作家的關照。
首演于1896年的《藝術家的生涯》來源于法國作家繆爾若的小說《波希米亞人的情境生活》。作品描述了一群生活在巴黎閣樓上,窮困潦倒的文化人,他們饑寒交迫,卻又各自胸懷理想。在狹小的空間環境中相互關心有愛,充滿歡樂與憂傷。尤其是繡花女咪咪與詩人魯道夫崎嶇坎坷的愛情經歷,成為戲劇中的主線。由此,普契尼也開始形成了與前輩偶像相似的審美情懷,表現平凡的生活,表達小人物虐心的愛情。此后,普契尼在《托斯卡》塑造了羅馬畫家為保護政治犯而與邪惡勢力同歸于盡的悲慘故事;在《蝴蝶夫人》中描繪了巧巧桑為愛情感人至深的犧牲;在《圖蘭朵》中將具有東方情調的英雄性、悲愴性、抒情性推向了極致。
在以威爾第、比才、普契尼為代表的三位音樂大師共同奮斗中,真實主義歌劇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徹底顛覆了以往陽春白雪,高不勝寒的歌劇題材。宮廷奢靡的生活景觀與王室貴族的傲慢從此告別了大行其道的時代。真實主義歌劇敞開心扉,以平實的記敘方式著眼于都市生活,與公眾的生活閱歷嚴絲合縫的對接。其間所透露出來的關懷、理解、體恤、同情,在創作與欣賞之間架起了溫暖的審美橋梁。
[1][波]麗莎.音樂美學譯著新編[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74.
[2]張前.音樂美學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177-206.
[3]洛秦.音樂與文化[M].寧波: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58.
J832
A
高媛媛,畢業于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古箏專業,河南省音樂家協會會員,現就職于河南經貿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