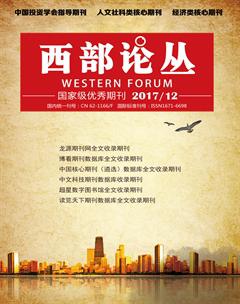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擇偶特征個案研究
劉偉
摘 要:婚戀是青年男女重要的人生課題,因此懂得如何選擇合適的異性伴侶,是現代男女交往的第一步,也關系到未來幸福家庭的建立。本文以廣西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研究對象,在社會學理論基礎上,對新生農民工擇偶過程中的行為動機分析,揭示新生代農民工階段性的擇偶需求表征,借助理論框架辨析以探索擇偶行為的模式、價值觀和意義,為新生代農民工“擇偶難”問題提供借鑒。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婚戀觀 擇偶標準
一、研究背景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是中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做出了巨大貢獻。2018年4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指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這是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首次過半。近年來這群人的婚戀問題成了眾人關注的焦點,據《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顯示,63%的基層打工者處于單身狀態,有對象的37%中,感情能維持一年以上的只有56%。“擇偶難”成了該群體亟待解決的問題。
擇偶是生理,心理,文化交互作用下的行為。隨著社會結構迅速變遷,新舊社會制度變化中,有關男女傳統的角色的定位也在不斷轉變。女性可以是商業精英,被標榜為現代女強人的典范,而男性可以是持家的賢內助,被贊為貼心“暖男”。從社會角色的角度來說正是角色期待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擇偶行為,因此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擇偶行為的特征有助于推進新生代農民工“擇偶難”問題的研究。
二、新生代農民工擇偶特征分析
(一)、“我“與他/她的相識階段
1、擇偶渠道:男女結緣,業緣、地緣皆靠譜
擇偶渠道每個時代不盡相同,盡管交通發達,科技進步,可供人們結緣的方式向多元化發展,但經筆者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擇偶渠道,多依賴自己的業緣或地緣,其中男女無太大差異。換言之,他們擇偶候選人多是身邊能夠接觸到的人,一般是工作中的同事或是朋友,鮮有選擇異地戀。
“我的對象有些是以前上學時候的同學,一些是在我工作時認識的。那時我在ZS的一個酒吧里打工做吧臺的,她家就在附近,所以就常來喝酒,我們就認識了。我交往的對象要不就是同事,要不就是同學。我沒談過異地戀,都是我生活圈子的人,或者是qq群,閑聊的那種qq群,然后就約著打游戲認識的。”
從中我們看到,距離是擇偶的關鍵因素,青年男女二人素昧平生(如路人),空間距離,區域遠近,確實會影響擇偶的機會。同時這種距離不再局限于地域,更趨向于一種“業緣”,以“共事”為中心,辦公室戀情,兩小無猜的愛,甚至是網戀。
2、相識“眼緣”是基礎
當一個人同另一個人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被對方的外表長相、氣質神韻所吸引,這種現象就是眼緣。就是看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者說是你看對方覺得親切,主要是指自己通過眼睛觀察對方而感到不陌生,反而有熟悉的感覺。自由戀愛中的初期很少看重對方財富,知識,地位等深層次方面。“長相處開始就是看對眼,然后看相處一段時間和不合適,如果開始就不合適,那我想后面不會久。”
所謂的一見如故,一見鐘情,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相聚淡如水,正表達了青年男女二人的好感的互換,而眼神的交流優先于物質交換,正因這種認知,這種心靈磁場才會產生共鳴。若沒有這一契機,是很難繼續進一步發展的。
3、告白女性也主動
現代化的社會強調自由戀愛,由年輕人自己做主。人們互動機會多,選擇機會更多,無論男女自主性都較過往增強。戀情的開始時,通常需要通過告知來確立更進一步的關系,所以提出確立關系的這一行為就稱為告白。一般情況下是男方向女方告白,這通常被認為是正常的,如果一個女性向男性告白,就會被視為很奇怪,或者女方本人也會擔憂這一行為是否會造成自己以后不被男方珍惜。
然而現實戀愛中,告白并非都是男性,女性告白的也存在,且人數不少。然而女性向男性表白,也確實被某些人視為不值得稱贊的行為,在訪談中有被訪者是這么解釋女性的告白行為“如果一個女性太主動,我就不太會珍惜,你懂嗎,雌性和雄性,雄性就是喜歡享受獵物的那個過程嘛,然后那個女的太主動,讓給我她有點掉價的感覺”。眾所周知我國社會長期以往就以“端莊賢淑”標榜優良女性的形象有關又或以女性就該有較高的道德情操來要定位時有關,這種觀念顯然也限制了女性追求愛情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從告白的結果來看,成功告白與否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有人告白采用高調的方式,導致對方難堪,失敗后,自己也進退兩難。“工作中認識的女同事,她當眾告白我,然后我被拒絕了,后來那女的就離職了,因為天天見,很尷尬嘛。”除此之外,告白行為也受到了個人性格的影響,有人性格比較積極,有的人比較內斂,像“宅男”“宅女”他們自身就不喜歡交際,就算遇到喜歡的也只是暗戀,難以采取行動。正如一位被訪者因為性格內斂,就很難做出告白的行為。“我覺得挺難開口的吧,我就是越喜歡一個人,就越對他表現出冷漠,但是你看不到我的時候,我在后面默默看他。”最后,告白成功與否與個人預設相關,通常人們會預設對方的情感和自己相似,若假設錯誤,就會導致不愉快的結果。正如文中向男同事告白的女同事,必定是認定對方也是對其抱有相同情感,然而卻事與愿為。而消極的一方總覺得對方對自己時冷漠的,從而不曾邁出第一步。
(二)、“我”與他/她的互動階段
1“自己人”邏輯,不滿也會忍
在中國,“熟人”直接作為婚戀的“中樞”,因此,中國年輕之間的“婚戀”生活往往并不是從浪漫開始,而是一個將“外人”變為“自己人”,最后變為“另一半”的人際互動過程。在將伴侶從“外人”真正變為“自己人”甚至“另一半”之前,中國人普遍傾向使用“裝”的角色策略(陽志平,2011)。“裝”會讓對方,在你來我往,相互調情、相互試探的曖昧關系之中,逐步深化關系,然后,慢慢地,對方就從“外人”變為“自己人”直到“另一半”了。而也只有,婚戀雙方不再需要去“裝”,才到了這個“自己人”的婚戀階段。考察新生代農民工戀愛中的偏差行為后發現,青年男女很少向對方表露自己的真實情緒,即使不滿,常常表現出“風度”,或正面的形象,負面的很少。通過這種“裝”,去迎合對方的角色期待。
“交往的時候我一般不對她發火的,我覺得我還是蠻理性的一個人,再說就算我很憤怒,我也會忍著的,控制的,不會在她面前失態。”換言之,這種行為正是一種將對方視為“外人的”體現。這表明他們還都處在在婚戀早期,更多使用的各種“裝”的策略,使自己更符合對方的“角色期望”。
2、一旦無趣就分手
青年男女終于走向下一階段,但又因個人身上具有的不同特質的差異,成功牽手不久,又急速分手。在新生代農民工看“對眼”并不能代表戀情的順利發展,他們在相處的過程中,會進一步追求興趣,個性上的共鳴,若是在這一階段發現興趣不和,個性不匹配,期望不符那就很容易出現一刀切現象,“我還是想找一個跟我有共同興趣愛好的女性和我一起生活,就是因為沒有這個愛好,所以我覺得她很無趣,我就把她否定掉了。”同時他們的感情周期非常之短,短到可以是一個月、一個禮拜甚至一天。
其中造成“短周期戀情”原因包括如下,其一,關系的穩定性和年齡相關,青少年時期人的心智不成熟,經濟能力不成熟,情感不成熟,因此較難以維持穩定的情感交往。其次,青年階段正值人生的機遇期,這是的生活就面臨很多不確定,戀愛自然無法維系,尤其當兩人的生活軌跡不同時,就更難繼續下去,正如上文中的案主,自身不想結婚,而對方確實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從而關系很難維系。其三,角色模糊對于兩性關系的認知,情緒化,過于理想化。文中很多親年都是因為以對他人失去興趣為借口提出分手,這表明他們對婚戀關系并沒有以嚴謹的態度對待,也沒有長遠深刻的思考。
3、若能門當戶對那最好
新生代農民工無論男女大都向往對象和自己的工作環境,興趣愛好,個人背景等方面是相似的。“實際我們男性在挑對象的時候,也看對方背景,也會嫌棄女性窮的,我也不想做鳳凰男,那樣傷自尊,我就是希望找個門當戶對的吧,各方面條件跟我超不多的。稍微低那么點點也行。”
有人要求興趣,嗜好個性相近的。“我是個很注重生情趣的人,所以我希望那個他也能和我在興趣愛好上能夠合得來,然后,我們吃飯的時候就聊彼此的愛好,看看聊得起來不,要是我們話題對不上,自己心里也會減分的。”
有要求教育程度,價值理念,職業類別相近的。“現在我希望我能在工作環境中,找一個合適的人,因為我也不是很看臉的人,最好能在同樣的工作崗位或環境中認識的,這樣我才方便想繼續了解下去。因為彼此既然都在一起工作了,各個方面條件也應該差不多,我喜歡選擇一個熟悉的。從相處中,建立更深層的關系。”
綜上所述這些以門當戶對為訴求的男女們之所以向往門當戶對,完全是為了彼此能在往后的生活中能夠融洽相處,他們一般認為兩人的條件、個性、價值觀、理念、人生規劃同質性高,會有助于將來的溝通,從而產生共同的看法,彼此容易接納,產生一定的共鳴。確實有關調查表明,同質婚的穩定性要高于異質婚,離婚率也相較低。此外,我們看到青年男女在初期更強調精神上的同質性多于物質背景上的相似性。
(三)、原生家庭于“我”的影響
2001年新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條規定:“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愿,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尊重當事人的主觀愿望和婚姻自由的原則,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下發揮著作用,但并非絕對的,更不具備強制色彩,它是自由戀愛的補充。
父母在兒女婚戀中的從主角退居二線,甚至越發不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親子關系的疏離。根據調查發現,一些未婚的男女甚至對于原生家庭更為留念,更為依賴,相處也十分融洽,“其實,我自己也不打算遠嫁,所以同事給介紹對象,我都給拒絕了,我以不想嫁太遠為借口,還蠻管用,我跟家人處的好,舍不得”。“以后找對象我還會考察她對家里的父母孝不孝順”。父母對兒女是一種出于愛的擔憂,包容與尊重。兒女則是秉持對自己對家人負責的態度,謹慎挑選對象。正因如此父母才會“催婚”但無論如何,子女幸福,平平安安是父母的期望,為人子女的也希望父母,身體健康,安享晚年。
因此現代人們通過父母包辦,也只是通過找尋合適對象,其本質仍是自由戀愛,而現實中也確實有那種父母催就隨草草結婚的人,筆者只能建議三思而后行。婚戀非兒戲,對自己負責,才能對他人負責。另一方面父母也要多點體諒與尊重,融洽溝通,共同面對人生。
小 結
社會學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漢斯佛萊德·凱爾納(Hansfried Kellener)對婚姻與社會實體的構建問題做出研究,他們指出,婚姻是兩個人從面對不同的自我,他者和世界,轉而面對協商各自的自我,他者和世界,以獲取貨重建嶄新的意義;這是建立知識的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 of knowledge)。兩個不同的人進入一個婚姻關系,連個人的身份都增加了。婚姻可以被看成是“規范的工具”(nomic instrementiality),當事人不僅進入新的社會角色,也是進入新的世界,兩人的共同世界。其中規則是兩人間的約定俗成。但在中華文化中,我們仍可以聽到一些父母涉人子女擇偶過程中的故事,有些父母替適合年齡的子女征婚介,紹相親對象,尋找交往對象的例子。這如目前東方衛視制作的一檔《中國式相親》的第幾相親交友節目,節目父母兩代同臺,突破“代際沖突”新切口,實現婚戀問題中兩代人共同討,婚戀觀,擇偶標準等,致力男女于雙方能一并順利相親成功。但筆者強調的是:真正和伴侶共度余生的是子女本身,父母出現的意見,或是下的決定,不見得適合子女。父母雖然擔心子女的婚事,也要尊重子女的相法,不要喧賓奪主,因為今日的社會已不是由“父母之命,媒約之言”決定婚假對象,而是要讓子女做決定,決定誰才是資源平等對待,共同奮斗的伴侶。
參考文獻
[1] 孫中興, 《愛情社會學》, 人民出版社,2017
[2] 翁恒盛, 許孟琴, 《婚姻與家庭》,心理出版社,2002
[3] 潘允康, 《社會變遷中的家庭》,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4] 潘允康,《論自由擇偶》,《青年研究》,2002年第5期
[5] 李銀河,《當代中國人的擇偶標準》,《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