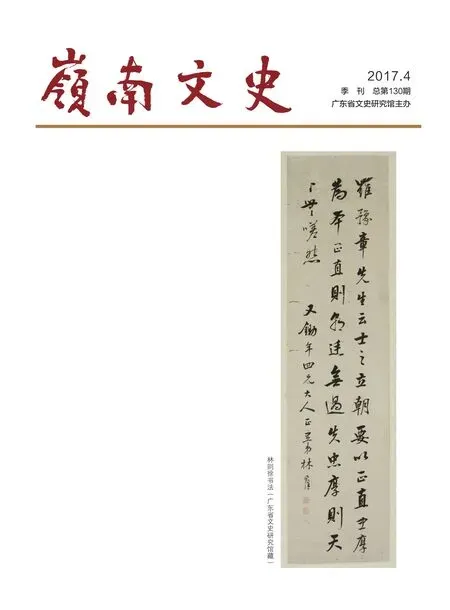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比較研究專題調研座談會綜述
本刊編輯部
2017年4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調研組前往安徽開展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比較研究專題調研,在黃山市(古徽州),考察了墨、茶、硯等企業,在宣城市考察了當地的造紙業,在涇縣考察了查濟古鎮。4月19日,調研組在黃山市召開專題調研座談會。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麥淑萍、館員徐南鐵、鄭楚宣、徐春蓮、區鉷、張國雄和安徽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劉江穎,館員方利山、汪柏樹,黃山市政府副市長陸群、黃山市文化委主任胡建成等出席了座談會。與會領導和專家學者就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的異同、特色和相互借鑒等問題開展研討。
與會領導和專家們認為,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各有特色,可以相互借鑒。文化的比較不是比優劣,而是研究其文化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社會發展的軌跡,文化精神的內涵,以及這些文化特質帶給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人們以新的視角分析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的異同,在比較中定位更準確,認識更透徹。兩地兩館專家學者共同探討粵商文化與徽商文化的差異和發展進程,通過對比了解粵商文化和徽商文化兩者的成就和異同,找到共同的規律,從地緣條件和歷史興衰中把握商業文化的發展脈絡,以及這些商業文化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從而從文化的角度對粵皖兩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是很有意義的。

徐南鐵認為,徽商和粵商的文化精神有共性。比如,本份、善良、積極、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善于開拓,用于闖蕩。徽商少小離家討生活,粵商背鄉離井遠涉重洋,廣東籍的華僑遍布世界,敢于向外發展。徽商精神作為中國商幫的傳統受到大眾景仰。粵皖商業文化的不同比較,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一是不同地域環境的影響。安徽是內陸省份,徽商的主要產生徽州更是處于皖南的崇山峻嶺之中。盡管眼光和腳步受其所限,徽商還是從皖南山區出發,沿新安江一路開拓。走到了山外的徽商,勢力直達江浙滬,尤其是上海、杭州,影響遍及全國。而粵商則背負五嶺,面向海外,因而他們受歐風美雨影響較大,視野有所不同。二是不同歷史傳統的影響。清朝曾有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的政策,在這種歷史環境中成長的粵商習慣于跟外商打交道,密切關注中西商業的態勢。所以當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商業的熱點向上海遷移時,即有大量廣東人涌向開埠之初的上海,形成早期開發上海的重要力量。如上海的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符合市民階層發展方向,卻都是廣東人開創的。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徽商沒有與這種大勢形成如此緊密的關聯。三是不同文化品格的影響。三大外來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進入中國,都是在廣州登陸。中國最早的現代報紙,中國第一位留學生,都產生于廣東。廣東的商業文化也明顯帶有異質文化色彩。即使在近半個世紀,皖粵在文化方面也有明顯的不同。如1978年,安徽的小崗村自行分地,成為改革的先聲;而廣東的大進制衣廠則以“兩頭在外”的方式,開啟開放的歷程。徽商鼎盛時期,與官府聯系緊密,胡雪巖是著名的“紅頂商人”。這與徽州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讀書做官觀念是相通的。但是粵商與政治文化中心的聯系相對疏離,更多一些對現代商業精神的崇拜。地緣、時代、文化精神的差異形成了徽商與粵商的不同,做較為深入的文化比較,可以讓我們理性地分析和認識自己,并有所揚棄,從而對社會的未來發展產生積極的意義。

汪柏樹認為,徽商富有愛國主義精神。1949—1950年的屯溪當代徽商,是踐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努力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并為此作出重要貢獻的徽商。1949年5月,屯溪市人民政府成立,屯溪轉型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國家的公營經濟成為經濟領導力量;95%以上的徽商業戶皆參加了以貫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為宗旨的市工商聯合會(含其籌備會)及其下設的各行業公會,這是屯溪徽商轉型為當代徽商的時代條件與主要標志。屯溪市工商聯和徽商各行業公會,根據“勞資兩利”方針,正確處理徽商內部的勞資矛盾關系;根據“公私兼顧”原則,正確解決外部的公私矛盾關系,為徽商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創造正確前提。1949-1950年的屯溪當代徽商群體是城鎮就業的主力軍,積極繳納稅款,踴躍購買公債,努力捐助各項公益事業,籌款興辦學校,支援抗美援朝,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及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
方利山認為,宋代以后開始初具特色的徽州文化,以其豐厚積淀和巨大張力,孕育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光彩奪目的徽商;而在明淸時期事業達到鼎盛的徽商,又以自己的強大經濟基礎和突出的聰明才智,實現了徽州文化的全面杰出與輝煌。“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復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系的地域商幫,與晉商、粵商、龍游商相比,自有特色。有較髙文化素質的徽商,“賈而好儒”,將儒、官、商進行了靈動的協調,交替為用,以儒飾賈,以仕護商,以商促仕,在長三角這一得天獨厚的大市場里首先創出一片天下,進而在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大顯身手,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聲望。徽商既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又是一個特定人物群體,更是一個時代創新篇章, 因而也是一份寶貴歷史遺產。徽商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產生、崛起、興盛和逐漸從頂峰消退,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必然出現,這樣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演進,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又和中華傳統文化大背景、和長三角歷史地理條件緊密相關。我們要堅持聯系地、全面地、本質地看問題,盡量避免孤立地看問題,盡量避免表面性和片面性。
區鉷認為,商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的基礎是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徽商被稱為“儒商“,是因為徽州地區的文化特色就是愛書重道。粵商主要是指廣東商人。大部分廣東人的祖先是不安于現狀的中原人,在中原不得志,南遷至廣東。在廣東如果仍然不安于現狀,就向海外發展,所以粵商文化是外向型的,而且敢為天下先。當年明清朝廷都曾實施海禁,可是粵商就敢組織武裝船隊出海經商。外貿是粵商重要的業務,清代十三行遠近聞名。粵商因為要和外國人打交道,所以在翻譯這一行業中也是先行者,以至于英國人在《南京條約》中專設一條,要求清政府不得追究曾為英國人提供過翻譯服務的中國人。粵商文化的基礎是嶺南文化。嶺南文化向來有務實的傳統。這一點從嶺南文化的代表人物趙佗、冼夫人、慧能、洪秀全和孫中山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慧能的頓悟說、洪秀全的基督教中國本土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就是很好的例證。正因為粵商文化有務實的嶺南文化為基礎,才會有粵商的開發、開拓行為。粵商文化的短板是傳統文化底蘊不夠深厚,這一點應該向徽商學習。歷史上商人是士農工商中最低等的人,連科舉考試都不允許參加。盡管在清代粵商有過輝煌的日子,但反映粵商文化的文學作品極少。目前比較有影響的是小說《蜃樓志》,但對其研究不多。
鄭楚宣認為,徽商文化可供粵商借鑒學習。一是誠信為本,以義制利。徽商“賈而好儒”、信儒、行儒,堅持誠實守信、以義制利的商業道德,支撐了其幾百年經久不衰的光輝業績和崇高信譽,這對于我們今天糾正市場經濟的一些失信行為,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二是善于了解、把握和運用政府政策。徽商比較重視政治,非常注意處理好和政府的關系,并通過政府了解政策走向,善于把握和運用政策來確定企業發展方向和經營方式,從而促進了成功。相對而言,粵商由于太務實,太注重經濟而忽視政治,總以為政治太空、太虛,不可捉摸,而不愿多花時間去了解、把握國家政治和政策走向,從而影響了其對企業發展方向甚至管理方式的正確決策。三是注重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質,合理選用人才。合理選拔和使用人才,對人才注重德才兼備、放手使用、各盡其能,培育一支思想文化素質較高和經營管理能力較強的人才隊伍,這是徽商成功的一大要素。而粵商受廣東“重富不重貴”的傳統影響,加上由于改革開放初期“英雄不問出處”、“殺出一條血路”特殊的國情省情,在廣東造就了很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水平的富豪,粵商不大注重自身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同時,粵商選用人才也是一種較典型的實用主義,總認為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市場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以致缺乏選用人才方面較為長遠的戰略眼光,不注意培養、儲備有發展潛力的人才。所以,粵商應多向徽商學習。
張國雄認為,粵商、徽商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影響的商幫。兩大商幫大致都是在宋代開始活躍,徽商的全盛期在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期,粵商則自宋后至清末民國一直興盛,至今仍為中國對外貿易之重要力量(華商)。徽商主要馳騁于國內市場,山貨、糧食、木材、茶葉等商品行銷全國,最后發展到以鹽業為代表而達到鼎盛。粵商因中外貿易而生,主要征戰于海外市場,華商群體和企業百年老店至今不倒。粵商、徽商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貿易發展最活躍的民間力量。徽商重儒,商貿經濟實力的積累轉化為徽州文化的發展動力,促進了徽墨、宣紙品牌的樹立,暢行天下。粵商勇闖天下不忘文化傳播,將嶺南武術、粵劇、粵菜、粵方言以及風俗習慣等帶到了東南亞、北美、澳洲,成為這些地區民眾眼中最早的中國文化符號。弘揚中華文化是粵商、徽商共同的傳統。“一帶一路”倡議的互聯互通,從資金、政策、基礎設施、貿易到民心相通的實施,都離不開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群體。在交流、互鑒中講好“中國故事”,民營企業群和商人群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新機制,給予華商和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更加廣闊的空間。繼續發揮好粵商、徽商的文化傳播功能,必將極大地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