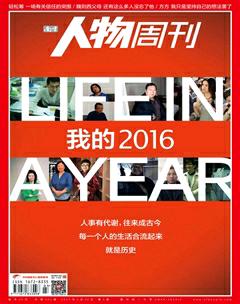淡豹 該好好說話了
《給未來的女兒》
2016年11月的第二個周二,編輯給了我一封讀者來信,內容是遭受性騷擾該怎么辦。很好回。我不要寫找派出所、找朋友那些規范化的方式,想鼓勵她一下,世界不會永遠這樣。當時在草稿里寫,希拉里當選了,你要看到婦女運動史上特別重要的一步。那時候對希拉里會當選一點疑問都沒有,太確定了。我看著比爾·克林頓的照片,想著他就是第一先生了,挺好。

但是周三,特朗普當選。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人類學博士剛畢業,住在紐約。我們一直聊天,非常崩潰,其中也有幾秒我意識到回信白寫了,但不是說負擔,而是覺得自己之前寫得好可笑啊,世界怎么會變成這個鬼樣子。
那天,我和朋友一邊看大選,一邊也在看Steven Cobelt 的直播脫口秀。我倆的共同愛好是看美國政治脫口秀,諷刺那些政治保守的落后的政治人物,以及相信他們宣傳的人。大選結果出來以后,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是,突然間你看了很多年的那些笑話不好笑了。你沒法再以諷刺的態度面對這一切,你以往諷刺的態度縱容了這一切。你對自己這些liberal(自由主義者)自說自話,在智力的愉快里喜氣洋洋,也等于拒絕同情和理解你諷刺的人所面對的困境,它創造了更大的割裂。大洋兩邊的我們倆在微信上討論,到底該怎么樣認真對待自己的寫作和生活。那時候我在想責任感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人,所以寫了篇非常正面的檄文,沒有調侃,沒有繞圈子,就覺得,應該好好說話了。
實際上,來信者的感受很尖銳,性騷擾的問題確實很嚴重。如果所謂很專業化地去給標準答案,那我就喪失了激進性。以中國的廣袤、人口及社會問題的繁多,這樣一個個case(案例)的制度建設,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才會完成。同時,制度建設和立法并不能解決問題。比如公司對女員工遭遇性騷擾出臺的條例,老實說,我不覺得是一個更好的未來。最近騰訊年會的事情,引發社會上的反感和批判后,他們對女員工說對不起。這個道歉是bullshit(胡說),整件事跟女權沒有關系,一個公司的年會搞這種低俗化的游戲,根本是社會淪喪。
有的朋友不能理解我的沮喪,問我為什么這么難過,是不是移民政策有什么問題?我說跟我個人沒什么關系。我在一種崩潰的情緒下寫了《給未來的女兒》,非常長,是完全不考慮閱讀量的寫作。它其實是對知識分子責任、對優越感、對知識上的傲慢的反思,很大程度在談什么樣的秩序是可能的、未來大家怎樣相互理解和溝通。
文章發出后,一些高校的女生社團聯絡我,分享一些想法,我也收到來自個人的私信。很多人覺得受到激勵,我很意外和感動。這種反饋給了我信心,倒不是關于女性,而是關于寫作——寫作確實不需要考慮傳播度。這幾年我比較悲觀,做好了東西,聽的人會聽,不聽的人會不聽。假設我的文章是奶酪,肯定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與其我站在路口,給每個人遞上一塊,不如放著,會有人去拿。這些是真對奶酪有興趣的人。
但是特朗普的事情又讓我有了新的反思。媒體不能自說自話。如果奶酪是好東西,關涉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我們所有人的未來,而不只是有些人愛吃、有些人不愛吃的零食,你的放棄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2016年開始時我是一種心態,到年末又是另一種心態。我還沒有找到方案,2016年全然在困惑中結束。
性別敏感
我在北大讀的社會學系本科、人類學碩士。人類學有很多田野活動,到地方上,師兄會讓你給當地的官員、教授敬酒。我不想敬,還哭過。但當時沒有那種很強烈的性別歧視感。
我對性別的敏感其實起源于在芝加哥大學做交換生的一年。我的田野工作跟木偶戲相關,曾經參加了一個關于中國戲曲形式的工作坊。一次活動上,中國戲曲學院某某系主任來芝大訪學,發表了一個小小的talk(講話)。這位男系主任在講解一個招式的時候,點名一位女職員,讓她當場表演。你很容易想象到他的頤指氣使,這種行為在中國很常見,但在美國,不大可能發生。當時我們在研究室里吃盒飯,女職員沒有想到,也有點不舒服吧,上臺以后說 “這個怎么跳呀”,中國女孩常用這種忸怩的神情表示拒絕,但系主任一定要她表演。她演示完,系主任就說:“小X,你今天怎么穿個牛仔褲,這么緊,動作也做不好。”
那一剎那我很心疼這個女孩子,一方面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面對過的很多事情。在國內時你不大會有意識,因為習慣了。另一方面,有“吾國吾民”的感覺。這事在美國發生, 很多外國教授在場,我會有點這個意義上的羞恥。種族關系的羞辱感疊加著性別關系,所有的矛盾好像都因為這個結構關系尖銳化了。
這事有一個后續。當時我很受沖擊但沒想清楚,沒有反抗意識,會議結束后還是按照慣例,去和那位指指點點、特別討厭的系主任交換了郵箱。我沒寫過信。2009年9月或10月,他給我寫了一封郵件,問:“你是不是從美國回到北京了,我們是不是要吃個飯?”我覺得特別惡心。
報警
我對胡同很感興趣,對北京平房和胡同生活有很多想象。2015年夏天回國,胡同的房子也是我看的第一個房子,我不挑,看了覺得可以,當天就簽了。我沒想住很久,也不是體驗胡同文化,跟去大理住洱海邊、去葡萄牙住海邊一樣,挺新鮮的。要知道有賊我能住嗎?
事情差不多發生在凌晨一兩點。被我發現后,那個人跑了,我打電話報警。我在廚房,聽見有人弄門的聲音,他又回來了。這是我最害怕的時候。我問警察到哪里了、什么時候來,110那邊說:“已經安排了,你就等著吧,別著急。”我問能不能查一下,她說:“咱們倆說話呢,看不著,你得掛了我才能打。”沒有接警規范,完全是特別大媽式的、不耐煩的回復。
到了派出所,他們也不給我立案,在我要求下還是立了。立得很不愉快,他顯然沒有按照你的回答去修改記錄,就讓我簽字。我說,你這根本不是我說的話呀。比如他問我有什么損失,我跟他講,那人后來回來了,顯然是不怕我。但是我看著他的電腦屏幕,寫的是“沒有財物損失”,他在乎的是這個。
我在美國也遭遇過搶劫,但是當時就抓到了人,當晚我跟著去了警局。后來出庭,我還去做了證人。警官留了私人電話,說有事你再打來。整個流程很利落,挺長見識。我挺感興趣北京這邊的流程,所以問朋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應該怎么跟進。他說,你去派出所,找人家副所長,天天纏著,人不會主動找你的。我后來實在跟不起了,田野工作就到這為止。
我也考慮過棚戶區那篇文章要不要講這些,后來覺得沒必要。我在朋友圈寫過110的接警規范問題,因為這是報警中心的培訓,是有可能推進的一個進步。但是破不破得了案,跟警察資源、國家任務都有關系,寫進文章也推進不了任何東西。我是一個政策上的實用主義者。
左翼理想
我真的希望可以寫出好的東西。那種高興感會讓我停止沮喪很久。
2016年初到媒體工作以來,我的個人生活沒多大改變,閱讀、寫作,以前創造沒啥價值的論文文本,現在創造沒啥價值的別的文本。整個世界的向右轉是我這一年里最大的感觸,讓我想要更好地做一個知識人。聽起來可能有點高蹈,但確實是我的想法。作為一個知識人,你應該考慮怎么去生活、去寫作。這種生活并不是指個人的幸福。
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在本校讀研,我覺得跟外校考來的人玩不到一起去,有點像大學里的北京小孩和外地小孩。但是現在,我反而和研究生同學比較有共鳴,因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走上了學術的道路。學社會學、人類學的人幾乎沒可能不左翼,因為肯定會關心平等問題,不太容易走到文化保守主義或中產階級的精致生活。
我很喜歡一位北大畢業的詩人王璞,他在一個訪談里說,我們之所以虛無是因為當代史的無效。他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很深。有首叫《寶塔》的詩,結尾說:“它可以是毛茸茸的,果味兒的,熒光的。但首先是紅色的。”意思在于,你的理想或生活方式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態,但它首先應當是革命性的,是左翼的。
我們這代人經常陷在虛無中,一種表現形式是:保衛或珍惜自己的精神生活,放棄公共生活。職業生活給自己提供物質保障,私人生活提供朋友和快感,個人與社會、工作與內心都是割裂的。這既是很多知識青年對現實失望的后果,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結果。
假如說我在年末的困惑中有什么收獲,是這個想法:我們可以孤立地在書齋中寫作,可以在工作中努力,但是無論如何要激進一點,要有左翼理想,要有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求。這與《給未來的女兒》想法一致。每一個人在自己能夠接受的范圍內、在社會生活空間里結合自己的生活理想,去承擔某種責任。如果你是女作家,你可以不只寫文學規定或認為女性應該寫的內容,一個公司職員可以敢于讓自己更成功。同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聲,提醒大家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希望大家都意識到自己遭受的東西。但我不只關心性別,社會公平的各方面我都挺關心。
幾年前,有一個叫作“淡豹全球后援會” 的ID老在我微博上留言,吹捧我。我說我很不舒服,你把名字改掉吧,我不想成名。那個人就改掉了。可以看得出來這不是組織,就是某個蠻開心的讀者搞了這個事。到2013年春節的時候,有人問我記不記得這個事。他說那個“后援會”是一個江西學生,19歲,文藝青年,到杭州打工,搞空調安裝,聽Pink Floyd看One,很喜歡我的文章,會推薦給他江西老家的朋友,這些朋友基本也在各地打工。小男生從杭州回江西家里村子里過年,他們約好到縣里唱K。晚上他戴著耳機走路,發生了車禍,就在去KTV的路上。他的朋友給我發信的時候,這個男生已經不在了,搶救了幾天。發信的孩子說他朋友生前很喜歡我,所以取了那個ID,他覺得應該告訴我這件事。
我當時哭了幾天。因為我從來沒覺得自己的寫作能對別人產生影響。我那時候還在美國,和幾乎不可能認識的人通過文章有了交流。我想不要很諷刺性或者輕薄地對待寫作 ,還是得認可它的可能性,它確實是一個交流的媒介。他的去世是悲劇和偶然,但他和我的關系完全是積極的。我覺得自己蠻幸運,如果我的文章曾經讓他開心過,我也蠻高興。我應該好好寫,不應該輕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