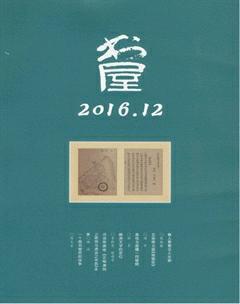書屋絮語
讀完旅美學者傅鏗著作《煙雨鄉(xiāng)愁》時,對“鄉(xiāng)愁”二字有了別樣的理解:一是地理上的鄉(xiāng)愁,長駐異地他鄉(xiāng),對故鄉(xiāng)的思念和舊時人事穿越時空,會在不經意處涌現(xiàn),漫漶成一片。二是文化的鄉(xiāng)愁,文化如血脈貫通,與呼吸共永。文化是根柢,抽離不得,稍有晃動,形態(tài)失真,而且會聯(lián)動到思維與語言,須臾不可分。三是“中國情懷”的鄉(xiāng)愁。遠離故國,在中西文化會通之中,對于國別身份和文化寄存之間,始終不忘祖,文化情結與心靈歸宿俱在。“所謂‘中國情懷其實便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情結。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蘇武書》所謂‘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癥結”。
作家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雖未讀,但標題的意旨頗令人回味。人最斗不過的是時間,最害怕的也是時間,一分一秒都在耗費你自己的生命,這是不可復制的歷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確豪情萬丈,勇氣可嘉,然何嘗不是一種對時間的抗拒,一種對俗世的反拔?誰都恐懼被時間“軟埋”而無生氣。美國作家、一生都堅持用中文寫作的韓秀新著《尚未塵封的過往》跨洋而來,“塵封”二字與“軟埋”恰相呼應,仿佛這一年文學的主題詞。表面上看,韓秀在“塵封”二字設置了前綴“尚未”,似乎樂觀些,但通讀全書,面對逝者如斯,唯有震驚;一切終將塵封,故事腐朽。
我非常喜歡韓秀著作封底的一段推薦性文字:“在傳統(tǒng)的文人日漸凋零,紙本的書信往來也幾乎被及時的網絡通訊全面取代之際,昔日那種藉由尺牘言志傳情的筆墨交流,以及在魚雁往返的等待中,隨著時間的發(fā)酵而益顯可貴的溫厚人情,早已湮沒在速食文化的洪流中不復追尋,而隱藏在書信背后的諸多文林往事,隨著物換星移而鮮為人知了。有感于此,作者緣自親身經歷,從自己的記憶出發(fā),在數(shù)十年來累積的大批書籍、剪報、信夾、日記和筆記等資料中奮力跋涉,為讀者解讀層層密碼,重現(xiàn)幾位文壇耆宿的風范,以及他們晚年生活的點滴。”尺牘“言志傳情”代表著人事的熱度;過往的記憶代表著“溫厚人情”,而我們確在其中,以史為鑒。
而后,讀過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黃仁宇《明代的漕運》、許倬云《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以及郭娟《紙上民國》幾種,這些都可歸于文化或“中國情懷”鄉(xiāng)愁的一類。同樣,我們對于歷史、文化、人物和事件都懷有很深的敬意,事實存在,小子不敢言語,唯有緘默而懷想。張君勱說:“……如果中國去了解西方如去了解佛教一樣,那會有一種接納的心靈、一種友誼的反應,此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實際上,整個十九世紀在政治上、社會上西方對中國的沖擊與在文化上和精神上西方對中國之沖擊,同樣是毀滅性的企圖。它要求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被擱置下來,或甚至失去其自身之同一性。那就是為什么學者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采用一種一廂情愿的、以博物館中死物為材料所需要的研究方法。結果本當友誼地合作和樂意接受的地方,竟以敵對、破毀,以及抵抗的態(tài)度對待之。”
(邵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