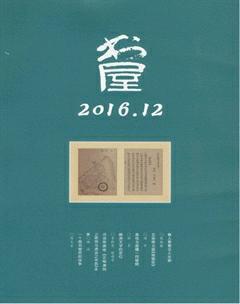從“情何以堪”到“愛(ài)何以立”
秦燕春
《青瓷紅釉》定稿于2009年暮春,初版于2010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而實(shí)則自始至終,這本書(shū)唯一的正確的定位與命名,只能是“立愛(ài)”。從“情何以堪”(是書(shū)出版序言)到“愛(ài)何以立”,期間的過(guò)渡或者可以是“情何以立”?這是本書(shū)現(xiàn)在的修訂版試圖完成的愿景。最終完成與否,交于讀者裁斷。
因是書(shū)之寫(xiě)作完全出于約邀,初始動(dòng)筆純是基于完諾。所寫(xiě)甚苦,蓋談情說(shuō)愛(ài),準(zhǔn)風(fēng)月談,早非2009年之筆者關(guān)懷愿力所在,而窮透“情”之本質(zhì)、布露“愛(ài)”之本色,又非彼時(shí)之筆者力所能及。直到全書(shū)寫(xiě)作進(jìn)行到三分之一,“立愛(ài)”的骨核概念被硬生生寫(xiě)出到光明地,是書(shū)展開(kāi)的動(dòng)力方才飽滿,之后的部分是以一天一萬(wàn)字的速度完成。代價(jià)是書(shū)稿殺青后作者病倒一月,無(wú)論如何都不肯好,而在之前我是二十年沒(méi)吃過(guò)一片藥、強(qiáng)壯活潑如小鹿的人。
是“立愛(ài)”自己要走進(jìn)世界。
自古皆有死,人無(wú)信不立。傳統(tǒng)中國(guó)關(guān)于“而立”的倚重,透底只是生命的擔(dān)當(dāng)與承荷。素凈而自然。“立愛(ài)”首出之典藏是《尚書(shū)·伊訓(xùn)》,“立愛(ài)惟親,立敬為長(zhǎng),始于家,終于四海”。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此意在《禮記·祭義》中又被孔子闡發(fā)為“立愛(ài)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zhǎng)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
然即令今日,我落筆拈出“情何以立”作為再版修訂補(bǔ)入諸文中論牟宗三先生“情觀”之春苦悲覺(jué),亦完全不在有意設(shè)計(jì)當(dāng)中,亦完全是第二次的“主題”主動(dòng)現(xiàn)身、走進(jìn)世界。
2015年歲中,這本書(shū)又帶來(lái)一位更其意想不到的讀者與朋友,東亞儒學(xué)與臺(tái)灣儒學(xué)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臺(tái)灣新竹清華大學(xué)的楊儒賓教授,偶見(jiàn)拙作,謬獎(jiǎng)不已,以為能傳儒門(mén)人世水深土厚之微言大義,鄭重勉勵(lì)者再三。楊教授給出讓筆者心動(dòng)神往的理由,如果唐君毅先生或牟宗三先生生前得以見(jiàn)及此類“情書(shū)”歷史書(shū)寫(xiě),當(dāng)有一會(huì)心處。
紅塵滔天,人海蒼茫,我之筆墨的確慣寫(xiě)小女柔情、閨閣風(fēng)花,且每每能得真味之詮。此點(diǎn)優(yōu)長(zhǎng),亦可當(dāng)仁不讓。然于中能否見(jiàn)及曠代大儒“家國(guó)天下族類之感”這等宏業(yè)?筆者不才之木,卻也心向往之。故盡管是書(shū)初版檔期過(guò)后、再版邀約幾度出現(xiàn),主客原因皆有而均未能落實(shí)。這一次,很大程度基于前輩學(xué)者的首肯,筆者方鄭重考慮其再版。
筆者私意確也認(rèn)定,至少在中國(guó)古典學(xué)術(shù)視野中,最好而根本的學(xué)問(wèn)書(shū)寫(xiě),都該是“情書(shū)”。中國(guó)“情性論”所涉問(wèn)題極廣,即涵上求情性起源,亦需研習(xí)情性關(guān)系,更要涉及性與習(xí)、性與天、心與情性、理與欲等同族相關(guān)范疇。“情”作為包含各種情緒、情感在內(nèi)的集合名詞,其出現(xiàn)與被討論的時(shí)代絕不太晚。中國(guó)文化某種層面常被視為“情”的文化。“發(fā)憤抒情”(《惜誦》)成為屈原創(chuàng)作的力量源頭乃至中國(guó)文學(xué)的力量源頭。
因?yàn)榘l(fā)自人性對(duì)秩序與和諧的渴望或需要而同時(shí)又在試圖掙脫或超逾秩序與和諧,亦緣于漢代以降“獨(dú)尊儒術(shù)”的基本政教格局形成,“情”在后世中國(guó)的思想行程可謂起起落落、異常曲折。大致說(shuō)來(lái),在佛、老的論述中,“情”是妨礙體道的負(fù)面因素;但在儒家的系統(tǒng)中尤其在陸、王心學(xué)的體系中,道德畢竟需要透過(guò)道德情感顯現(xiàn)出來(lái),道德情感被視為心靈的主要內(nèi)涵,是人類結(jié)構(gòu)中先驗(yàn)的因素。“情”具有不可化約的價(jià)值。在無(wú)情、怯情、化情、重情諸多主張中,儒家支持的多是“重情”論。儒教因此成為性情之教,“情性論”成為儒家哲學(xué)最為重要組成部分。通大道、測(cè)情性成為圣人所以為圣人的標(biāo)志。道、情兩端為亙古大義,道至情達(dá)則是。大道關(guān)乎變化以應(yīng)對(duì),情性系乎明理于取舍。對(duì)于側(cè)重經(jīng)驗(yàn)性與人間性的儒者,既然“道始于情”、“禮作于情”、“文起于情”,比“復(fù)性滅情”這類逆向而生更重要的或更妥當(dāng)?shù)穆窂健?dāng)然該是“因情”、“稱情”、“養(yǎng)情”……之“情教”種種。
而“情”要表現(xiàn)(知情者出之),這被視為“道”展開(kāi)的可能。今儒中的有識(shí)有志之士認(rèn)為深受佛、道傳統(tǒng)影響的中國(guó)修行傳統(tǒng)對(duì)“情”未免多持否定,盡管精微如唯識(shí)宗亦能夠深入精研意識(shí)各種變形,卻對(duì)“情”的展開(kāi)不夠重視。晚近學(xué)界于“情”的諸面相稍能推介,與存在論的出場(chǎng)與本質(zhì)論的黯然這一西學(xué)轉(zhuǎn)型(認(rèn)識(shí)論轉(zhuǎn)向)直接相關(guān)。然中國(guó)語(yǔ)境下的“情性”,是否能夠以存在的面相與本質(zhì)的實(shí)存盡之,如何能夠在“日盡其性情”當(dāng)中踐行超越,依然任重道遠(yuǎn)。
如此“立志”、“立情”,可謂高遠(yuǎn)博厚之選。只是筆者小才微善尚屬不能,竟能試以“情史”小用,而明、而證、而藏此經(jīng)天緯地之“情本體”乎?程朱學(xué)者有謂,“仁者,心之德,愛(ài)之理”,毋寧可以將“理”、“愛(ài)”關(guān)系理解為“理”為其體,“愛(ài)”為其用。而“情”居其間、乃成為發(fā)散這一“全體大用”之殊相的可能性?
請(qǐng)?jiān)囈允菚?shū)修訂版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