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絲綢中的龍鳳合體造型探析
張 慶, 方 敏(.江蘇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江蘇 無錫 453;.蘇州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 蘇州 53)
歷史與文化
楚國絲綢中的龍鳳合體造型探析
張 慶1, 方 敏2
(1.江蘇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設計學院,江蘇 無錫 214153;2.蘇州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針對楚國絲綢紋樣中存在的一些龍鳳合體造型,以類型學將這些紋樣進行分類,通過追溯這些紋樣的形態,結合從先秦文獻中歸納出的天文學原理,以及楚王族祖先的職業等要素,分析了其中的象征意義。研究表明,楚國絲綢中的龍鳳合體造型是楚人對當時天文學原理的描繪,屬于天體崇拜范疇,并非圖騰的概念,鳳紋是楚國在天文學中對應的分野,龍紋則是作為鳳的交通工具出現的,這也是龍鳳合體的主要原因。
楚國;絲綢;鳳紋;龍紋;天體崇拜
在當前出土的楚國絲綢中,出現了大量造型生動的圖形,其題材、造型、材質等均富有特色,可謂填補了中國東周時期絲綢紋樣的空白。在這些紋樣中,尤以龍紋、鳳紋的數量居多,因而學者們常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此類紋樣之中,如彭浩[1]在《楚人的紡織與服飾》中用大量的篇幅羅列了楚國絲綢中的各類龍、鳳紋,伏兵[2]在《楚文化中鳳的造型》對楚國絲綢刺繡、青銅器中鳳的造型特點進行了全面分析。不可否認,龍紋、鳳紋是楚國絲綢中造型獨特的紋樣類型之一,其樣式多變,不僅外形各異,更有寫實、抽象之分,營造出了風格多樣的紋樣群。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圖騰崇拜理論的影響,張正明[3]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尊鳳貶龍的觀點,認為鳳紋是楚人的圖騰,因而導致楚國的龍紋被之后的學者所忽視。大多數學者在研究楚國絲綢紋樣時側重于鳳紋,對龍紋的研究較少,更是忽略了楚國絲綢中龍鳳合體的造型。這些龍鳳合體的造型樣式極富地域特色,在其他諸侯國的紋樣中并不多見。鑒于楚國王族曾經是負責觀象授時的天文學世家,本文以先秦時期的各類文獻為基礎,通過還原楚人心目中的天文學理念,了解楚人的精神世界,同時分析龍紋和鳳紋的關系,力求理清這些龍鳳合體造型的象征意義。
1 楚國絲綢中龍鳳合體造型的類型
楚國絲綢中所出現的龍鳳合體造型各異,風格多樣,龍、鳳的形體特征均在其中得到了生動的表現,有的龍鳳身體相蟠,有的龍鳳首尾相接,還有的龍頭鳳身,反映了楚人不拘泥于成法的造型技巧。總體來說,按照考古類型學,楚國絲綢中的龍鳳合體造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龍鳳身體相蟠的造型,第二類是龍鳳共用同一身體的形態,第三類是龍頭鳳身的樣式。

圖1 九店東周墓刺繡紋樣Fig.1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Jiu Dian tomb of Eastern Zhou
第一類龍鳳身體相蟠的造型多出自戰國時期靠近郢都的楚墓中,如包山楚墓、馬山1號楚墓、江陵九店東周墓等,在其他地區并不多見。在此類紋樣中,鳳紋幾乎都是畫面的視覺中心,側面描繪的形體大多數較為完整,呈展翅欲飛之狀,具有細頸勾喙、長足利爪的特征,尾部多為魚尾狀;龍的外形細長而婉轉,蟠繞在鳳的身體上,動態十足,最終形成一幅完整而生動的圖像。在這些紋樣中,龍的數量一般多于鳳,其樣式多變,既有雙龍共身的雙頭龍,如江陵九店東周墓中所出刺繡(圖1);又有單尾的單頭龍,如包山2號楚墓所出的一鳳三龍相嬉紋樣刺繡(圖2)。同時,龍的表現形式亦有寫實與抽象兩種,有的龍細節清晰,龍頭、龍身的描繪十分細致,如馬山1號楚墓所出的龍鳳相蟠紋繡(圖3);有的則將龍頭簡化為箭頭狀的圖形,龍眼、嘴等均被省略,具有代表性的是馬山1號墓所出的一鳳三龍相蟠紋繡(圖4)。

圖2 包山2號楚墓刺繡紋樣Fig.2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Bao Shan No.2 Chu tomb

圖3 馬山1號楚墓刺繡紋樣Fig.3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Ma Shan No.1 Chu tomb

圖4 馬山1號楚墓刺繡紋樣Fig.4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Ma Shan No.1 Chu tomb
第二類是龍、鳳共用同一身體的形態。這種樣式目前在楚國絲綢中僅見于戰國時期馬山1號楚墓所出的一龍一鳳相蟠紋繡(圖5)中,其中的龍、鳳共用同一身體,龍頭長嘴外張,龍身細長而蟠曲成“8”字形,勾喙的鳳頭位于“8”字形內側,與細長的龍身相接,整個造型十分生動,以婉轉的曲線巧妙地將龍鳳合成一體。類似的紋樣在楚國其他材質的器物中經常出現,如春秋晚期曹家崗5號楚墓所出彩繪漆木瑟中就多次出現過這種裝飾紋樣,戰國中晚期九連墩楚墓中也發掘出了龍頭鳳尾的玉佩(圖6)。可見,此類紋樣在出土的楚國絲綢中雖然屬于個案,但是它普遍地出現在其他材質的楚國器物中,足見其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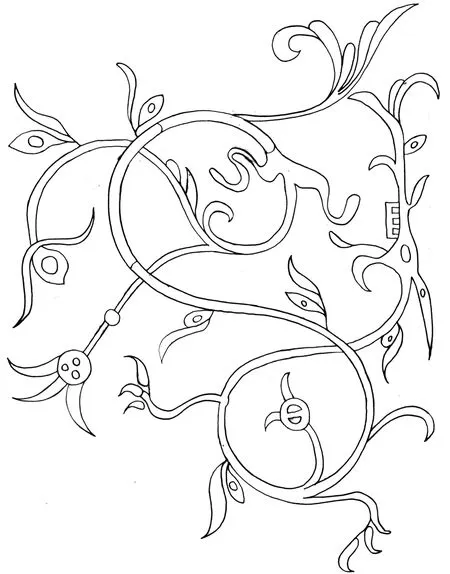
圖5 馬山1號楚墓刺繡紋樣Fig.5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Ma Shan No.1 Chu tomb

圖6 楚國漆器、玉器中的龍鳳合體紋Fig.6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dragon pattern with and phoenix pattern in lacquer ware and jade of Chu State
第三類是龍頭鳳身的造型,此類紋樣在楚國絲綢中所出的數量不多,在馬山1號楚墓、長沙烈士公園3號墓中出現過兩種樣式,但它們在楚國絲綢中屬于特色鮮明的紋樣類型,具有龍頭、鳳身、長足、鳥爪等特征。紋樣的腿部造型與同一畫面中鳳紋的腿部幾乎一樣,不同之處在于其頭部變成了龍頭形,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亞類。第一種亞類的龍頭呈三角形,無角,但頭上飾有較長的花冠,與鳳紋頭部的裝飾相似,爪抓藤蔓,口銜藤蔓上的花,鳳形身體上的翅膀被省略掉,如圖7(a)所示;第二種亞類的龍頭上出現了優美的鹿角形角,仍然飾有一根較長的花冠,鳳形身體整體布局呈“S”形,被描繪成兩個側面,其中一個側面與龍頭直接相連,另一個側面是鳳身及翅膀,細長的鳳足上均有利爪,最終形成了奇特的紋樣形式,如圖7(b)所示。

圖7 長沙楚墓中刺繡紋樣Fig.7 Embroidery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Changsha Chu Tomb
2 商、西周時期的部分龍鳳合體造型
要弄清以上三類龍鳳合體造型的來龍去脈,首先要追溯龍、鳳在同一個畫面中出現的圖像。縱觀先秦時期的紋樣史,龍鳳合體造型曾經在商代普遍流行的“獸面紋”中出現過。關于商周時期“獸面紋”的組成,本文支持張光直[4]、阿城[5]提出的“獸面紋”是在表現人形神駕雙龍的說法,這與《山海經》中經常出現的神人駕兩龍的描述完全一致。
從商代晚期開始,“獸面紋”中就已經出現了龍、鳳在同一個畫面的場景,它們經常都是圍繞一個雙臂微張的神人為中心組成對稱狀的畫面,如在商代晚期父辛尊腹部的裝飾紋樣(圖8)中,侈口外張的雙龍圍繞中間的神人呈對稱狀布局,雙龍兩側的下方各有一只神情自若的鳳紋,雙龍及雙鳳的特征十分清晰。在湖北院墻灣楚墓中所出的戰國時期楚國玉器中也有相似的造型(圖9),人形神、雙龍、雙鳳均以寫實的手法進行表現,其造型、構圖幾乎與商代“獸面紋”一致,不同之處在于鳳紋所出現的位置稍有差別。荊州博物館整理的考古簡報中稱其為神人操兩龍形佩[6],這件器物的出現對于梳理商周紋樣的發展脈絡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是沒有被廣大學者所重視。

圖8 商代青銅器中龍紋與鳳紋同時出現的畫面Fig.8 The pattern which contains dragon and phoenix in Shang dynasty bronzes

圖9 楚國玉器紋樣Fig.9 The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Jade in Chu State
龍鳳共用同一身體的圖像也曾經出現于商代晚期青銅爵腹部的裝飾紋樣中(圖10),龍、鳳共用同一身體的圖像圍繞人形神呈對稱狀布局,龍頭朝向中間的神人,鳳頭則替代了龍頭的尾部。二者渾然一體,形成了奇特的造型,極似一個正面描繪的獸面形象,這也是前人將其稱為“獸面紋”的重要原因。

圖10 商代青銅器中龍紋與鳳紋合體的畫面Fig.10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with dragon pattern and phoenix pattern in bronzes of Shang dynasty
龍頭鳳身的造型在西周青銅器中也曾經出現過,如在西周早期應公方鼎的裝飾紋樣(圖11)中,龍頭、鳳形身體的特征十分明顯,鳳形身體的尾部帶有長尾羽,龍頭上沒有龍角,飾有與鳳紋類似的花冠。朱鳳瀚[7]在《中國青銅器綜論》中稱其為龍首鳥身紋,其中龍頭、鳳身的造型均與當時的龍、鳳紋無異。
考慮到楚文化曾經與商、西周文化均有一定程度上的交流、融合,早期的楚國先后與商、西周的關系一度較為密切,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才分道揚鑣。高崇文[8]認為楚文化是江漢東部商文化孕育的,到了西周早期,楚王族叛商親周,《史記·楚世家》:“鬻熊,文王之師也。”鬻熊正是楚王族的祖先之一,曾與周文王交好。由此可知,商、西周的文化因子必然會對楚國文化產生影響,而楚國絲綢紋樣中出現的龍鳳合體造型均在商、西周紋樣中能夠找到相似的圖像。鑒于楚文化強大的包容性及楚人積極進取的學習態度,可以說,楚國絲綢紋樣中有很多圖像是在商、西周的基礎上延續及發展而來[9]。

圖11 西周青銅器中的鳳形龍紋Fig.11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dragon pattern and phoenix pattern in bronz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3 楚國絲綢中龍鳳合體造型的象征意義
從形態上分析,楚國的龍鳳合體造型中融合了楚國所流行的龍、鳳的主要特征,體現了龍、鳳在楚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弄清楚國絲綢中龍鳳合體造型的象征意義,必然要涉及到鳳紋與龍紋的起源及象征意義,學術界中此類觀點可謂眾說紛紜。
宋公文[10]、張正明[3]等認為楚國流行鳳紋屬于圖騰崇拜范疇,圖騰崇拜是從一些西方學者考察北美等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原始部落時,根據其部落留存的圖形,認為某些動植物是其祖先,并在一些制度上制定了相關的規范。然而,西周王室也十分崇拜鳳紋,《國語·周語上》“周之興也,鸑鷟鳴岐山”,《說文解字》“鸑鷟,鳳屬,神鳥也”,鸑鷟即為鳳。在西周青銅器中存在大量的鳳鳥紋樣,但周文化與楚文化的源頭并不相同[11],楚王族為祝融之后,與東夷文化密切,而周王室則發源于西岐,祖先為后稷,與羌戎文化交融。可見,“鳳紋為楚人的圖騰”的說法并沒有十足的依據。若要探清楚人崇拜鳳紋的緣由,必須從源頭上進行分析。依據當前的考古資料可以發現,鳳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東夷地區曾經流行的鳥紋,在商、西周二代的器物中也廣泛地出現過鳳鳥紋,商代甚至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起源傳說。可見,鳳紋在當時極受統治階層的青睞,其中肯定蘊含著極為重要的寓意。而楚王族的祖先曾經為商、西周二代的王族負責“觀象授時”的神職工作,對當時的天文歷法非常熟悉。商、西周時期流行的用以觀測太陽、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運行的十二次,將周天的黃道分為十二等分,從東往西逆時針依次命名為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用來觀察太陽系行星的運行軌跡。《國語》中就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的記載。在先秦的天文學中,楚、周、秦三地在天體星宿中的分野均對應在南方[12],周王室對應十二次中的鶉火,楚國對應鶉尾,秦國則對應鶉首(圖12),整個南方正是以鳳作為方位神,因而周、楚、秦均崇拜鳳紋[9]。王昆吾曾經將新石器時期的鳥紋分類,其中就有一種屬于鶉鳩型,《山海經·西次三經》有:“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鹖冠子》“鳳鶉火禽,陽之精也。”《禽經》中記:“赤鳳謂之鶉。”可見,曾經流行的鶉鳥正是鳳的前身,象征太陽。周、楚、秦均以鳳作為祥瑞之物,也是鳳紋廣泛流行的原因。此外,在楚人的心目中,鳳紋還是火正祝融的象征,反映了楚地的太陽崇拜。《白虎通·五行篇》中有:“祝融者,其精為鳥,離為鸞。”其中,離在《周易》中為火、太陽,鸞為鳳,明確地說明了鳳與祝融之間的關系。

圖12 十二次及分野Fig.12 The map which contains “Twelve Ci” and interfluve
龍作為通天的神物,在中國流行的時間較長,最初是對東宮蒼龍星宿的描繪。古人除了觀察太陽系各大行星的運行軌跡之外,還通過分析東宮蒼龍星宿的變化來制定歷法,以服務于農業生產。1982年,在距今約8 000的興隆洼文化遺址中出土過石堆龍,之后在距今約6 400年的濮陽西水坡遺址中又發現了龍、虎的組合圖像,龍紋在東方,虎紋在西方,代表了當時的人們對東、西方位所對應星宿的認識。古代文獻中對龍的描述也與天上蒼龍星宿的形態一致,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的爻辭大多數描述了龍,如“見龍在田”“飛龍在天”“龍戰于野”等。東晉的干寶認為乾、坤二卦的這些爻辭通過蒼龍星宿的形態記錄了一年十二個月份的變化[13],《說文解字》載“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講的是蒼龍星宿從春天開始顯現到秋天逐漸隱匿的天文學現象。正因為龍具備如此神通的本事,在先秦的文獻中還被描繪成祝融等神人的交通工具。《山海經·海外南經》:“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1895年的《山海經存》中所繪祝融的插圖(圖13)與商代“獸面紋”中所描繪的均是神人駕雙龍的形象。《九歌·東君》中也有:“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莊子在《逍遙游》中亦有“乘云氣御飛龍游于四海之外”的描述。

圖13 《山海經》中祝融駕雙龍的形象Fig.13 The images of Zhu Rong driving two dragons in “Shan Hai Jing”
總之,在楚人的天文學中,鳳是太陽神祝融的象征,而龍既代表東宮蒼龍,又是一些神人的交通工具。楚人以高超的復合造型技巧融聚了龍、鳳最具特征的元素,與楚國絲綢中曾經出現的“扶桑鳳鳥紋”[14]一樣,完美地反映了楚人的精神世界。由此可知,龍鳳合體造型屬于天體崇拜的范疇。
4 結 語
從源頭上看,楚國絲綢中出現的龍鳳合體造型是由鳳紋和龍紋共同變化、演繹而來,曾經在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中就已經出現過,只是沒有廣泛流行。龍鳳合體造型在楚國絲綢紋樣中得到了全面的發展,說明它們在楚人的心目中具有非凡的地位。可以肯定,龍、鳳都是楚人心目中的神物,并不存在尊鳳貶龍的看法,否則二者不可能出現合體的現象。學術界曾經廣為流行的“圖騰說”在分析楚國絲綢紋樣時并不一定適用,一些學者由于不了解楚國王族天文學世家的背景,套用西方的圖騰學說,認為鳳是楚人的圖騰,這種解釋并不科學。
綜上所述,龍鳳合體造型中的鳳為祝融的象征,龍為其交通工具,體現了楚人對太陽神祝融的崇拜之情,是楚人對心目中所理解的一些天文學現象的描繪,屬于天體崇拜的范圍。在造型方法上體現了楚人高超的藝術技巧,反映了楚人不拘泥于成法、勇于創新的心態,最終在東周列國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特色,并影響了后世中國傳統的祥瑞紋樣,如龍鳳呈祥圖形等。因此,需要追溯龍、鳳紋樣的源頭,研究當時的天文學背景方能知曉龍鳳合體造型的象征意義。
[1]彭浩.楚人的紡織與服飾[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94-109. PENG Hao. Spinning and Clothing of Chu Dynasty[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1995:94-109.
[2]伏兵.楚文化中鳳的造型藝術[J].絲綢,1998(3):40-43. FU Bing. Plastic art of phoenix in the Chu culture[J]. Journal of Silk,1998(3):40-43.
[3]張正明.楚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76-181. ZHANG Zhengming. Chu Culture[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1987:176-181.
[4]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2014:318. ZHANG Guangzhi. Chinese Bronze Age[M]. Beijing: SDX Joint Company,2014:318.
[5]阿城.河圖洛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4:93-123. A Cheng.Hetu and Luoshu[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4:93-123.
[6]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院墻灣一號楚墓[J].文物,2008(4):22. Jingzhou Municipal Museum. NO.1 Yuanqiangwan tomb of the state of Chu in Jingzhou city, Hubei[J]. Cultural Relics,2008(4):22.
[7]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68. ZHU Fenghan. Chinese Bronze[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2009:568.
[8]高崇文.楚文化研究論集:三[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33-34. GAO Chongwen. The Analects for Chu Culture: V3[M]. Wuhan: Hubei People Press,1994:33-34.
[9]張慶.楚國紋樣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15:287-300. ZHANG Qing. The Research on Decorative Pattern of Chu State[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2015:287-300.
[10]宋公文.楚國風俗志[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512. SONG Gongwen. Customs in Chu State[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1995:512.
[11]涂又光.楚國哲學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24. TU Yougua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u State[M].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1995:24.
[12]丁緜孫.中國古代天文歷法基礎知識[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214. DING Miansun. Basic Knowledge of Astronomical Calendar in Ancient China[M].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ress, 1989: 214.
[13]李鼎祚.周易集解[M].成都:巴蜀書社,1991:1-27. LI Dingzuo. Anthology of Zhou Yi[M]. Chengdu: Ba Shu Press,1991:1-27.
[14]張慶,方敏.楚國絲綢中“扶桑鳳鳥紋”造型的象征意義[J].絲綢,2012,49(7):61. ZHANG Qing, FANG Min. Pattern and spirit of Chu dynasty[J]. Journal of Silk,2012,49(7):61.
Research on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dragon and phoenix pattern in silk of Chu State
ZHANG Qing1, FANG Min2
(1.Department of Design and Arts,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2.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dragon pattern with and phoenix pattern in the silk of Chu State, these patterns were classified by archaeology typology. Through tracing back the initial shape of those patterns, this paper analyzed symbolic meaning of those patterns by combining the astronomy principle which came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documents, and the occupation of Chu imperial kinsmen’s ancestor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deling which combines dragon pattern with and phoenix pattern in the silk of Chu State describes the astronomy principle in Chu State, which belongs to astrolatry rather than the concept of totem. The phoenix pattern was the concept of “Totem” in the astronomy principle in Chu State, and the dragon pattern appeared as the transportation tool of phoenix.
Chu State; silk; dragon pattern; phoenix pattern; astrolatry
10.3969/j.issn.1001-7003.2017.01.011
2016-05-19;
2016-12-06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4YJC 760085)
張慶(1982―),男,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傳統工藝美術與視覺藝術研究。通信作者:方敏,教授,151267085@qq.com。
TS941.12;K892.23
B
1001-7003(2017)01-0064-06引用頁碼:011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