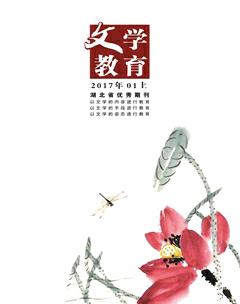作為一種文學(xué)符號的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是一個(gè)迷人的文學(xué)符號,她像是一個(gè)靈動(dòng)而巨大的地理磁場,吸附著無數(shù)作家對她一往情深的想象和書寫。生于故鄉(xiāng),長于故鄉(xiāng),成年后離開故鄉(xiāng)去城市打拼,年老后又費(fèi)盡氣力回到故鄉(xiāng),這大抵是許多“農(nóng)裔城籍”的作家相似的生活軌跡。在他們內(nèi)心深處,盡管空間意義上的故鄉(xiāng)早已不再是從前模樣,村里的人事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一種隱形的力量仍拉扯著他們,故鄉(xiāng)依舊擁有讓人深夜輾轉(zhuǎn)反側(cè)的魔力。
吳佳駿的《無處還鄉(xiāng)》是以第一人稱的敘述展開全文的,漂泊而獨(dú)居的“我”,在萬家燈火照亮城市夜空之時(shí)開始“眺望”故鄉(xiāng)。黃昏似乎是霓虹燈光的“敵人”,而“我”在此刻的所思所想,都源自童年的美好記憶。那些頗具鄉(xiāng)村色彩的意象,諸如鴨、羊、背簍、落日等等,都只不過是作為童年經(jīng)驗(yàn)的故鄉(xiāng)在“我”腦海里根深蒂固的種種記憶符號。這些與都市經(jīng)驗(yàn)截然相背離的體驗(yàn),將“我”帶入一種矛盾與對立的情感狀態(tài)之中——“我的感受總是這么龐雜”。作為農(nóng)村人的“我”,因身份特征和習(xí)性難改,終究只能是城市里沉默而卑微的他者。
毫無疑問,故鄉(xiāng)能使“我”充滿矛盾和分裂的內(nèi)心得到短暫的平衡。“我”在閑暇時(shí)候多次返鄉(xiāng),在石板路上平復(fù)“內(nèi)心的凄惶”,因?yàn)榭吹搅斯枢l(xiāng)蒼翠的山、潔白的云、石壁間的藤蔓、樹杈上的鳥……這些打有故鄉(xiāng)印記的自然符號勾起了“我”的鄉(xiāng)愁,緩解了“我”都市生活中的焦慮。然而,在懷念那些充盈著鄉(xiāng)村倫理溫暖的往事背后,回鄉(xiāng)也讓“我”感受到了“疼痛”。每次回鄉(xiāng)聽到鄉(xiāng)人去世的消息,生命消逝帶給了“我”巨大的心理震動(dòng),它引導(dǎo)“我”思考生命的意義。
接下來,作者詳細(xì)地講述了叔公之死。一生樂善好施、勤勞本分的叔父,擁有著大多農(nóng)民樸實(shí)、堅(jiān)韌的品格。當(dāng)疾病纏身時(shí),所有的辛酸苦楚只能由他一人承擔(dān)。叔婆煞費(fèi)苦心四處挖藥草給叔公吃,心力交瘁,長期下去,她對丈夫的愛也變成了恨,無法抵擋時(shí)間的消磨。在作者冷靜的敘述中,叔父的四個(gè)子女在他生病期間始終是缺席的,他們早已離鄉(xiāng)遠(yuǎn)去,陷入各自生活的泥沼里。盡管叔公死前想再看子女一眼,但死神并沒有給他完成夙愿的機(jī)會(huì)。這就是當(dāng)下農(nóng)村老人所面臨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讀到此處,一種生命的悲涼與凄楚撲面而來。吊詭的是,當(dāng)叔父的子女匆忙趕來參加父親的葬禮時(shí),“他們只在叔公的靈堂前磕了幾個(gè)頭,燒了幾沓紙,表情十分平靜,仿佛靈堂里躺著的那個(gè)人,跟他們沒有絲毫的關(guān)系”,這種驚人的麻木與對生命逝去的無情漠視,傳遞出以血緣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親情倫理在現(xiàn)代鄉(xiāng)村的徹底瓦解。自然,在“我”的眼中,他們是不需要故鄉(xiāng)的人。
幸運(yùn)的是,“我”還是心存故鄉(xiāng)的。父母生活在鄉(xiāng)下,親人的存在讓故鄉(xiāng)賦予了“我”精神上的意義。故鄉(xiāng)在親人的去世后,最終也會(huì)成為“一個(gè)地理名詞或文學(xué)符號而已”,這就是故鄉(xiāng)的宿命。在我看來,《無處還鄉(xiāng)》最值得稱道之處,就在于作者撕去了鄉(xiāng)村被賦予的田園牧歌式的浪漫幻想外衣,剝?nèi)チ肃l(xiāng)村作為底層的苦難光環(huán),而是從個(gè)體生命體驗(yàn)的角度,揭示了物欲橫流的商品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下,鄉(xiāng)村存在的真實(shí)而復(fù)雜現(xiàn)實(shí)情境。作為文學(xué)符號的故鄉(xiāng),透過想象和虛構(gòu),我們時(shí)刻在接近她,但我們無法真正重返故鄉(xiāng)。因?yàn)槲覀冊噲D抵達(dá)的故鄉(xiāng),只存在于記憶里,存在于兒時(shí)鄉(xiāng)村的草木蟲魚、風(fēng)雷雨電之中。她消逝在童年結(jié)束之時(shí),消失于經(jīng)驗(yàn)之下。故鄉(xiāng)像是一座城堡,我們邁著步子向她靠近,但我們卻離她越來越遠(yuǎn)。
周聰,青年評論家,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現(xiàn)居湖北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