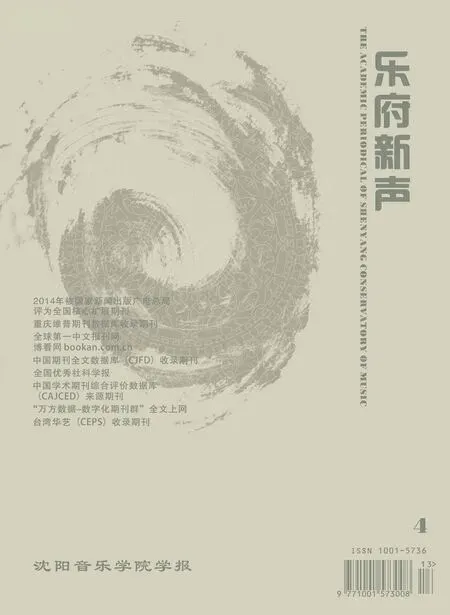混生音樂族性的美學分析(導論)
宋 瑾
混生音樂族性的美學分析(導論)
宋 瑾[1]
混生音樂即跨文化雜交音樂,可分雙源混生、多源混生/一度混生和再度混生等類型,因此混生音樂的族性很復雜。其族性混雜,卻往往歸屬某一來源族體。對此,極少有人關注。在混生音樂創作上,存在族性體現缺乏感性效果的現象。今天進行非遺保護、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復興,需要從美學上分析各種混生音樂族性及其相關問題。
混生音樂/族性/感性效果
一、“混生音樂”指謂
“混生音樂”(hybrid music或 mixed music),全球化語境中的用語,亦為音樂人類學和后殖民批評語境中的用語。相對于“原生音樂”(“根源音樂”original music)或“傳統音樂”(traditional music),混生音樂是由不同文化中的既有音樂混合而成的音樂,發生在跨文化交流之中。亦可稱為“雜交音樂”。有的為雙元或雙源混合(雜交),有的為多元或多源混合(雜糅)。歷史上的原生音樂即傳統音樂,與原初族體(ethnos)相關;當下的原生音樂指新出現的音樂品種,如單純的電子音樂,與新生創作、研究和愛好者族群相關。混生音樂可分一度混生音樂和再度混生音樂。前者由不同的原生音樂混合而成,后者由一度混生音樂和其他音樂再度混合而成。這里涉及“原種”(stock)、“基因”(gene)等基本概念。原初族體在相對穩定而封閉的地理、社會環境生活,產生了相應的原生音樂。無論是人種還是樂種,“原種”意味著最初始的族體和根源音樂(由于追溯的困難,事實上“原種”的純粹性難以確定,只能在相對意義上確認)。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原種的遺傳總是會出現變異,但是只要基因未發生質變,人種和樂種就還是原種。對作為文化事物的音樂而言,用“基因”來描述是一種隱喻,但卻有助于說明問題。因為混生音樂意味著樂種的變異。打個比方,如果中國傳統音樂是驢,西方古典音樂是馬,那么20世紀出現的中西結合的“新音樂”就是騾,它是雜交的物種,基因發生了變異。而在隋唐時期,四夷音樂納入宮廷的“十部樂”、“九部樂”,被漢化了,就像小溪流或山澗流入黃河,被染黃了;黃河水沒有變色,傳統音樂沒有質變(但卻具有可感知可分析的混生特點)。而新音樂則像黃河遭遇了藍色海洋,變成了“綠色”,是新的混生樂種。詳見后述。
二、混生音樂典型
其一,中國政治語境中的“新音樂”,傳統音樂與西方古典音樂結合產生的音樂,如國歌。屬于官方音樂及其影響范圍的社會大眾音樂范疇。其他東方國家的新音樂也如此。
其二,中國學術語境中的“新潮音樂”,傳統音樂與西方現代音樂結合產生的音樂。屬于藝術音樂范疇。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相同或相似的新潮音樂。新潮音樂往往屬于專業作曲家群體和相應的學術界。
其三,中國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新民樂”,傳統音樂與現代流行音樂結合產生的音樂。如“女子十二樂坊”,各地旅游文化中變異的鄉土音樂;文化產業中的相關音樂。屬于流行音樂范疇,與相應的表演群體和粉絲群體相關。
其四,世界傳播的民族音樂變型,如扎伊爾、古巴等國的雜交音樂,具有多源多樣的混生性,主要歸屬此兩國。再如方丹戈(fandangos),是西班牙、墨西哥、印第安等的音樂,加上流行音樂元素混和而成的音樂,都與文化產業有關,主要歸屬西班牙和墨西哥。還有弗拉門戈(f l amenco),是由吉普賽人將印度、阿拉伯、西班牙猶太人的音樂混生而成的,主要歸屬西班牙。在傳播上,“歸屬”僅僅是一種標簽。
其五,全球化中新異質化的音樂,如爵士樂、搖滾樂、“第三潮流”等。近年來人們熟知的“搖擺巴赫”也是典型之一,屬于再度混生音樂。它們以美國為中心向全球輻射(產生的原因和過程各有各的復雜性),各有喜愛的群體, 等等。總之,所有跨文化雜交的音樂,都是混生音樂;它們各自歸屬某個文化群體。
三、混生音樂的族性和歸屬
如上所述,特定混生音樂與特定族體相關,反映了族體的特點,體現了族體的精神面貌;它們總是在特定的社會、時期,為了滿足特定族體的需要而產生的。混生音樂的族性很復雜,因為原初族體不斷衍變;新族群不斷出現。本課題的“民族”采用以下民族學研究成果:種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民族(nation)。種族如初民的部落,今日的家族,是同血緣關系的族體。族群如漢族、蒙族等官方確認的56個民族,是若干種族聯合的族體。民族如中華民族,是若干(56個)族群聯合的族體。此外,本課題的族性也涉及“文化群體”,如宗教文化群體(基督徒、佛教徒等),它已超越了初始國別、族群和種族,也有相應的音樂樣式,其中包括某些混生音樂樣式。新近還有“賽伯族”(cybernation),指因特網的網民,具有更大范圍的超地理國界和超原始族體的特點,但也具有“亞族體”的特點,即非典型的族體特點。雖然賽伯族是精神族類,身體只有進入虛擬世界(音頻視頻或間接觸覺關聯)時才是在場的,但是他們畢竟帶有現實中與生俱來的初始族體印記。“賽伯格”(cyborg)指局部電子人,將現代電子裝置與人體結合,實現更迅捷的人-機互動;如果加入賽伯族,可視為升級的網絡人。網絡歌曲、口技打擊樂(Beatboxing)、混搭(Mashups)等音樂類型屬于這個新族體文化,其中的混搭具有顯著的混生性,其他則具有相對于原始族性而言的中性化特征。與族體相關的日常用語如“人民”、“公民”等,多用在政治語境中;相對上述族體而言,它們具有模糊性。
混生音樂的族性及其歸屬問題,無論從時間維度還是從空間維度看,都很復雜。
從時間維度看,一方面跟歷史相關(族體歷史文化的根脈),另一方面跟時代相關(族體精神因社會變化而變化的特征)。例如中國的新音樂,是20世紀“新文化”“新音樂”運動的產物。國人力圖祛除自己族性中的劣根,改變受壓迫的狀態,被動-主動雙向學習西方列強音樂文化,與未完全被拋棄的自身傳統音樂結合而成新音樂。新文化主體具有民族傳統的根脈,但力圖超越而成新族體,接受新思想,設定新目標,甚至從發型、服飾、語言等方面都力圖革新。事實上所有的“新”都來自中西結合。中國新音樂作為中西結合的產物,被歸在中國一邊,就像騾子被歸在驢的國度一樣。但是它畢竟有馬的基因成分,在中性或中立標準(如抽象學理標準)的參照下,也可以歸屬馬的國度。有的新音樂作品由于采用了接近歐洲族群的少數民族(例如新疆各民族)的音樂,結合西方古典音樂創作技法,音樂語言和作品風格顯得洋腔洋調,如小提琴曲《紅太陽的光輝照耀著塔什庫爾干》,無須費勁就可看出它隸屬于“馬”的程度更大。還有一種族性歸屬的說法,即新音樂歸屬新生中華民族。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在20世紀以來形成一個新族體;新音樂的族性體現這個族體的特點。即便如此,無論是非遺保護還是民族復興,都指向傳統族體音樂文化;比起新音樂來,傳統音樂文化這一“元”離西方音樂文化那一“元”更遠,更有獨特性,它的傳承或重建對世界多元音樂文化生態更有利,對國家軟實力提升更有利。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究。
從空間維度看,一方面跟多源原生音樂相關(與兩種或多種原初族群音樂文化的聯系),另一方面具有獨特的整體特征,并且在分布上不同于原生音樂的疆界。這跟跨文化傳播和融合有關。例如西方小提琴傳到印度,出現了“印度學派”,以至于小提琴大師梅紐因生前還專程去印度“學習”。再如原本就是混生的爵士樂或搖滾樂,從西方傳播到全球,在各地出現了異質化分支。中國的搖滾樂就混合了漢語、五聲音樂和國人氣質等成分(卻削弱甚至祛除了原有的批判精神)。“搖擺巴赫”則是再度混生音樂,即美-非一度混生的爵士樂和歐洲巴洛克時期巴赫的音樂再度混合。由于超越了傳統意義的“二度創作”范圍,音樂語言和風格都發生了重要變化,“搖滾巴赫”隸屬于爵士樂的程度更大(本來如此)。宗教音樂初始作為地方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部分,傳承過程具有穩定性甚至惰性(長期不變或逐漸量變)。隨著全球傳播,信眾成分逐漸混雜,音樂也出現異質化分支;許多分支在地方化的同時出現混生性。如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和東南亞,如今傳播到全球各地,已經不再限于東方;其佛事音聲在世界各地也有差異。基督教和天主教從西方傳播到全世界,信徒和音樂也都出現多樣性和混生性。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亦然。群體和音樂都變化的情況下,混生音樂的族性也就超越了原初的族體。
四、國內外相關研究概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下列論文大多為某個區域、某個混生現象的研究成果。[1]搜索IIMPFT(國際音樂期刊全文庫),輸入hybrid,得到1592條結果;2016-10-25得到10008條結果;輸入hybrid music 得到8845條。限制在學術期刊全文文獻,得到1397條。
2009年11月21日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民族音樂學第54屆年會的亞洲音樂學會分會上,斯蒂芬·布盧姆(Blum, Stephen)作了題為《一個學會和它的雜志:混生性的故事》(A Society and Its Journal:Stories of Hybridity)。布盧姆是受學會委托為亞洲音樂學會成立50周年而寫的綜述性文章,刊登在該學會學術期刊《亞洲音樂》2011年冬季至春季號[2]Asian Music42.1 (Winter-Spring 2011): 3-23.。在這篇文章里,作者重點探討亞洲音樂文化的混生性和后殖民性。
L-基多施(López-Gydosh, Dilia)和漢考克(Hancock, Joseph)的論文《美國人及其身份:當代美國黑人和拉丁風格》(American Men and Identity: Contemporary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o Style)發表于2009年《美國文化雜志》。[1]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32.1 (Mar 2009): 16-28.論文考察非裔美國人和拉丁美洲人的文化風格,探討二者之間的音樂關系、社會和視覺識別等,以及20世紀和21世紀的流行趨勢。
湯因比(Toynbee, Jason)和威爾克斯(Wilks,Linda)發表的論文《英國黑人爵士樂的受眾、世界主義和不平等》(Audiences, Cosmopolitanism, and Inequality in Black British Jazz),[2]Black Music Research Journal33.1 (Spring 2013): 27-48.作者通過考察以英國黑人音樂家為特點的爵士樂音樂會觀眾,認為英國黑人爵士樂包含了實際上被稱為世界主義的風格,盡管其中因成分不均等可以劃分為若干重要的不同方式。
湯普森(Thompson, Tok)的文章《口技節奏、混搭和賽伯格身份:21世紀的民俗音樂》(Beatboxing, Mashups, and Cyborg Identity: Folk Music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3]Western Folklore70.2 (Spring 2011): 171-193.該文探討兩種新藝術的音樂傳統,即口技節奏和混搭,認為從其公共的、變化的形式所顯示的跡象看,它們往往跟民俗音樂相關。作者考察審美選擇和身份之間的關系,關注點聚焦在“人-機”主題上。賽伯格(局部電子人)、人與機器交互連接的認知功能,所有這一切在21世紀初日益變為現實。
拉波特(Rapport, Evan)發表了題為《彼爾·法恩根的格斯文改編曲與美國的混生性觀念》(Bill Finegan's Gershwin Arrangements and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Hybridity)的文章,[4]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Music2.4 (Nov 2008): 507-530.探察了法恩根對格斯文《藍色狂想曲》、《F大調協奏曲》的管弦樂改編曲,認為它們提供了闡釋格斯文作品的基礎,即法恩根的改編曲提示格斯文這些作品的風格是以流行音樂技法為基礎的。作者認為他們二人的作品突出了美國的混生性觀念,尤其是關注“爵士交響樂”、“爵士音樂會”以及種族的理念,等等。
在關于族性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特別要提到的是英國的斯蒂夫·芬頓的《族性》[5][英]斯蒂夫·芬頓.勞煥強等譯《族性》,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是民族學基本概念深度研究的成果,涉及該領域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族體、族裔、種族、族群、民族、群體、人民、族性和文化等等,以及許多錯綜復雜的關系。后者如 “族性”與“文化”的關系。在范圍上,有時文化大于族性,如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文化具有世界性,超越了原初種族、族體和族性;有時小于族性,如同一族群內部分化的階級、階層、語言、習俗和信仰等文化的多樣性或差異性。漢族這個族群內部就有這樣的多樣性或差異性。該書還列舉了學者對馬來西亞婆羅洲島北部的沙撈越地區人口族體分析的例子,說明實際的族體劃分和族性研究的復雜性。還用前蘇聯的族體、階層等事例來說明國家意識形態介入族性分析的復雜性。美國移民的多源性則呈現了除了不同群體人口差異之外的等級差異。作者以紐約黑人為例,指出對這個族群的來歷,用“南方移民”比用非洲黑人和奴隸,或非洲裔美國人好得多。而“白人”之間也有差異,如波蘭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猶太人等。作者還介紹和分析了“構建論”和“原生論”的爭論,涉及“原生群體”(primordial group)和“族裔傾向行為者”(ethnically oriented actor)、移民、“族裔紐帶”(ethnic ties)及其具體化的“情感紐帶”與“理性籌劃”、族裔認同或文化身份認同、歸屬感與族性話語等重要問題。作者的分析對本課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在社會性別的研究領域,西方學界對新出現的人群做了劃分和探究,如女性主義、新女性主義、酷兒(queer)等等。這種人群的劃分,基于性別觀念、取向,帶有明顯的政治和文化意義。這些新族群擁有自己的音樂觀念和選擇行為。例如一個被稱為“歌劇女王”的男同性戀群體,喜歡借助歌劇女主角的個人性征、相關角色劇情和歌唱特點等來抒發自己的情感。[1][美]露絲·索莉. 謝鍾浩譯《音樂學與差異》,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175-184頁。
在全球化、后現代主義或后殖民批評研究領域,部分西方學者集中討論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全球化研究將人群劃分為“全球人”(globals)和“本土人”(locals)。前者指能經常跨地域活動的名人或精英,后者指沒有能力離開本土的普通人。[2][美]齊格蒙特·鮑曼.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后果》,商務印書館2001年,緒論2。福柯則別出心裁使用“全景監獄”(panopticon)、“對觀監獄”(Synopticon)的詞匯來劃分社會權力關系中監視群體與被監視群體,以及媒體中的名人和電視機旁的普通人。[3]同上 .30-31、33、47、50、52。顯然,這些劃分都不是民族學意義的劃分,而是全球化語境中的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階層劃分。
后現代主義反對本質主義的族體劃分,它的觀念滲透到音樂人類學,出現了“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劃分,進而出現“局部局內人/局外人”等劃分。本地人并非就是局內人。在后殖民批評領域,學者在殖民時期的宗主國和殖民地劃分基礎上,探討殖民者撤退之后,原殖民地人依然延續西方中心主義狀況。關于文化身份認同,情況更為復雜。殖民地人從第二代開始就受到西方音樂文化教育,移民西方國家的黑人和黃種人從第二代開始也逐漸蛻變,為此出現了奇特族體——黑皮膚、黃皮膚都掩蓋不了“白心”的事實;人種已不能作為族體劃分的依據。當今美國黑人的身份認同為“我是美國人”。在美國的黃種人也如此。那么在原殖民地的本土人民又怎樣呢?他們也接受西方式教育,文化身份認同是一回事,實際心性又是一回事。這些問題具體涉及到“地方性”(locality)。有學者指出如今的“地方”已經跟過去不一樣;在現代化進程中,已經蛻變了。今天仍然將地方當作像過去那樣具有整合性的共同體,那僅僅是一種預設或想象。
(二)國內相關研究
關于音樂民族性的研究。在中國,這個問題過去是在政治語境下探討的。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對革命時期的文化運動及新文學藝術的特點概括為“三化”,即革命化、大眾化和民族化。首先要革命化,文藝才能作為“有力武器”;革命需要團結大眾,所以文藝要大眾化;借鑒西方文藝,需要民族化,才能在中國產生作用。就音樂而言,“借鑒西方作曲技術,創作具有中國風格的作品”已成為音樂家共同遵守的原則。后來的民族性問題探討,則逐漸轉移到學術語境中來。但是,人們并沒有意識到新音樂的族性歸屬問題。即便有個別學者提出新音樂可以看成“中國風格的西方音樂”(劉靖之),卻無人持續關注,更無人對此進行專門探討。
關于新音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現代中國歷史發生的“中西關系”問題討論上。這方面的言論很多,有專著、學術期刊論文,也有學位論文;截至本文寫作初始時期(2017年1月),中國知網“新音樂”主題文章將近3800多篇,不一一列舉。但是都沒有直接探討族性歸屬問題,也很少探討族性的直觀有效性問題。
關于新潮音樂的研究,中國知網“新潮音樂”主題文章有180多篇,多集中在“中西關系”的問題上,尤其是西方現代技法的借鑒問題。由于涉及現代作曲技法,研究者多為專業音樂家或學子。另有一些爭論集中在現代音樂的可聽性問題上。還有一些重大課題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重大規劃項目《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器樂創作研究》,其中第二卷梳理了有關新潮音樂的爭議。但是對新潮音樂的族性和感性問題的研究也很少或沒有。
關于新民樂的研究,中國知網“新民樂”主題文章有230篇左右。由于新民樂與流行音樂有關,所以受到的關注面較大,也得到媒體的較多傳播。這個領域曾經集中在一些時尚音樂群體的表演,如“女子十二樂坊”之類。從已發表的言論看,褒貶不一。贊揚者認為新民樂吸取了流行音樂元素,有利于現代人特別是青少年接觸并喜愛傳統音樂。批評者則認為它已經不是傳統音樂,對青少年有誤導作用。
關于“原生態音樂”的探討,源自中央電視臺青歌賽增加的“原生態”組。中國知網“原生態民歌”主題文章有3600多篇,集中討論其特點和傳承等情況。“原生態唱法”主題文章有1450篇左右,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唱法上,即美聲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之外,是否可以再列出一個原生態唱法。特別是將它和民族唱法比較,認為都是民族的唱法,區分在于前者是民間的民族唱法,后者是學院的民族唱法。這些討論沒有吸取現代民族學關于“民族”的劃分,概念上比較模糊,有待深入探討。與本課題關系更為密切的問題是,原生態音樂(上文所說的“原生音樂”)一旦進入了現代傳媒,就不再是原生態了。筆者曾經形容它們為“動物園里的動物”或“魚缸里的魚”,因為它們脫離了原生環境,進入了人工環境,中性化的環境;從自然文化變成人工文化,功能和價值也隨之改變。雖然它們本身不是或不一定是混生音樂,但卻由于環境和文化方式的改變而成為重要研究對象。對它們的研究,有利于探討族性問題以及本課題其他相關問題,例如“族性”在音樂中的體現等。
近年來,民族音樂學或音樂人類學研究出現熱潮。關于族性研究,出現了“中性化”文論。“中性”(neutrality)指沒有原始民族性的性質,包括環境的中性化和人的中性化;出現了“中性人”的新指謂,指沒有民族屬性的族類。相應地,也出現了中性化音樂,即沒有民族特征的音樂。中性人還有具體類別,按照信仰、職業、階層、性趣等劃分。[1]宋瑾《中性化:后西方化時代的趨勢(引論)——多元音樂文化新樣態預測》,交響2006年,第45-58頁。這些族群的音樂有不少是混生性的,如上所述的宗教音樂分支、流行音樂等。
五、本項目擬解決的問題、目的與方法
(一)問題:混生音樂的感性特征、族性歸屬、功能與價值、生存與發展。
其一,混生音樂的感性特征。在兩個或多個音樂原形(原生音樂)混生之后出現了新形,它攜帶著各原形的“基因”。這些音樂原形的特點可以通過理性分析抽取出來,但是在感性上,則具有整體格式塔特征,可以在直觀中被感受和辨別。好比騾子,可以分析出馬和驢的基因,更重要的是可以被直觀為新品種,并從兩個原形的參照中被區分開來。但是現代混生音樂(如新潮音樂)在理性分析上尚可找到原形,而在感性特征上卻未必聽得出來。以至于有不少現代音樂作品呈現出“中性化”特征,無法區分族性。不少國內外作曲家認為個性比族性更重要。也有作曲家認為族性無法抹除,彰顯個性的同時,將自然流露出族性。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探討,以利于相關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其二,混生音樂的族性歸屬。有趣的是,幾乎全世界的混生音樂都被統歸到某一個國家或民族。至少起源上如此。我國新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混合而成的音樂,如今已成為主流音樂。在族性歸屬上,毫無爭議地納入我國現代社會。其他東方國家的新音樂亦然。問題是,為什么騾子一定歸屬驢,而不是馬?爵士樂是非洲傳統音樂和美國音樂(西方古典音樂及南美民族音樂)混合而成,雖然后來在全世界傳播,但依然歸屬美國。而搖滾樂是在爵士樂電聲化的產物,路經是從美國到英國再到美國然后傳到全世界。歸屬上籠統為“西方流行音樂”,人們依然以美國為中心。New age里的Ethnic fusion類型,以及后現代主義無機拼貼的“復風格”類型,是一種“拼盤”,難以確定其族性歸屬。新音樂采用西方管弦樂寫作,經常以民族傳統音樂為主題。如何區分中國作曲家創作的民族風格的器樂,與西方作曲家采用中國民歌創作的器樂,二者之間的族性差異?普契尼歌劇《圖蘭多》中采用了“茉莉花”,無人認為它是中國作品。而中國作曲家改編的“茉莉花”也無人認為它是西方作品。那么音樂的族性是由作曲家的國別族別確定的嗎?文化氣質在感性上如何界定如何呈現?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音樂文化”觀念成為共識,因此需要確認每一“元”。那些事實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的音樂類別,將合并同類項,歸入某一元。
其三,混生音樂的功能和價值。混生音樂的起源本身就說明它是應運而生的,它被某個社會某個時代某個族體或人群所需要,因此具有特殊的功能和價值。例如第三世界的新音樂,都和歐洲殖民主義有關。中國的新音樂也如此。在20世紀上葉,救國救民成為主流思潮。為了強大起來不受欺負,需要向強國學習。于是出現了各種新事物,包括新音樂。所謂“新”,就是和傳統不一樣;中西結合的結果,騾子不同于驢。它在當時具有啟蒙、團結、激勵國民為自由和幸福而抗爭的功能和價值。建國以后,它又成為運動的聲音。如今,它依然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保持主流身份和狀態,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甚至有學者稱之為“新傳統”。同時,它和新潮音樂一道被當作學術探討的問題,即“中西關系”、“古今關系”、“雅俗關系”和“(音樂)內外關系”等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國內外的音樂產業都樂于走混生道路,目的是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混生的新產品,往往擁有更大的受眾。例如非洲和南美洲的許多新音樂,往往是多源混生的結果,被銷售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歐美。
其四,混生音樂的生存和發展。目前中國處于新的轉型期,政治上要求建構中國話語體系、軟實力、國際傳播和話語權,經濟上要求實現工業向后工業的轉變,文化上要求建立或復興中華文化、美學精神等。在這樣的社會環境或語境中,混生音樂是否符合時代需要,能否擔當轉型的促進者責任,需要深入探討。尤其是和“非遺”相比,和古老的文化傳統相比,現代混生音樂的生存合理性在哪里?它應該走向何方?這是特別需要探討的問題,關系到未來我國音樂文化的發展方向和路徑。
(二)目的:學術目的和實用目的
其一,學術目的。澄清各種相關思想觀念、概念、爭論,為建構“新音樂美學”奠定基礎,為建構“多元音樂美學”提供“一元”。如上所述,混生音樂的族性問題未受到足夠充分的關注。歐洲殖民主義的結果是所有東方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東西結合或混生的“新音樂”。由于西方音樂和各地新音樂的存活狀態都良好,唯獨傳統音樂被邊緣化并逐漸消失。“非遺”保護的意義就在于搶救傳統音樂文化資源;搶救這些資源是為了共享,為了多元文化生態的繁榮。筆者認為如今的“多元”處于人工態,它包括了被挖掘和保護的“原生態”的多元和新異質化的多元。換句話說,即各種原始的原形、現代新原形,各原形的變形,以及各種雜交形(混生音樂)——老原形之間的混生音樂、新原形之間的混生音樂、新老原形之間的混生音樂、各變形之間的混生音樂,各變形與各原形之間的混生音樂,等等。各種類型都歸屬相應的族群,并通過各種渠道向其他族群傳播。區分這些音樂類型,有利于明確多元音樂文化之“多元”的具體情況。原形及其變形的族性相對容易辨別,但是混生音樂的族性則需要細致分析。從現實情況看,新音樂、新潮音樂這類中西混生音樂并沒有獨立的區別于原有民族的族性歸屬,而是依附于雙源之一方,即中華民族。也就是騾子歸屬驢。即便如此,從多元生態看,不同原形混生的音樂,其族性特征不如原形那么鮮明。原形的鮮明度有利于一個民族構建自己的音樂文化體系或話語。
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上,“原樣保護”與“變化發展”之間,存在著持久的爭議。其中存在觀念、概念等問題需要澄清。如“非遺保護”的對象究竟是什么,意義何在。相對于混生音樂,“非遺”保護的就是原形,是驢。混生音樂或雜交音樂,首先是以原生態音樂為參照的,是不同原形或其變形混合而成。反之,研究混生音樂,對原生態音樂或“非遺”的傳承、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實用目的。促進混生音樂實踐健康發展;為解決音樂教育中的相關疑難提供參照;為政府相關決策提供咨詢服務。
在非遺保護的同時,應放開思路,更多地創造,包括新形音樂和更多樣的混生音樂。當然,對于已經出現的混生音樂,應給予理解和支持。這是促進當今多元音樂文化生態更加繁榮的需要。在全世界普遍存在混生音樂,而且隨著新族群的出現,或者新商機的利用,還在增加混生音樂的種類。顯然,特定混生音樂跟特定族群的政治、經濟、文化密切相關,又在全球化進程中相互影響。
具體目標:初步概括判斷音樂族性的尺度;為解決混生音樂的“民族風格”問題做出努力;分析迄今存有的幾種混生音樂類型;探討當今混生音樂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探究混生音樂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思路;為新音樂美學、多元音樂美學建設提供參考。
(三)方法:比較方法與美學方法
其一,比較的方法。“混生音樂”與“原生音樂”的比較。通過比較,看清二者或三者的差異,抑或混生音樂與作為根源的諸種原生音樂的差異。同時,看清混生音樂中各種原生音樂的“基因”,及其所占的比例;借鑒模糊數學的“隸屬度”計量法,看清混生音樂對各個根源音樂的隸屬程度。例如通過比較分析,察覺新音樂具體作品在中-西之間的隸屬度量。再者,比較混生音樂和原生音樂的族群歸屬——由樂看人,了解不同時代族群的特點和需要,由樂反觀族群的衍變情況;由人看樂,了解不同時代混生音樂的合目的性以及功能的產生和實現情況。
其二,美學的方法。即注重感性分析的方法。雖然大家都知道樂譜和音響之間不等同,樂譜僅僅是用記號大致記錄音樂;傳統音樂的樂譜更為簡略,僅僅記錄音樂“骨架”,活態音樂指實際活動中的音樂聲音。但是學界依然更多地通過樂譜分析來探討音樂意義。于是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樂譜分析可以發覺的民族音樂成分,實際上卻聽不出來,無調性的現代主義作品尤其如此。改編類混生音樂,“移植”和“主題化”類型較容易分辯原生音樂,“意譯”則不易分辨。“移步不換形”之“形”需要聽覺能分辯;“形變魂不變”的“文化氣質”更需要直觀把握。因此,美學的感性分析非常必要。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 analysis on ethnicity of hybrid music
Song Jin
Hybrid music is cross-culture music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ny types including two or multiple origin, mixture once or more times. Many hybrids music which have complex ethnicity is from same origin. In composing of hybrid music is lack of sensibility.We need research with aesthetic perspective in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ybrid music, ethnicity, sensibility effect
J601
A
1001-5736(2017)04-0061-8
本文為2015年度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研究項目“混生音樂族性的美學分析”之緒論,批準號15DD33。
[1]
宋 瑾(1956~),博士,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張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