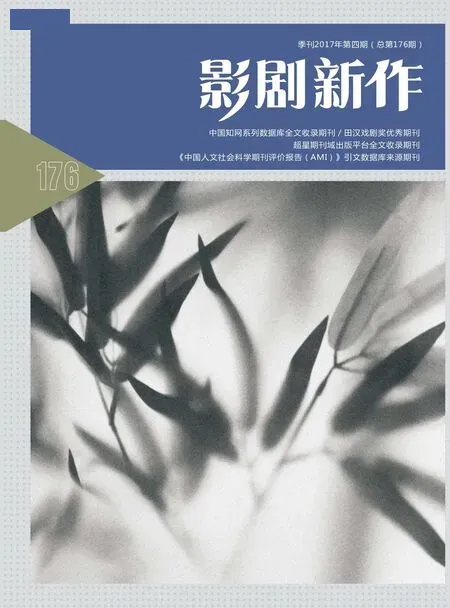東河戲藝術(shù)家幸巧玉的藝術(shù)生涯及成就
何厚偉
引 言
東河戲,又稱“贛州大戲”“東河劇”,源于贛州以東的貢江流域,是贛南客家地區(qū)傳統(tǒng)劇種。在其傳承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涌現(xiàn)出許多為之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優(yōu)秀東河老藝人,幸巧玉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已是84歲高齡的幸巧玉,仍然熱衷于她喜愛的戲曲事業(yè),努力地在傳承東河戲。雖已滿頭銀發(fā),但依然精神飽滿,說起話來擲地有聲,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完全看不出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但當年的她可謂是東河流域家喻戶曉的人物,被譽為東河戲的“當家花旦”,但凡老一輩的東河戲迷,只要提到幸巧玉的名字,都紛紛豎起拇指表示稱贊。
一、好事多磨 業(yè)精于勤
1934年幸巧玉出生于江西南康唐江鎮(zhèn)幸屋村的一個藝人家庭,其母是位普通的農(nóng)村婦女,其父幸三元是名祁劇演員。在那個十年九災的歲月里,父親迫于生計,經(jīng)常奔走于鄉(xiāng)鎮(zhèn)廟會,忙于演出,家里全靠母親一人操持。1940年母親不幸去世,這讓這個原本經(jīng)濟拮據(jù)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生活愈加艱難。由于家庭姊妹眾多,無暇兼顧,父親忍痛將她送給從湖南來贛州演出的祁劇藝人黃氏做童養(yǎng)媳,那年她才7歲。
幸巧玉天生擁有一副好嗓子。由于生長在藝人家庭的緣故,她從小聽著父親唱大戲,平時玩耍時也跟著哼唱,加上黃姓人家也是有名的祁劇藝人,讓她有機會跟著開闊眼界,漸漸地展現(xiàn)出她在戲曲方面的天賦。1945年,11歲的幸巧玉正式拜入東河戲著名男旦演員鐘名鵠門下。鐘名鵠師傅是對她人生影響最大的一位恩師,生活上鐘師傅像自己的父親一樣,對她照顧有加,但在藝術(shù)上非常嚴格近乎茍刻,容不得半點馬虎。當年師傅的教導至今猶時常在她耳際回響:“想要在戲曲藝術(shù)領(lǐng)域扎下根,就必須付出辛勞的汗水。”
學藝之苦,成名之難,只有藝術(shù)家自己最清楚。學藝時,她每天早起練功壓腿、喊嗓子、翻筋斗、跑圓場,時常摔得鼻青臉腫,喊得嗓子失聲。尤其學戲曲念白最為吃力,學戲必須先學贛州話,因為東河戲唱腔念白使用贛州官話,而她從小說客家方言,未曾進過學堂,面臨不識字的困難。為了盡快識字和熟悉劇本,幸巧玉把戲班里識字的人都當成她的老師,私下里拿著劇本請教,快速掌握,硬是憑借勤奮好學的精神和驚人的記憶,把劇本臺詞完整背下來。戲班平時演出,年齡尚小的她總在后臺跑上跑下,問這問那,躲在幕后看大人們演戲,人手不夠時還客串一些小角色。她珍惜每一次上臺的機會,有時為了得到鍛煉機會常常跟人爭演角色而哭鬧。師傅看出她對戲曲的熱愛,開始嘗試教唱一些大戲。因為刻苦學戲,加上初生牛犢不怕虎,她12歲時便登臺演出,能夠在《殺四門》《盜仙草》中飾演一些重要角色。師傅的嚴格要求,加上她聰明好學,又有一股不服輸?shù)膭牛纸?jīng)過了三年的藝術(shù)錘煉和實踐,1949年正式出師。小小年紀就掌握了東河戲的基本唱腔和身段表演,學會了大大小小近百出劇目,15歲時開始在劇團里嶄露頭角,成為主要演員,當時劇團的老藝人都夸她:“肚子好飽,文武雙全,昆、亂不擋。”
二、把握機遇 成于東河
新中國成立后,文化部戲曲改進局牽頭主持全國性“改人、改制、改戲”為內(nèi)容的“戲改”工作順利推進,1952年文化部和江西省文化局派專員來贛州了解東河戲情況,幸巧玉所在的“玉洪臺”戲班由鄉(xiāng)下轉(zhuǎn)移到贛州城內(nèi)演出。1954年經(jīng)贛州市政府批準,“玉洪臺”班社正式更名為“贛州東河劇團”。東河老藝人奔走相告,相擁而泣,他們的地位和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大地提高了藝人們的藝術(shù)積極性。劇團舊貌換新顏,有了固定的演出場所,添置了新的服裝、砌末等,東河戲的傳承和發(fā)展也迎來了歷史機遇。幸巧玉十分珍惜這個機遇,更加刻苦練功,積極向東河戲老一輩藝術(shù)家學習,如丁良州、劉良格、劉達江、劉福來等老藝人都對她進行過指導;另外她還廣納博采、兼收并蓄,打破門戶之見,向祁劇老藝人請教。正是這種善于學習的精神,她在唱腔和演技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0歲就成為了東河戲劇團的主要演員,劇團的“臺柱子”。
1954年,江西省文化局為檢驗和獎勵戲曲事業(yè)的改革和建設(shè)工作的成就,組織了江西省首屆戲曲觀摩會演。東河戲作為贛南行政區(qū)的代表參加此次演出,選送的劇目有《張旦借靴》《搶傘》《五臺會兄》《公堂挽發(fā)》《取成都》5個東河高腔劇目,演出獲得了圓滿成功。由幸巧玉主演的東河高腔《搶傘》獲得了優(yōu)秀表演獎及銀質(zhì)獎?wù)隆_@是她戲曲藝術(shù)表演生涯中第一枚獎?wù)拢两袢匀槐4嬷V笮仪捎癫]有因為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反而更加激勵她在藝術(shù)上精益求精,一心關(guān)注劇團發(fā)展。東河劇團剛剛成立時還處于困難期,為了不給文化部門添麻煩,劇團演員齊心協(xié)力自籌經(jīng)費,規(guī)定每天演三場戲,每人只吃兩餐,將省下來的錢買戲服。為了劇團事業(yè)的發(fā)展,已有5個月身孕的幸巧玉依然堅持演出。《戰(zhàn)宛城》里有一段張繡刺殺嬸母鄒氏的武打場景,她照演不誤,鼓聲一響入了戲,又是打斗又是翻滾,有驚無險地完成了演出,臺下觀眾一片叫好,豎起大拇指。幸巧玉后來回憶說:“我在臺上想的是把戲演好,對得起臺下的觀眾就好。”在她看來,戲就是生命、戲就是她的全部,正是這種對戲曲藝術(shù)的執(zhí)著讓她贏得了一大批的戲迷。
50年代中后期,劇團處于最好的發(fā)展階段,演出逐漸增多,除了贛南地區(qū),福建的長汀、上杭、龍巖等地都邀請東河戲劇團演出。劇團上演的《白蛇傳》《梁祝》《七姐下凡》《目連救母》等劇目,常演不衰,場場爆滿。觀眾對幸巧玉的喜愛可謂到了癡迷的程度,為了看她演戲,戲迷們晚上帶著席子睡在票房門口排隊買票,劇場前院落擺放著菜擔、糞箕、尿桶、獨輪車等。她回憶起下鄉(xiāng)趕廟會時的情景:“有一對白發(fā)蒼蒼的老夫妻,為了看她的戲,自帶干糧,一大早走十幾里的山路,有時餓了就在街上吃碗面條,夫妻倆喜歡東河戲的唱腔,喜歡戲里的故事”。對于戲曲表演藝術(shù)家來說,還有什么比老百姓的認可和贊賞更能讓他們感到幸福和欣慰呢?
三、藝術(shù)精湛 授徒傳藝
幸巧玉對唱腔藝術(shù)的理解,常常有自己的體會和感受。她說:“高腔是我們東河戲特有的本土聲腔,它的特點是唱腔高亢、音域跨度大,表演質(zhì)樸、曲詞通俗,具有濃厚的鄉(xiāng)土氣息。”為了讓筆者有更直觀的了解,她演唱了一段高腔目連中的《小尼思凡》一折,唱腔優(yōu)美、質(zhì)樸而不失韻味。
首先,在演唱上她很好地把握住高腔的行腔特點,這出戲音樂出現(xiàn)較多的五度、六度、七度等大跳音程,其中最低音和最高音的音域更是達到了十六度。她在唱腔旋律的處理上,根據(jù)自己的嗓音條件,大小嗓的結(jié)合,巧妙地加入潤腔和襯字,用她的話來說就是藝人們常用的“搭橋”,墊音的方式,從而使唱腔更加圓潤,婉轉(zhuǎn)細膩,更具有藝術(shù)感染力。比如《小尼思凡》中第一句唱腔“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年幼時削掉了頭發(fā)”,演唱時要把小尼姑內(nèi)心含羞的情緒表現(xiàn)出來,因此曲調(diào)唱腔不能唱得太重,速度上采用慢板形式,重視重音和滑音的處理,這樣才能獲得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效果。她還回憶了當年她學習《小尼思凡》時的情景:“這個戲是當時70多歲的師爺劉良格傳授于我,師爺身體不好,帶病傳授,唱一句停下來咳幾聲,就這樣半歇半咳的教下來。”說到這,她眼里泛著淚花,感慨萬千。日后這出戲也成為她在舞臺上的經(jīng)典劇目。
其次,幸巧玉十分重視對身段動作的設(shè)計。這得益于1956年她到北京參加中央文化部戲曲演員講習班的學習,當時授課的是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程先生為學員們示范了京劇的臺步、甩水袖、出場、做派等表演程式。通過這次學習,她吸收了京劇中許多優(yōu)美的身段動作,然后將其內(nèi)化,成功地運用于舞臺實踐。后期獲獎的劇目都能看到她對唱功和做工的重視,比如1957年主演的《豬崗寨》,獲江西省贛南地區(qū)戲曲會演優(yōu)秀表演獎;1958年主演的現(xiàn)代戲《黃崗風云》,獲江西省贛南地區(qū)戲曲會演優(yōu)秀表演獎;1960年主演的《昭君出塞》,獲江西省第二屆戲曲(青年演員)會演優(yōu)秀獎。當時的會演刊物給予了她很高的評價:“扮演昭君的演員能文能武、善唱善做……昭君剛出場就緊緊抓住了觀眾,她凄涼婉轉(zhuǎn)的唱腔和有條不紊的優(yōu)美動作,逐步將觀眾帶到了塞北沙漠那種一片孤城萬仞山的境界,演員最大的長處就是很少有矯揉造作之處,可見老師的真?zhèn)骱脱輪T的刻苦鉆研。”
她戲路頗寬,在傳統(tǒng)戲和現(xiàn)代戲中都塑造了不同的角色形象,無論是東河高腔《搶傘》中飾演的王瑞蘭,《尼姑思凡》飾演的小尼姑,東河昆腔《釵頭鳳》飾演的唐婉,東河彈腔《二度梅》飾演的陳杏元,《白蛇傳》飾演的白素貞,還是現(xiàn)代戲《雪山風云》飾演的黨支部書記,《蘆蕩火種》飾演的阿慶嫂,各有特色。真正做到了昆亂不擋,塑造的人物扮相俊美,嗓音甜美,唱做俱佳,表演細膩,成為贛南廣大戲曲觀眾最喜愛的東河戲演員之一。
新中國建立后,作為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東河戲表演藝術(shù)家,幸巧玉身上有著老一輩藝術(shù)家執(zhí)著、質(zhì)樸的精神,又有著新社會、新思想善于學習的品質(zhì),她的藝術(shù)生涯長達70載,黨齡超過60年,她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成長道路的艱辛,嚴格要求,態(tài)度認真,即使在教學上也是如此。22歲幸巧玉就開始收徒傳藝,她的大徒弟吳家珍和二徒弟梁瑞芳回憶起當年師傅教戲時的情景,反復強調(diào)說:“師傅告訴我們要重視基本功的訓練,先學小戲打基礎(chǔ),表演時要對人物傾注全部感情,仔細揣摩人物,做到貼近人物性格,重視戲曲程式的運用。”東河戲之所以能傳承400余年,就是與一代又一代的東河戲藝術(shù)家們虛心學習、身體力行、積極倡導密不可分。80年代中期,江西省電視臺來贛州錄制東河戲劇目,她參與錄制了《搶傘》《重臺別》《槐蔭別》等劇目,為后人留下了至今“活態(tài)”的東河戲唱腔音響資料。
結(jié) 語
總之,作為東河戲劇團極有成就的花旦演員,幸巧玉在流光溢彩的戲劇舞臺上,已經(jīng)磨礪了70個春秋,她懷著對戲劇藝術(shù)執(zhí)著的熱愛、刻苦不輟的性格,一生追求戲劇藝術(shù)事業(yè)的發(fā)展。2014年,東河戲列為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名錄,幸巧玉被評為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目前贛縣文化部門也在積極籌備“東河戲劇團”成立事宜,84歲高齡的她再次出山,收徒傳藝。2016年,贛縣東河戲參加“紀念湯顯祖逝世400周年”活動,其弟子謝華清主演的東河高腔《小尼思凡》得到專家的一致好評,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古老劇種重回舞臺之后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