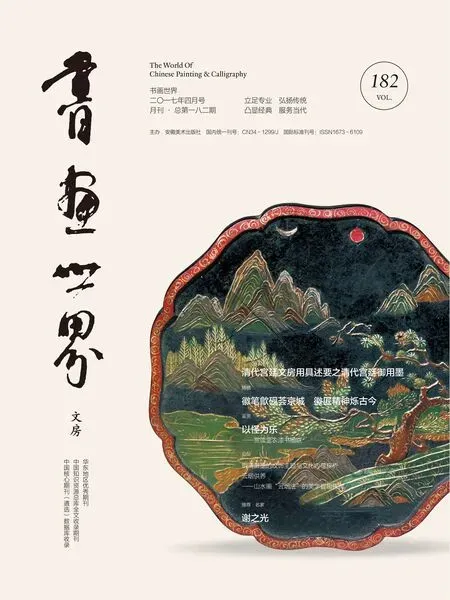云煙供養—山水畫“云煙法”的美學旨趣探微
文_任賽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
云煙供養—山水畫“云煙法”的美學旨趣探微
文_任賽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
山水之美,倘無云煙之供養,便會干澀枯燥。山水畫之美,正因有了玉帶纏繞,山嵐滋潤,山水林泉才變得嫵媚多姿、絢麗多彩。在山水畫的諸多技法中,除“樹法”“石法”“水法”“點景法”外,“云煙法”亦是尤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歷代山水畫家們最懂得云煙之于山川的重要,表現在畫作中就是:畫家們都十分重視對云煙的處理,力求將山嵐水霧運用得出神入化、妙趣橫生。所以,以山水畫之“云煙法”的技法運用和布局處理為切入點,就可以很好梳理和闡釋山水畫氣韻生動、云煙供養背后的審美內蘊和藝術旨趣。
山水畫;云煙法;氣韻生動;審美精神
一、引言
在中國山水畫技法中,除了“樹法”“石法”“水法”“點景法”之外,“云煙法”亦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歷代山水畫家都十分重視對作品中“云煙”的處理,因之也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審美經驗和創作理論。譬如,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山以水為脈,以云煙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云煙而秀媚”;再如元代畫論家湯垕在《畫鑒》中十分推崇“云煙供養”,在他看來,云煙之于大山而言,不啻是山之靈、水之魅。
總而言之,在山水畫里,云煙是不可缺的元素。表現重巒疊嶂的大山,如果有云煙穿插其中,一則能使畫面更加豐富,使構圖有分有合,避免直率,二則能使畫面有虛有實,于有限中見無限,得畫外之象。云煙對于山水作品來說,在氣韻生動與否這點上,雖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云煙法”的基本特征與表現技法
歷代山水畫家最懂得云煙對于山川之重要,在畫作中,畫家們都十分重視云煙的處理,力求將山嵐水霧運用得出神入化、妙趣橫生。比如,賀天健在《畫山水過程自述》中是這樣來區分各種狀態的云,就很有見地:
云—具有重厚質地或輕薄如帛者,但有時成一體系,能匯聚,能散布,能驅行如陣伍,能動掣像有帶領者,并且有時具有頭尾者。
氣—無動定的體系,無重厚的跡象,有時彌漫山間,有時飄搖而直上,在兩山之間的溪、澗、瀧、氿等水面上晨起有如鍋子里滾水沸動上冒出一股一股氣來一樣透到上面便凝結成云了。
霧—無跡象可見,但籠罩大地使人只有迷惘不清、眼力不足的感覺,它的力量可以使一切客觀實景、實物俱成模糊不清的現象。
煙—比云輕,比氣凝固,而有跡象,有時一縷上沖,有時成股橫馳,也能搏風如云,冒突而動,也能彌漫山谷,類如霧漾。
靄—早上雨后最容易見得到,它比煙輕,如果日光反映也像霞一樣色彩繽紛。常在山間、山邊或林表之際,如抹拂之狀或如涌現之狀。
嵐—山上蒸發之氣,不過這種蒸氣不是像云煙等是白色或黑色。人的眼睛看上去只覺得山上石上好像有什么氣籠罩或浮動其上,所謂嵐彩浮動的詞句可以表現它的質地和神情了。以上是對自然動態的說明。
一般而言,“云煙法”通常分為工筆和寫意兩類,大致可分為勾云法、染云法、勾染法以及空云法。勾云法分為小勾云和大勾云,小勾云多用于工細一路的青綠山水,大勾云法多用于粗筆大寫意山水。以墨線勾勒云流動或凝滯的狀態,有時再用白粉或赭石色復勾。如是比較工致的青綠山水,用淡墨細描白云,再用白粉細細提醒。水墨山水則多用空云法和染云法,或勾染并用。空云法即反襯法,借實見虛。在山石林木的點皴上著筆,于煙云處不著墨,而空白處留有云煙。清代戴熙說:“山石以畫而得,云水以不畫而得。山石成則云水自在。豈所謂名者實之賓乎?”染云法有內染、外染,由濃轉淡,漸漸承接,不露痕跡,有時可以用白粉渲染。漬染細分為墨漬、粉漬、干擦、濕染。漬染法是指不用墨線,單以墨色或彩色漬染而得。漬是在礬絹、半熟宣(或熟宣)上,在已經有墨色或色打底的基礎上暈染墨色,有一道比較明確的輪廓線。在繪畫時要根據宣紙或絹帛的生熟性質和需要表現“云煙”形態,相應地選取或并用云煙表現技法。云煙是一幅山水畫中的虛白處,而“實中虛白處,不論其大小、長短、寬狹,要能在氣脈上互相連貫,不可中斷”,否則便會散漫或凝滯。但“所謂氣脈上之連貫,并非將虛白之各個部分都連貫起來。實中虛白處,既要氣脈連貫,又要取得龍飛蛇舞之形,如此使實處既能通泄,也使通幅有靈動之感,更能使通幅有氣勢”。此外,上下云煙,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畫云煙用筆宜圓潤,運筆宜筆斷意連,多縈回交互,則筆勢靈動流走,具有飛動之意,切忌刻板。云煙的形態情致,皆是隨著氣候變化、季節變遷而不同:有的舒和閑適,有的飄揚清明;時而奔放濃郁,時而玄冥昏淡。同時也會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而各具特征。宋代韓拙在《山水純全集》里記載:“春云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云如奇峰,其勢陰郁,濃淡叆叇而無定也。秋云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云澄墨慘翳,示其玄溟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云四時之象。春陰則云氣淡蕩,夏陰則云氣突黑,秋陰則云氣輕浮,冬陰則云氣慘淡。此陰云四時之氣也。”從這些形象的比喻,可見山水畫中云煙的表現技法從中得到很好的借鑒,更能夠體現出繪畫技法秉承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畫理。
翰拙說:“夫通山川之氣,以云為總。”云煙在山水畫作品里的作用,大致可以從這兩方面說明。一是“通氣”。山水畫作品中的著墨部分通常以山石為主體,隨著山勢的走向附加樹木,注意脈絡的連貫,空白的部分“以云為總”。二是“助勢”。山石樹木是靜的,而云煙是相對動的,以云煙走勢助山勢,則山勢更加高峻崢嶸,正如郭熙《林泉高致》所說:“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煙霞鎖其腰則高矣。”俗語說“重若崩云”,即是通過大塊的云朵助其勢,寓動于靜。
一般意義上講,一幅山水畫中山石樹木部分往往是相對較實的部分,而云水則往往是相對較虛的部分。因此,煙云即可以起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作用。清代王概在《芥子園畫傳》中記載:“古人謂云乃山川之總,亦以虛無浩渺中藏無限山水皴法,故山曰云山,水曰云水。”由此可見,云氣的成功處理,對加強山水畫的詩意美、理想美的藝術創造,對于以有限的畫面去展現豐富的、無限的意蘊都起著重要作用。
三、“云煙供養”的審美內蘊與藝術旨趣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以山水畫之“云煙法”的技法運用和布局處理為切入點,我們就可以很好梳理和闡釋山水畫氣韻生動、云煙供養背后的審美內蘊和藝術旨趣。
眾所周知,山水畫自謝赫“六法”提出之后,第一為“氣韻生動”。山水畫家以“云煙”指代山水,不是云煙本身形態,所重是在氣韻。謝赫所指的“氣韻”之氣,既是對象精神狀態的表現,更是一種生命力的標志,而并非形態上的“氣”。“氣韻生動”是指表現對象的精神氣度要生動,山水畫中不僅僅要描繪出山石樹木、煙云、霧靄的外形,更要表現出它們的精神,也就是“造境”方可“形神兼備”,達到神似,氣韻才可以生動。
董其昌《畫旨》曰:“畫家之妙全在煙云變滅中。”清盛大士在《溪山臥游錄》云:“古人以‘云煙’二字稱為山水,原以一鉤一點中自有煙云。”似乎畫山水就是在畫云煙,將相對靜止的世界動起來。在《山水純全集》中,韓拙云:“凡云霞煙霧靄之氣,為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于此,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當順其物理也。”云煙霧靄,是山水之彩,就是山水的精華、山水的魂,沒有云煙,山水就失去了靈氣,畫出云煙霧靄,就是畫造化之真氣。
為什么說畫好云煙就畫出造化之真氣呢?因為“氣”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獨特范疇,在文學、中醫、風水等領域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不同于西方哲學,中國人有著獨特的氣化哲學思想。宋代張載 《正蒙·太和》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意謂“道”是物質變化的過程。《二程遺書》卷五云:“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意謂氣化而生萬物之后,各物種就能一代一代遺傳下去。清代唯物主義哲學家戴震:“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他將世界看成一團永恒的活火。清代王夫之《尚書引義·太甲二》云:“氣化者,化生也。”天地之間,萬物皆為氣結。通過聚散的形式表現為氣本體與個別存在物之間的轉化, 個體有生有滅,但氣無生無滅、永恒存在。正因為具體事物的生滅乃是氣之聚散, 這樣, 欲得“至實”之本體, 必須立于“太虛”。在山水畫創作中,這點體現在以云煙之“太虛”襯山水樹石“至實之本體”。
“云煙法”還滲透著道家哲學思想和審美觀念。道家研究天、地、萬物和人之間的規律。陳傳席在《中國山水畫史》中說:“老莊都無心藝術,但卻在不知不覺中對中國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對中國的繪畫,尤其是對中國的山水畫影響很大,這將在一部山水畫史中看得清楚。”道家的思想對山水畫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道”所蘊含的哲理,山水畫通過以景造境來體現“道”的哲理。
《老子·十六章》云:“致虛極,守靜篤。”《老子·二十六章》云:“靜為躁君。”《莊子·天道》云:“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家的哲學是主張“靜”的哲學,大致有三層意思:一是外在的靜,二是人們內在的平和坦蕩,三是道存在的狀態。而這三點又是相輔相成的。外在環境的“靜”可以幫助人們內心歸于平靜,內心的靜又是合乎道的。而內心的寧靜又決定了外在環境的安靜,對于一個內心寧靜的人來說,在喧鬧的外部環境也是安靜的。要想得“道”,人們首先要先靜下來。《老子·十章》云:“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具體做法為:“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排除感性經驗、語言概念和欲望的干擾,讓內心寧靜地體驗和直觀萬物,內守宇宙本源寂靜的本性,在萬物的生長、蓬勃、衰落中,觀察天道往復循環的道理。萬物在紛紜的運動中,各自都要返回到它們的根源中去。復歸到各自的根源就是寂靜,寂靜則是恢復了萬物的本性,復歸本性是永恒的規律。
清代笪重光《畫筌》有云:“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而靜氣不生。”山之靜氣,山水畫家往往用云煙來反襯。山水畫中的云煙通常表現霧靄、山嵐以造境,或是云煙蒸騰,或是云煙縹緲,或是云煙籠罩,云煙在牽引著山勢、山脈的走向,有云煙的遮擋,山色氤氳彰顯出氣勢。然而,虛靜之氣,并非死寂之氣。虛靜乃是動勢的本體,是真氣的積蓄,山水畫中虛靜之氣,乃是生動勃發之氣,是將真氣妙蓄于其間。《菜根譚》中對靜氣的闡釋:“晝閑人靜,聽數聲鳥語悠揚,不覺耳根盡徹;夜靜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頓令眼界俱空。”在虛靜之中,人與自然合一,一起復歸于靜,在“靜”態中,心靈“凈”了,從喧囂躁動的世俗中解脫出來,進入了天地萬物的寧靜狀態,人從物我兩忘再到更高層次上的物我合一。正如《莊子·天道》云:“言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之天樂。”這種“天樂”正是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美妙境界。
元代畫論家湯垕在《畫鑒》中講道,山水畫家離不開“云煙供養”。而云煙之于大山而言,不啻是山之靈、水之魅。山水之美,倘若沒有云煙之供養,只能是干澀枯燥的,正因為有了玉帶纏繞,山嵐滋潤,山水林泉才變得嫵媚多姿、絢麗多彩。
山水畫家最懂得云煙對于山川之重要。水墨氤氳中,畫家們把山嵐水霧運用得出神入化、妙趣橫生,從而創造出承載中國傳統哲學的山水畫藝術。如此說來,云煙不僅供養著山川秀色,也供養著一代代山水畫家。
[1] 謝稚柳.郭熙、王詵合集[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2] 童中燾.山水畫[M].杭州:西泠印社,1999.
[3]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4] 邱陶峰.賀天健畫山水自述[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5] 劉亞諫.中國畫道論[M].北京:中國書店,2012.
[6] 王伯敏.黃賓虹畫語錄[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