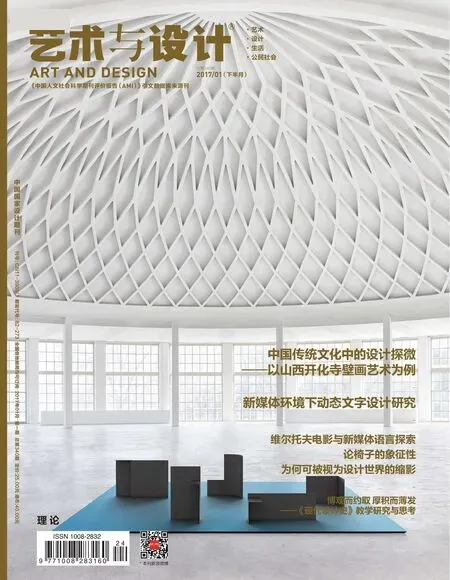都市空間中北京民俗藝術雙重狀態與應對策略
——以戲劇、廟會、民俗工藝品為例
張雯,胡春瀛,李晨宇
(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北京 100124)
都市空間中北京民俗藝術雙重狀態與應對策略
——以戲劇、廟會、民俗工藝品為例
張雯,胡春瀛,李晨宇
(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北京 100124)
高度城市化、國際化進程和現代傳播媒介的發展,使北京民俗藝術也向都市空間傾斜,越來越顯著地融合于城市的語境。原有的民俗藝術漸漸改變了曾經的存在環境,在當下都市環境下產生巨大變化,最為重要的標志就是呈現出雙重形態——一方面在逐漸消解自身,另一方面又在都市語境中形成了新的綜合的形態;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的運用與更新,應遵循在當下語境中發生的消解與重構的雙重狀態,采取與之對應的雙重策略。
北京民俗藝術;雙重狀態;應對策略
Internet :www.artdesign.org.cn
一、 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的當下運用
北京是一個既有悠久歷史又有現代國際化特征的雙重身份的都市,多年的建都史和深厚的歷史積淀,使北京擁有極其豐富的民俗藝術。同時,隨著高度城市化國際化的進程和現代傳播媒介在城市空間的發展,這些民俗藝術形式也隨之向北京都市空間傾斜,構成特定的都市民俗范疇,越來越顯著地融合于當下城市的語境與形態。
較為活躍在當下北京都市空間的民俗藝術大致可分為三類,包括以娛樂為宗旨的表演藝術,如戲劇、曲藝、相聲等,這是最為呈現北京都市文化特色的民俗藝術;也包括反映民眾生活民眾信仰的市井廟會民俗藝術,這是在北京都市比較普及并具有實用性的節慶民俗藝術活動;第三類是審美功能突出的美術工藝品,其品類繁多,有北京兔兒爺、京劇臉譜、北京泥人、北京布虎、北京風箏、北京皮影、北京木偶、北京風車、北京燈彩等。這三大民俗藝術種類并不能完全概括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的面貌,但是由于和當下城市生活以及和現代媒介比較容易結合,所以,相對普及地延續到城市生活空間,成為北京市內較為熟悉常見的都市化民俗藝術形式。
戲劇、曲藝、相聲等作為北京頗具代表性的都市化民俗藝術形式,和京城一直盛行以戲劇、曲藝娛樂內容的傳統有關,自金元以后戲劇興盛,演劇成為京城民間節日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節目,戲班也都有應節按節的戲。通常在正月初一,為慶祝春節,京城各劇場都要演戲慶祝。程瑞枯《都門元夕踏燈詞》詩云“幾盞琉璃敵夜光,燈懸天市數廊坊。梨園弟子翻新曲,一樣歌喉李八郎。”廊坊即今前門外之廊坊。詩中描述的就是此日前門一帶演劇的情景。①明清北京城是個“品”字的形狀,剛好在南邊突出了一部分,即前門至永定門包括天橋一帶,是各類表演類民俗藝術集中的場所。當下的北京天橋一帶,仍然顯赫地矗立著戲劇和曲藝的演出劇場,是北京市內重要的民俗藝術表演基地。
生機盎然的廟會民俗、節日慶典時盛裝表演的民俗藝術等,也隨著北京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從曾在鄉村和郊區繁盛的局面逐漸進入以都市空間為陣地的狀態。春節時期的廟會,在北京市區的幾大公園均有盛大場地,成為一年一度的大型常規民俗交易活動。還有一些表達民俗信仰的民間香會,本來活躍在北京的一些村落,如今也轉移到市內空間,成為北京市旅游觀光的重要節目內容。
民俗工藝品之所以成為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無論在都市還是鄉村,它們都是展現北京歲時節日、人生禮儀的民俗文化的重要載體。比如逢年過節在門上貼的民間藝術味道濃郁的年畫藝術、剪紙藝術,生兒育女贈送的紅蛋喜蛋的蛋繪藝術、八月十五拜月的兔兒爺等,這些民俗藝術在北京鄉村、都市四合院、社區都很普及,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既有傳承的形式,又有變異的元素,對城鄉的文化進行著融合,不斷形成新的共有的形式,體現了北京鄉村與都市民俗藝術整合的特征,它們縮小了城鄉的區別,聯系著北京民眾共同的生活愿望和趣味,不僅和“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北京精神相一致,而且,所蘊含的的熱鬧、喜慶、團圓、富足、平安、吉祥等形態,使抽象的北京人文精神得到了具體的呈現和審美的升華。
這些活躍在北京都市生活中的民俗藝術的分類,只是相對的區分,它們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交叉和互動的,比如戲劇曲藝需要生活習俗內容的參與,同時又融入北京的廟會民俗和節日慶典民俗之中,此外, 民俗工藝美術也與北京的戲劇曲藝、節日風俗有著不解之緣。比如北京的泥塑、臉譜、兔兒爺等,都是運用在戲曲、節日中常見的民俗元素。北京民俗藝術以展現民眾生活情景、寄寓民眾審美情趣為本質,融合在北京悠遠的傳統社會形態中,既是展現北京特征、北京味道的藝術形式,又豐富著北京社會、歷史、文化內涵,影響著社會民俗的變遷,進而間接地影響到社會精神與社會制度。
二、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當下的雙重狀態
作為中國首都的北京,在國際化和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經歷著最大程度的現代化重構,處在高速發展的國際大都市環境下的北京民俗藝術,也隨之接受著同等力度的的重新塑形。越來越多的民俗藝術進入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相融合,本身說明了它們逐漸被變異、被轉型、被重構的狀態,原有的民俗藝術漸漸改變了曾經的存在環境,在當下都市環境下產生巨大變化,其最為重要的標志就是民俗藝術呈現的雙重形態——一方面在逐漸消解自身,另一方面又在當下都市語境中形成了新的綜合的形態。
以北京傳統戲劇和曲藝為例:戲劇與曲藝都是方言藝術,戲劇與曲藝藝人運用方言口語發揮各種技巧,包括比喻、雙關、借代、諧音、諺語、俗語、夸張、歇后語和繞口令等,使民間藝術的口頭表現力特別豐富。更重要的一點是,方言是當地最樸實最貼近地方傳統的口語。老藝人說:“好曲走不遠”,是說方言的規定性。從方言的角度說,曲藝天生就是一種多樣性文化的演繹藝術。無論是京劇的鏗鏘聲勢還是越劇的吳儂軟語,各種形式的戲劇、曲藝藝人要讓觀眾感同身受,都要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和豐富的地方社會經驗去調動方言,方言對他們來說,是區域的行為規則和文化傳統,必須遵守,否則就會失去聽眾。②而今天隨著和國際接軌的需求,學英語、考托福、說普通話現象在北京普及,這種現象提升了北京作為首都的文化品位與形象,但是也造成了方言文化的生澀和瀕危。隨著表演藝術被市場化國際化,戲劇與曲藝需要面向世界范圍內的觀眾,戲劇和曲藝要用標準普通話演出。如果把戲劇曲藝一律改成標準普通話表演,傳統的戲劇與曲藝特色也就必然面臨轉型。一首膾炙人口的戲歌《說唱臉譜》,就反映了老北京人對于傳統戲劇既難以割舍又渴望創新的雙重愿望——“那一天爺爺領我去把京戲看,看見那舞臺上面好多大花臉……可唱的說的全是方言怎么聽也不懂,慢慢騰騰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這怎么能夠跟上時代趕上潮流,吸引當代小青年?……生旦凈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簡單,就連外國人也拍手叫好,一個勁的來稱贊,……就算是山珍海味老吃也會煩,藝術與時代不能離太遠,要創新要發展……”
普通話在北京都市的普及對于戲劇曲藝并不完全是沖擊,同時也是一種促使它們發生轉型與創新的動力。北京是世界文化中心,是世界留學旅居人士聚集之地,無論是旅居還是留學,都市民俗藝術都給他們提供了首選的入鄉隨俗的渠道,很多外國人為了強化漢語學習,在北京整體民風民俗的熏陶下,借助戲劇、曲藝和相聲藝術,提高漢語水平。中國戲劇、曲藝、相聲演員帶留學生弟子,擴大了民俗藝術的對外影響和交流,民俗藝術傳承經過多方人士的參與,增加了被外界了解關注的機會。戲劇和曲藝在立體多元的審視中,經歷著歷史的重新塑形。例如根據戲曲元素創作的《霸王別姬》《中華武術》,成為國內外流行的通俗歌曲,重新詮釋中華民族精神,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它們根據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新形勢和通俗歌曲表達的自由度,對民族傳統和現代文化的理解比重加以重構。從這個角度上說,戲劇和曲藝潛移默化地重塑著自身,在當下都市呈現一種時新的綜合的形態。
以節慶禮儀為載體的北京廟會民俗藝術的內容,亦隨著北京城市商業與近郊旅游產業發展的雙重影響發生變異。以北京朝陽區頗具影響力的民俗旅游村高碑店為例,它通過文化旅游的方式向世界展現北京特有的民俗習慣和藝術形式。高碑店具有國際知名的旅游品牌是村中百余年歷史的“高蹺老會”。傳統中高蹺會的民俗意義是期望通過“走會”這種活動形式,在村際交往中博得尊崇與艷羨,用村里老人的話表達就是走高蹺圖的是“耗財買臉”。耗全村之財、傾眾人之力所舉行的這種類似于狂歡的集體活動背后,承載的是高碑店人對“聲望”“權威”社會性情感的渴求。高蹺老會之于高碑店,不僅是歷史積淀中村落發展軌跡的標識,也是高碑店人對村落整體認同的象征。③在民俗旅游產業推動下,如今的高碑店高蹺會節日慶典的盛裝表演則變成旅客體驗民俗的一種手法,原來的民俗寓意逐漸淡漠,民俗風情的旅游越來越拋離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語境,原有承載的意義在漸漸被消解。
和戲劇以及廟會民俗藝術互動相關的北京特有的工藝美術品,如中秋節祭月的兔兒爺、慶賀春節的民俗燈籠、京味的臉譜、北京剪紙、北京風箏、彩蛋藝術,也在當代語境中改換著意義與形態。這些民俗藝術品本來有其明確的社會功能,如彩蛋是老百姓家中生兒育女的必備禮品,具有安康祝福寓意;兔兒爺為中秋增添了太平歡樂、幸福祥和的節日氣氛,具有強烈的社會功能。《清裨類鈔》記載:“京師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貴家巨室,多購歸,以香花餅果供養之,禁中亦然”。④兔爺既是審美工藝品,而且具有明顯的民俗意義,北京燈籠、鬃人等民俗工藝品皆是如此。隨著現代化潮流迅速改變北京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圣誕節、情人節等西方節日禮儀的傳入與傳統民俗節日交織在一起,不斷進行互動與同化,使北京民俗工藝品的社會功能在當代語境中發生變異,審美功能成為主要特征,民俗意義弱化了。為了強化審美功能,迎合當下審美標準,北京民俗工藝品的造型和樣式也發生了變異,如今天的北京臉譜、兔兒爺等,造型有了平面化、簡約化、卡通化的趨勢,加入對比強烈的現代色彩,嘗試融合到現代都市文化的背景里,審美功能超越了實用的功能,更多地成為國際國內前來北京觀光旅游人士的紀念禮品。
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延,北京都市民俗藝術越來越顯著地呈現一種共識的事實,即傳統民俗藝術內涵在整體生活傳承中快速地被現代生活方式肢解為碎片,但同時,這些傳統的文化碎片又在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斷地被重組與再造。北京都市民俗藝術也在這種必然趨勢下,呈現出消解與重構的雙重狀態。
三、 北京民俗藝術當下雙重狀態的應對策略
對于世界上各個民族來說,都面臨著現代文明與文化傳統對峙的嚴峻問題,傳承與創新民俗藝術的速度無法匹配當下文化進展的速度,是世界很多國家共同面臨的一個緊迫狀況。許多國家為此做出了相應努力,日本早在1950年政府頒布的《文化財保護法》中,就提出“無形文化財”(即包括民俗藝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韓國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著力于傳統民族、民間文化的搜集和整理;⑤意大利作為文化遺產大國,在文化遺產的志愿保護方面卓有成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一國際公約之所以通過,就是為了保持全球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從各國可借鑒的經驗來看,對于北京民俗藝術的保護傳承運用,必須尊重民俗藝術自身在當下消解與重塑的雙重特性,從而進行對應的雙重策略,對不同的民俗藝術進行理性的取舍。
(一)對應民俗藝術“消解”狀態的策略:對無法適應城市文化的北京傳統民俗藝術種類,應合理地運用博物館存檔與展示系統,從保護北京民俗藝術的角度來說, 理性進行取舍,利用博物館藝術館形式對無法進入“當下”的民俗藝術進行存檔與展示,其實是開發一種傳播形式,博物館具有保存與傳播、聯系歷史與當下的文化交流角色與功能,這種開發借用了民俗藝術的內核要素,開發的對象并不是民俗藝術本身,不造成對民俗意義的扭曲,而是民俗帶給全球的共享文化資源。北京應建立民俗藝術主題博物館,活躍各級國家博物館與國際公眾的交流,使國際公眾可以充滿興趣與理解地與北京民俗藝術接觸,都市語境下對于民俗藝術的創新與運用,應建立在更加能夠激活北京與當代世界交流的前提下,而不能為了保護傳統民俗藝術不忍取舍,反而禁錮了北京已融入世界當下背景的對外文化交流。
(二)對應民俗藝術“重塑”狀態的策略:促進北京民俗藝術中一些與現代世界理念價值相契合的元素成分的轉型,經過篩選和改造,形成新的適應當下的形態,轉化為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
北京近十年的城市改造,逐漸探索出民俗藝術、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發展新模式,規避了原來民俗藝術區改造方式的弊端。城市化的進程雖然使北京民俗藝術保護傳承工作變得緊迫,也使民俗藝術保護傳承的策略越來越趨向成熟清晰。如大柵欄的民俗街區改造,采用“節點更新、協議騰退”的方式獲取空間,更換了原來的“全盤拆遷”,保留了原始民俗藝術的創作空間。新的商業進入原來的街區,形成輻射帶動效應,引導現代元素介入了民俗創作,引進當代時尚設計師在對手工藝人傳統技藝、文化傳承的基礎上進一步設計,包括商標設計、投影墻裝置等,代表項目有“CAFA視覺傳達系學生與修車小鋪”“LINGO與兔爺張”“都市實踐與老張木板年畫”等。這些項目發揮了北京民俗藝人的話語權,激勵了民俗藝人創作主動性與激情,保護了北京民俗藝人創作權益和創作追求,使他們“活在當下”。從這些探索中可以看出當下對北京民俗藝術更新傳承的可行性。北京在積極參與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互動中,一些新的民俗傳承更新的策略也正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建立起來。
四、結語
歷史悠久的北京既是孕育民俗藝術的土壤,又是向世界呈現深厚民俗文化的窗口,作為首都城市,這一聞名的歷史古城有著幾千年的建城史和幾百年的建都史,具備調集全國各類能工巧匠進京的優勢,千百年融中華民族精華于一身,得天獨厚的條件構成了北京豐厚的民俗藝術文化底蘊。同時,北京作為國際化都市,快速接納全球文化風潮,更突出地呈現出既具有古老文化又具有現代氣息的雙重特征。致力于北京都市民俗藝術的傳承運用,并不是致力恢復都市化趨勢中已發生變化的民俗藝術的社會土壤,也不是致力恢復北京傳統風俗的原始面貌,而是遵循北京民俗藝術在當下都市環境中發生的消解與重構的雙重狀態,采取與之對應的雙重策略。■
注釋:
①李真瑜.戲劇與北京的民俗文化[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63.
②董曉萍.全球化與民俗保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
③康麗.從傳統到傳統化實踐——對北京現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續現狀的思考[J].民俗研究,2009(2):164.
④(清)徐柯.清裨類鈔[M].第1卷“時令類”.北京:中華書局,1984.
⑤馬蘭.全球化視野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1(6):417.
Dual Status of Beijing Folk Art in the Urban Spa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ake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Opera the Temple Fair and the Folk Artistc Craft
ZHANG Wen,HU Chun-ying,LI Chen-yu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24,China)
A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a in the city,Beijing folk art tend to the urban space and exists 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the city. Beijing folk art changed the original environment and has a huge change,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 is the dual status of present : on one hand,it dissolves itself in gradually,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formed a new integrated form. To protect and inheritance Beijing folk art,we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dual status of Beijing folk art in the present,to take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Beijing folk art; the dual status;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G127; J528
A
1008-2832(2017)01-0128-03
檢 索:www.artdesign.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