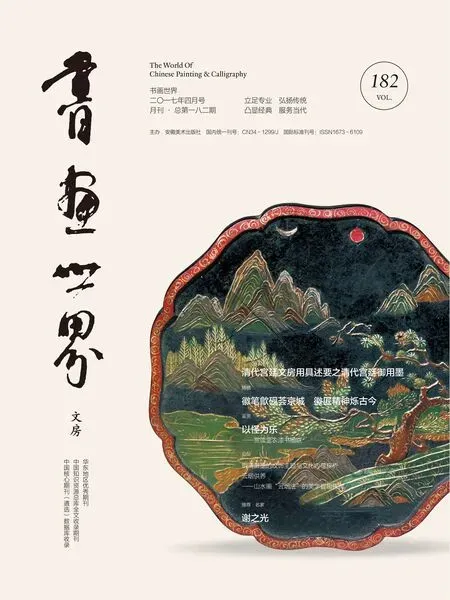蘇軾《黃州寒食詩帖》藝術(shù)風(fēng)格淺析
劉軍
廣西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
蘇軾《黃州寒食詩帖》藝術(shù)風(fēng)格淺析
劉軍
廣西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
《黃州寒食詩帖》被譽(yù)為“天下第三大行書”,不僅僅是因為蘇軾突出的文學(xué)修養(yǎng),更在于蘇軾卓越的書法功底以及“無意于佳”的書法意尚。本文以藝術(shù)風(fēng)格作為切入點(diǎn)分析《黃州寒食詩帖》藝術(shù)特征。
思想;藝術(shù)特征;對比
蘇軾是北宋時期的大文豪。蘇軾一生中在文學(xué)藝術(shù)的各個領(lǐng)域,有非常突出的建樹。譬如詩詞方面,他為后人留下了兩千七百多首詩詞,可謂卷帙浩繁,佳作如林;繪畫方面,他是“文湖畫派”的代表人物;在書法領(lǐng)域,他是“宋四家”之首,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另辟蹊徑,率先提出了“尚意”理論,并身體力行,證明自己的美學(xué)主張,創(chuàng)作出了經(jīng)典的行書作品—《黃州寒食詩帖》。
一、《黃州寒食詩帖》的創(chuàng)作背景
蘇軾(1037—1101),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蘇軾自幼聰慧異常,博覽群書。作為北宋的文學(xué)家、書法家和朝廷官員,其思想上受到儒釋道的影響,并以儒家文化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撐和最高的人生理想。其秉持書如其人的觀點(diǎn),“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這正是以儒家思想為依據(jù)的論書觀。
元豐二年(1079),蘇軾身陷“烏臺詩案”被捕入獄,后被貶黃州。蘇軾在黃州的三年,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使道家思想成為這一時期的精神支撐。元豐五年(1082),在寒食節(jié),聯(lián)想到自己的不幸,觸景生情創(chuàng)作出千古名篇—《黃州寒食詩帖》。
二、《黃州寒食詩帖》的藝術(shù)特征分析
在書法史上,《黃州寒食詩帖》向來以“天下第三行書”著稱。人們之所以如此推崇蘇軾的這件作品,乃是因為它本身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和突出的藝術(shù)特征。
(一)厚重而靈動的線條
在用筆方面,《寒食帖》中,每個字無不落筆沉著,行筆澀進(jìn),提、按、轉(zhuǎn)、折凝重,收筆圓融,筆畫雄渾勁健。蘇軾用筆多偏側(cè),行筆簡便,筆法隨意而出,其線條樸實(shí)無華,別具一格。《蘭亭序》雖有幾處涂改痕跡但書寫極其瀟灑自然,用筆多露鋒,正鋒與側(cè)鋒交相輝映;顏在創(chuàng)作《祭侄文稿》時情緒極度悲憤,錯訛之處,當(dāng)即涂改,用筆多藏鋒逆入,中鋒用筆,筆勢圓潤,情緒飽滿。“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xì)筋入骨如秋鷹。”由此可見蘇軾對王羲之和顏真卿書法的高度重視。就《寒食帖》而言,其筆法多取于顏真卿。
(二)寬博而多變的結(jié)構(gòu)
從結(jié)體上來看,《寒食帖》字多取橫勢,體勢寬博而多變。論及結(jié)字,黃庭堅曾用“石壓蛤蟆”的比喻,形象地勾畫出蘇字結(jié)體扁平的特點(diǎn)。在結(jié)構(gòu)方面的最顯著的特點(diǎn)是參差錯落。仔細(xì)觀察,可以看出前三行結(jié)字以扁平為主;第四行、第五行,結(jié)字緊密,筆畫肥厚的風(fēng)格體現(xiàn)明顯;至“蕭瑟”二字,筆勢放開,字形闊大,字形出現(xiàn)正斜交替變化。《蘭亭序》在結(jié)構(gòu)上同樣極盡變化,通篇作21個“之”字各有不同的體態(tài)美感,無一雷同;《祭侄文稿》結(jié)體多取橫勢,結(jié)體寬博,首尾變化明顯,正面表現(xiàn)了顏真卿悲壯波動的情緒。將三件作品進(jìn)行比較,則《黃州寒食詩帖》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便更加明顯。
(三)錯落而空靈的布局
就章法上來看,《寒食帖》行距舒朗,字距稍緊,但是在空間、結(jié)構(gòu)變化上又錯落有致。其中“年”“中”“葦”“紙”均為長筆畫線條,一方面給縱向空間帶來了延展性,另一方面,四字的位置安排也恰到好處,從而使整幅作品節(jié)奏感加強(qiáng)。《蘭亭序》章法自然,一氣呵成;《祭侄文稿》書面并不是很清爽,修改隨處可見,通篇書寫節(jié)奏由慢到快:開頭部分還能壓抑住內(nèi)心的情感波動,字形大小均勻,當(dāng)想起親人死難,便肆意揮灑,悲壯的心情表現(xiàn)淋漓盡致。由此可以推測顏真卿當(dāng)時書寫過程中情緒波動之大,蘇軾學(xué)習(xí)了顏真卿在《劉中使帖》中的章法布局,如“耳”字同樣使用長筆畫線條,筆勢迅速果斷,蒼勁古樸,意味深長。猶如錐畫沙一般,使其藏鋒,更顯沉著。
(四)濃稠而黝黑的墨色
蘇軾作書,喜用濃墨,《寒食帖》也是如此。用墨過多,極易產(chǎn)生“墨豬”,蘇軾卻能通過轉(zhuǎn)折處重按然后迅速轉(zhuǎn)折,產(chǎn)生一種凌厲、勁健的效果。加上墨色黝黑發(fā)亮,更是奇異誘人。《祭侄文稿》將渴筆枯墨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全文只蘸七次墨,用干枯的墨色變化來表達(dá)傷痛的情緒。墨色的干枯對比加強(qiáng)了藝術(shù)感染力,藝術(shù)效果同內(nèi)心的情感達(dá)到了高度的統(tǒng)一。同為“清四家”的劉墉和王文治,二人被后世譽(yù)為“濃墨宰相,淡墨探花”。想來兩人的用墨特點(diǎn),也無不受到了蘇軾《寒食帖》的影響。
三、結(jié)語
《黃州寒食詩帖》是蘇軾謫居黃州時真實(shí)的生活狀態(tài)的折射。蘇軾以橫溢的才氣和意造無法的筆意寫出了這篇詩卷,充分詮釋出了“無意于佳”是最好的書法創(chuàng)作狀態(tài)。清人宋犖曾評蘇軾此帖“偶然欲書,遂入神品”。蘇軾在評吳道子的畫時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這句話其實(shí)也完全可以用來評價蘇軾本人的作品。李澤厚曾在《美的歷程》中說道:“蘇軾在美學(xué)上追求的是一種質(zhì)樸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tài)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黃州寒食詩帖》也因此而流傳千古。
約稿、責(zé)編:徐琳祺、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