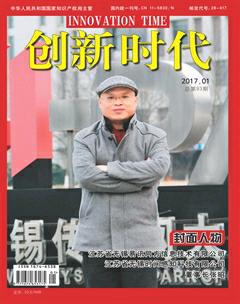2020年,我們與火星有個“約會”
在嫦娥探月工程不斷取得成功之際,越來越多的中國航天人和航天愛好者將目光投向火星。終于,2016年4月22日國防科工局局長許達哲在就中國首個航天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宣布了火星探測任務正式立項的重磅消息。
火星探測:一路坎坷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已經發射了嫦娥一號、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和嫦娥五號T1總計4顆探測器,未來還將發射嫦娥五號取樣返回探測器、月球背面著陸的嫦娥四號和地月L2軌道的中繼星,不僅過去的成就舉世矚目,更有未來的錦繡前程。相比之下,中國火星探測工程2016年才正式立項,未來更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個工程看起來是兩個階段的事情,很少有人留意到,其實中國的火星探測和月球探測幾乎是同時起步的。
探月工程正式啟動于2004年,嫦娥一號發射升空則是2007年10月24日。而早在2005年11月,中俄兩國總理定期會晤中就考慮制定聯合雙邊太空探索計劃,到2007年3月26日,兩國簽署聯合探測火星和火衛一的合作協議。根據中俄兩國的協議,俄羅斯將利用福布斯-土壤號是探測器空余的空間和運力,為中方搭載一顆火星探測器。這就是螢火一號的由來。
螢火一號:出師未捷身先死
螢火一號火星探測器是中國航天少有的國際合作項目,選擇借船出海而不是自力更生,是因為我們實在缺乏深空探測能力。舉例來說,當年中國發射的距離地球最遠的衛星是雙星計劃中的探測一號,由于火箭入軌控制問題,遠地點比原計劃高了一萬多千米!要向距離地球最近也有5500萬千米的火星發射探測器,長征火箭的導航制導控制系統恐怕暫時無法滿足需求。
即使火箭有可能改進以滿足需求,測控系統的不足也是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航天測控網絡當時只具備對地球軌道目標的測控能力,為了滿足嫦娥一號月球探測器的測控任務,要在喀什站和青島站各新建一座18米的統一S波段測控天線,還要借用中科院的大型射電望遠鏡通過甚長基線干涉(VLBI)技術進行測控。所以說,當時的中國從硬件到經驗都不支持開展獨立的火星探測。
深空探測具有全球性、科學性等特點,國際合作是其主流發展模式。前不久英國BBC采訪中國探月和火星計劃總師吳偉仁時,英國人不無惡意地評論,中國在合作日益增強的太空探測活動中被認為是一匹孤狼。這并不是我們閉關鎖國,而是被美國封鎖的困境使然。中國航天始終歡迎國際合作,螢火一號項目的實施就是一個范例。國際合作的螢火一號項目,有助于中國彌補能力和經驗的短板,多快好省地開展火星探測。國際合作對中國航天是有利和必要的,只可惜后來的發展可謂計劃趕不上變化。
即便有俄國人交流幫忙,火星探測對中國航天來說仍然充滿未知,無論是深冷溫度環境的控制還是超低剩磁的控制,或是超遠距離的測控和通信,都是不小的挑戰。但是上海航天八院在研制螢火一號探測器的過程中陸續解決了這些技術難題,用23個月就完成了一般5年才能完成的研制任務。
但遺憾的是,由于俄羅斯方面研制進度滯后,福布斯-土壤號探測器無法在2009年10月如期發射,發射日期推遲到大約26個月之后的下一次發射窗口。而更糟糕的是,2011年11月9日福布斯-土壤號探測器發射后,主發動機沒能進行啟動點火最后墜落太平洋,導致螢火一號探測器也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
螢火一號的失敗,雖然不是中國航天的原因,但仍給了中國火星探測當頭一棒。在嫦娥一號探測器的成功發射和中國航天技術全方位進步的鼓舞下,嫦娥一號總師葉培建等人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國應該獨立進行火星探測。
獨立火星探測:屢敗屢戰
繼螢火一號之后,獨立的火星探測方案不斷出爐,其中既有上海航天八院的螢火一號改進型方案,也有北京航天五院的嫦娥探測器改進方案。上海八院的方案中,火星探測器以螢火一號為主體,增加了推進巡航段,使探測器具備了獨立飛向火星和進行制動進入火星軌道的能力,還增加了兩個30~50千克的火星穿透撞擊器用于研究火星地質構造。北京五院的方案更為大膽,他們以嫦娥一號平臺為基礎,更換了用于火星探測的載荷,并增加了一個約50千克的小型試驗著陸器,將使用氣動剎車輔助減速進入火星軌道,驗證火星環繞探測和火星大氣進入、下降和著陸的技術,總體水平上類似歐洲的火星快車。
這些方案并沒有停留在紙面上,且不說上海成熟的螢火一號改進方案,北京五院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突破了火星測控通信的輕型應答機和輕質量天線,以及深空導航制導技術,還進行了火星著陸技術的研究,實際開展了軟著陸氣囊原理樣機的空投演示試驗。火星探測技術的研究同時使中國航天的運載火箭和測控網絡都有了巨大的發展,探月工程中長征三號火箭就改進提高了制導精度,而喀什站35米、佳木斯站64米專用深空測控天線的建成,也讓中國的深空測控能力有了飛躍性的進步。
遺憾的是,福布斯-土壤號探測器兩年的拖延和2011年的失敗,無情地粉碎了這一切,將中國火星探測計劃打入冷宮。然而中國科學家并沒有放棄獨立開展火星探測的希望,2011年后仍然不斷提出火星探測的倡議,但始終沒有得到國家批準立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印度的曼加里安號火星探測器于2013年成功發射并于2014年成功入軌。
或許是由于印度的成功,2013年中國航天火星探測的構想也有了較大的變化,從以軌道器為主外加撞擊器或試驗性著陸器,演進升級為軌道器、著陸器和巡視器三位一體,預定發射時間為2018年。
盡管從技術上看,火星探測對中國人來說已經不再遙遠,但國家始終沒有正式立項,而火星探測26個月一個窗口的限制,意味著錯過一次就要再等兩年多,于是計劃于2018年發射的火星探測繞落巡探測器,也只能推遲到2020年再發射了。
有優勢,有風險,也有機遇
2016年1月11日,中國自主火星探測項目終于正式立項。根據目前公布的消息,中國的首個火星探測器將是一個環繞、著陸和巡視結合的空前復雜的項目,其復雜度不僅超過了美國在航天競賽時代發射的水手號和海盜號探測器,也比歐空局的火星快車復雜得多。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就選擇了難度極高的繞落巡一體方案,這種選擇并非無的放矢。開展深空探測,既有航天競賽時代提高國家威望的理由,也有提升航天工業技術水平的需求,還有探索未知獲取新發現的意義。無論從哪個角度說,中國的繞落巡火星探測方案都有其必要性。
從政治上說,我們一直津津樂道于中國是第三個獨立掌握載人航天能力的國家,那么同樣備受關注的空間科學和深空探測領域,中國自然不能長期缺席。
2020年是一個火星探測的熱門年份,不僅中國和印度均有探測器發射飛向火星,美國的2020年火星車、俄歐聯合的地外火星車、阿聯酋的希望號探測器屆時也將發射升空,中國火星探測任務將吸引更多的關注并帶來更大的影響,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為了提高首次任務的成功率而簡化火星探測器設計。
繞落巡一體的設計看似十分激進,但仔細分析其跨度并不是太大:火星軌道器對今天的中國航天來說不是什么問題;火星著陸器的預研也一直在進行,除了2011年就已經進行過的氣囊緩沖試驗,2016年3月航天五院508所還進行了超音速降落傘風洞試驗;至于火星巡視器,玉兔號月球車面對的月球環境溫差要比火星苛刻得多,所以做一個能用的火星巡視器同樣不是太大的難題。
簡而言之,對于今天的中國航天而言,火星環繞、著陸和巡視探測技術都有一定的基礎,繞落巡一體探測可以發揮技術牽引作用,有利于以更少的經費更快地提高中國深空探測的水平,先發射驗證性的火星軌道器并非必不可少。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首次火星探測技術上最大的難點在于著陸,而最有科學價值的部分在于巡視探測,這個結合環繞、著陸和巡視的火星探測方案,兼顧了經費投資、工程技術和科研任務,這些都使得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更具難度和復雜性。雖然存在著一定風險,但也是目前形勢下最好的選擇。
中國火星探測的未來
中國的月球探測計劃循序漸進的繞落回三步走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2017年肩負月球取樣返回任務的嫦娥五號即將發射,那么火星探測又有怎樣的規劃和未來呢?
在中國航天和中科院早期的規劃中,火星探測同樣打算謹慎地進行繞落回三步走,但隨著技術和能力的提高,火星環繞和著陸探測已經合二為一,于是三步走也就成了兩步走,首次火星探測繞落巡任務完成之后,中國將進行空前難度的火星取樣返回任務。
火星取樣返回任務是火星無人探測皇冠上的明珠,它不僅具有極高的技術難度,花費同樣不菲。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進行了火星飛掠、火星環繞、火星著陸和火星車巡視探測,但在火星取樣返回任務上仍然充滿挑戰,而目前估算的高達50億~90億美元的任務開支,讓財大氣粗的美國航天局也不得不拉上歐空局聯合進行。
中國航天打算挑戰火星取樣返回這樣的旗艦級任務,可不僅僅是勇氣可嘉,而是認真開展了各種預研準備工作。目前中國長征九號重型運載火箭已經進入關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論證階段,重型火箭使用的500噸級液氧煤油發動機已在2016年8月完成首次燃氣發生器—渦輪泵聯動試驗,未來的重型火箭火星轉移軌道運力可達44噸,足以支持一次大型火星取樣返回任務。
火星取樣倒不一定非要使用SLS或長征九號級別的重型火箭,美歐聯合的火星取樣返回任務也提出過3枚宇宙神5型火箭或是一枚宇宙神5型火箭加一枚阿里安5型火箭的輕量級設計。2015年國際宇航大會上,中國投遞的論文中恰好也有類似的方案,即使用一枚長征三號乙或長征七號火箭加一枚長征五號火箭執行發射任務。總之,未來火星取樣返回任務的運載工具不會是個問題。
火星取樣返回任務中樣品的轉移一向是個難題,而在2017年的嫦娥五號任務中,中國就將驗證月球樣品的軌道轉移,在這項技術上中國遙遙領先于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其他國家。更有趣的是,2015年中國火星取樣返回的論文中,甚至直接借用了嫦娥五號的概念,提出使用一個330千克的鐘形返回艙攜帶火星樣品返回。至于火星取樣返回任務中的火星著陸和取樣技術,也將在2020年火星繞落巡探測任務和2017年嫦娥五號任務中得到驗證。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2020年火星繞落巡探測任務進展順利,中國將有望和美歐同步開展火星取樣返回任務,這將使中國的火星探測技術和能力達到國際領先水平,而包括嫦娥五號在內的一系列任務,將為火星取樣返回任務奠定堅實的基礎。
雖然前路依舊困難重重,但是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信心滿滿,為2020年與火星的“約會”做著積極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