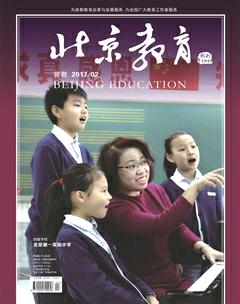重新理解教書育人
朱曉宏
[摘要] 時至今日,“讀書成人”早已是婦孺皆知的教育信條。教師也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境域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教書育人”的職業認同。但是,教書真能育人嗎?這似乎是一個未經審視的問題。檢視“教書育人”這一約定俗成的教師職業觀,由此引發的基本問題是教書與育人的關系,其前提問題則是知識與成人的關系。本文旨在重新理解“教書育人”,圍繞人與書的關系、教書與育人的關系展開論述,并依此反思“教書”與“育人”的割裂現象,明確提出“教書即育人”,期待課堂教學呈現嶄新之氣象。
[關鍵詞] 書寫文字;人類經驗;教書育人
教書育人,或許是每一位教師耳熟能詳的話語了。事實上,相當多的教師也比較認同此種關乎其職業特質的表述,但是,教書真能育人嗎?這似乎是一個未經審視的問題。蘇格拉底曾言,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依此理,似乎也有必要檢視“教書育人”這一約定俗成的教師職業觀。由此引發的基本問題是教書與育人的關系,其前提問題則是知識與成人的關系。若教師對此類問題缺乏教育學意義上的學理反思,似乎也不能理直氣壯地說其工作就是教書育人了。嚴峻的現實是,一些教師確實操勞于“教書”,但是,似乎無暇顧及“育人”。或許有教師否認上述推斷,認為自己在教書的同時確實考慮到教學生如何做人,但是,這種關于“教書+育人”加法式理解,難以厘清教書與育人的內在關系。因此,重新理解“教書育人”,似乎也不為過。
人與書的關系:人 — 符號 — 文化
縱觀人類歷史,人與書的關系有著綿長的敘事。書的歷史可追溯至“書寫文字”,但是,人類最早發明文字的目的不在于復制口語,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語無法完成的事情。目前,考古學家們能夠找到的人類祖先最早留下來的文字信息是“29086單位大麥37月庫辛”,這是遠古時期蘇美爾人的賬單,最可能的解讀是:“在37個月間,總共收到29086單位的大麥,由庫辛簽核”。[1] 對此,或許有人會失望吧。人類的書寫文字史既不是起源于哲學,也不是詩歌,而是無聊至極的財務賬目。事實上,這份文字是記載于大約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泥板上。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寫下文字是一件極其耗時的差事,哲思或詩歌等等,只能通過口頭語言,口口相傳。例如,希伯來《圣經》、古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佛教的《大藏經》、中國的《詩經》等,最早出現時都是口述作品。
誠然,隨著人類生產生活內容的不斷豐富,世界各地的人類祖先都不滿足于使用部分表意文字,逐漸發明了完整的表意文字。如蘇美爾人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已經擁有了完整的文字系統,今天稱之為楔形文字;中國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也擁有了完整的表意文字系統,即我們漢字的祖先——象形文字。從此,人們用這些完整表意文字來寫詩、寫戲劇、編史、發表預言,甚至記食譜等等。
在此,我們僅僅擷取了人類“書寫文字”歷史的若干片斷,就看到了人在宇宙間的神奇存在,即人能夠利用符號創造出一個文化大千世界。動物只能對“信號”做出條件反射,只有人能夠把這些“信號”改造成有意義的“符號”。所以,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將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2]。依據卡西爾的研究結論,書與人的關系呈現出了一個基本邏輯:“人—運用符號—創造文化”。因此,“人—符號—文化”是三位一體的。[3]
歷史地看,由于承載文字的工具的局限,完整表意文字創造之后,它與普通人的距離還相當遙遠。直至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并廣泛使用之后,“書寫文字”才真正走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近代以來學校教育的普及,“書寫文字”與每一個普通人的關系才日漸親近。當然,對于每一個具體的人而言,理解蘊涵于“書寫文字”(或符號)的意義,這絕非一個簡單的生物遺傳過程,而是一個復雜的教育和文化過程。
毋庸贅言,一個人只能通過后天的教育過程才能擁有識文斷字的能力。個體一旦獲得這種能力,透過書中的文字,顯現在其視域中的將是一個無限廣袤的“文化-意義”世界。這是符號的力量,也是文化的力量,更是教育暨人類文明延續的力量。與此對照,一個文盲的生活世界是多么有限啊。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強調“掃盲的目的并不是單純使一個不識字的人能夠識得幾個字,而是要使他更好地同他的環境協調一致,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義”[4]。
教書與育人的關系:
經驗傳承 — 個人生活 — 人類延續
承上所述,我們在人類歷史發展的視域中看到“書寫文字”作為人類創造的文化符號,承載了人類個體生活和種族生活的全部經驗,它包括習慣、制度、信仰、勝利和失敗、休閑和工作。這些經驗對于個體生存和種族延續固然十分珍貴,但是,人類生活的延續面臨兩個嚴峻挑戰:其一是人類群體生活中每一個成員的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即作為群體生活經驗載體的特定個體,總有一天會消亡;其二是這些符號化的群體經驗無法通過生物遺傳方式實現代際復制。
人類生活若要繼續下去,歷代社會成員所積累的經驗,只能通過成熟的成員與未成熟的成員之間的傳遞,才能夠保證人類族群的延續,這就決定了教育的必要性。換言之,人類生活的所有經驗包括符號形式的經驗,均不能像其他動物那樣通過生物遺傳基因實現代際相承。教育因此就成為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也只有教育能夠彌補人類先天不足的缺陷。對于人類而言,每一個新生的個體,生來就是未成熟的,孤弱無助的,沒有語言,不懂社會規則,更談不上擁有種族生活的各種觀念和信仰。這些幼小個體,先天遺傳的生存能力少的可憐,如果要生活下去就必須通過教導和學習實際經驗的代際轉換。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教育是生活的需要”[5]。他清楚地看到教育在個體生活和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未成熟個體與生俱來的能力與成熟個體生存能力之間的差距逐步擴大。一個孩子僅憑身體的生長和個體的直接經驗,都不足以支持其有品質的個體生活和高度文明的群體生活延續。社會正是通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使人成為人,并實現人類文明的代際傳承。記得筆者的碩士導師陳桂生教授在回憶其小學生活時,朗朗上口地誦讀其小學課本中的內容:“學生入校。先生曰:‘汝來何事。學生曰:‘奉父母之命,來此讀書。先生曰:‘善,人不讀書,不能成人。”后來,有機會一睹民國時期的老課本,果然有此段文字。頓時驚嘆于小學課本給一個孩子頭腦中留下的深刻印跡。由此可見,“不讀書,不成人”早已是民間婦孺皆知的教育信條。教師也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境域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教書育人”的職業認同。
在此,教書與育人的關系直接得以顯現。“書”直接承載著前人經驗或者說人類文明成果,“教書”即“教育”的日常語言表述,實為人類經驗或人類文明的傳遞。個人的生長與生活過程,也內在于人類生活和人類文明的延續過程之中。可見,成人過程與育人過程具有同一性,“讀書成人”與“教書育人”也因此具有內在一致性。
盡管如此,但是,不同時代的人們對于讀書與成人關系的理解似乎存在一定差異。一方面,生活在農耕時代的家長,他們把孩子送到私塾里,多數僅是指望孩子成年之后,能初通文墨,記賬,寫信,趕上春節寫寫春聯罷了,即使在科舉盛行時期,農村里雖有耕讀世家,但是,靠讀書成為秀才、舉人、進士的只占少數,《范進中舉》也只是出現在小說里的讀書人的傳奇故事。另一方面,從中國私塾里的蒙學讀物,到科舉取士的必修書目,多是圣人之言或儒家經典;從西方教會主日學校的《圣經》讀本,到文法學校里的必修書目,也多是西方社會的人文經典。從這一時期中西方的書本知識里看,內容上都直接關乎人的道德形塑,“教書育人”的內在關聯是不言而喻的。
以學校為標志的制度化教育產生之后,人類的生活和生產經驗或者說人類文明成果系統地進入基礎教育課程,并以諸多科目的書本形式出現在兒童面前。以學科課程為例,大致分為理科、文科、藝體等。與之相應,課程的系統化程度決定著教師之教的專業化取向,中學教師多按學科分工,如數學(學科)教師、語文(學科)教師、物理(學科)教師等等。由此引出的問題是,教師的“教書”行為失去對書中意義世界的關照,換言之,“教書”與“育人”的聯系被人為地割裂。
對于語文、歷史和思政①三科教師而言,課本內容與學生的道德成長直接相關,這些教師的觀念中也多有“文以載道”的意識,“教書育人”似乎是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但是,一些教師或許太在乎教“書”中的“道理”了,忘卻了“書”中的意義世界,而意義只能在兒童的直接經驗中綻放。與此同時,理科教師或許不認可上述同行們的“道德說教”,但也糾結于如何滲透德育。他們在教學中的通常做法:一是注重與教學內容直接相關的某位科學家廢寢忘食的鉆研精神;二是在教學過程中不時給學生講些做人的道理。對此,一方面要理解這些教師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里的“教書”與“育人”已然成為兩件事了。
基于前文中闡明的“人與書的關系”,教師有必要深刻理解學科課程作為人類生活的特定文化符號所承載的意義世界,以及其對于學生成人的內在價值。杜威就曾在其論文《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提醒關注“學科的社會性質”[6],并強調學科教育必須與人的自覺經驗發生關系。以此反思當前的學科教學,過于關注學生掌握概念性知識的能力,卻遮蔽了這些學科知識產生之初與人類經驗的直接關聯,即忽視了“教書”對于學生成人過程的文化意義或社會價值。
師者何為:教書即育人
關于師者何為的話題,韓愈的“傳道、授業、解惑”早已被廣大教師津津樂道,也常被用來作為“教書育人”的注腳。“教書育人”也被寫入我國頒布的師德規范①之中。但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的學校教育作為一種制度化教育存在形式,與韓愈時代的非制度化教育相差甚遠。盡管教師在觀念上認同教學是“傳道、授業、解惑”,行動上卻實實在在地傾向于傳授掌握知識之“術”,而書寫文字作為文化符號所承載的意義世界似乎已經遠離師生的生活世界。
事實上,書寫文字中的“道”即意義世界,是人類經驗的精華所在,并以基礎教育課程的形式進入中小學教科書。在這些書本中,“經驗與知識是統一的,不是二元的。”[7]表面上看,不同科目的教科書里包含不同領域的知識,實質上,“這些知識本身就是經驗,它們是種族的經驗。它們體現了人類一代一代的努力、斗爭和成就而積累起來的結果。”[8]這其中蘊涵著波瀾壯闊的人類生產和生活實踐,換言之,這些知識里蘊藏著色彩斑斕的意義世界。因此,教學不是教知識本身,而是通過間接經驗影響學生的直接經驗,促進其個人經驗的改善。換言之,用人類文明照亮兒童心靈。遵循此理,教育學意義上的“教書”即以直接經驗的方式引導兒童進入人類的間接經驗,并以此改善其直接經驗,進而提升其心智水平,即實現課程的“育人”價值。這也契合德國教育學家赫爾巴特主張的“教育性教學”[9]。
在赫爾巴特的時代,“教之學”(即教授)與“教育之學”是兩個概念。他在解釋德語“教育”概念時指出,“教育”這個詞是由“訓育”和“牽引”兩個詞來的。據此可知,德語“教育”的基本含義有二:(1)引出,即它是一種內發的活動;(2)內發有一種方向(近于訓育,即對青少年的心靈產生直接影響,有目的地進行培養)。[10]同時,赫爾巴特充分認識到個體有限的生命阻礙其獲得無限經驗的可能,指出“教學作為經驗與交際的補充”[11],并與訓育共同構成真正教育的措施。因此,赫爾巴特指出,一個青年人純粹出于得到好處的目的向教師學習本領和學識,這是無關緊要的,關鍵是其思想的形成,這對于教育者來說就是一切。[12]若將這番話轉換成今天的教育學話語,“教育性教學”就是要通過基礎教育課程的教學養成兒童的世界觀,即課堂學習在兒童狹小的個人世界與宏大的人類文明世界建立起直接關系。具體到教學的操作層面,“教育性教學”就是“教書即育人”,即在教學過程中用人類文明開啟學生的心智,通過改善學生的思維水平來提升其意識品質。
試想一下,如果教師的視域中存在“人—符號—文化”的關系,他們就能夠從書本世界中觸摸到前人的生活世界,進而能夠自覺地透過教科書中的知識直觀到人類經驗的流變。此時,知識不再是簡單的、靜態的抽象物,而是“處于運動狀態中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知識是一個能動的過程,它并不存在于抽象的思想中,而是融在人的欲望、意志、行動甚至整個生命之中。”[13]由此可見,中小學基礎教育課程中的各科知識都不是外在于學生個體的概念式真理。
這些書本知識是前輩的直接經驗,凡是經驗一定有著內在的生命力,即知識貢獻者個體的求索體驗。教學一定要打開概念化知識,喚醒知識的原初意義,即讓間接經驗以直接經驗的方式呈現在兒童的生活世界,與兒童的直接經驗接軌。這樣的“教”能夠在兒童與課程之間真正建立一座心靈之橋。通過這座橋梁,教師引領兒童走進內涵豐富的人類文明世界。兒童的視域由此朝向人類經驗建構的精神世界,沿著人類文明之階梯,他們探索著走向一個光明的未來。
總之,教書即育人,理應成為當代教師的職業信念,并由此展開其日常教學的豐富樣式。這樣,教師就擁有了全新的知識觀、全新的教學觀,并能夠自覺運用前人的間接經驗改善學生的直接經驗,課堂教學也將呈現嶄新氣象。至此,求知、愛真理、追求光明,將內化為兒童真實的學習生活體驗,而非校園里的標語或口號。
參考文獻:
[1][以色列]赫拉利著.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M].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1.
[2][3][德]卡西爾著.人論[M].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5、12.
[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編著.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65.
[5][美]杜威著.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7.
[6][美]杜威著.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M].趙祥麟,任鐘印,吳志宏,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53.
[7]滕大春.杜威和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下)[J].河北大學學報,1996(1).
[8][美]杜威著.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M].趙祥麟,任鐘印,吳志宏,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20.
[9][10][11][12] [德]赫爾巴特著.普通教育學·教育學講授綱要[M].李其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3、159-161、68、13.
[13][美]哈特著.從信息到轉化:為了意識進展的教育[M].彭正梅,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50.
本文系北京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兒童學校公共生活體驗研究》(課題編號3059-0002)的階段性成果
編輯 李剛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