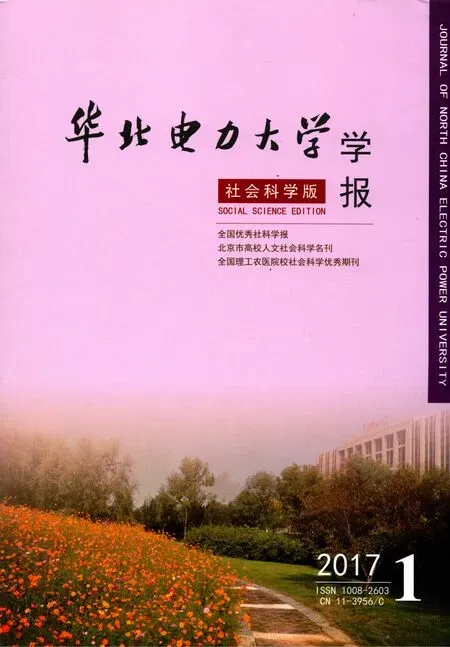論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
趙金偉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
● 法學前沿
論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
趙金偉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對于是否構成犯罪、審查重點與判斷順序以及正確量刑均有重要的意義。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標準應當綜合身體動靜、規范評價、法益狀態等標準,采取“兩步走”從形式到實質、外在到內在的分層次遞進式思考進路。第一步運用身體動靜說作為判斷標準,當第一步的判斷難以得出妥當的結論時,就需要第二步運用規范評價說的標準。規范評價說中規范“基點”的選擇可謂是重中之重,規范“基點”的確定應當考慮義務和法益兩個要素,即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其所履行的義務,侵害和威脅法益的行為究竟是作為還是不作為。行為人的義務是確定規范“基點”的前提所在,可分為監督義務、阻止義務和保護義務。當作為與不作為發生競合時,行為人主動設定因果流程,使法益狀態惡化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禁止規范”,行為人的不應為而為就可能構成作為犯;行為人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流程,沒有使法益狀態好轉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命令規范”,行為人的應為而不為構成不作為犯。
作為;不作為;法益狀態;規范評價說;身體動靜說;犯罪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1:2009年2月9日,被告人文某的妻子胡某因病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胡某在治療期間處于昏迷不醒的狀態,需借助呼吸機維持呼吸,醫院向文某發了胡某的病危通知書。胡某住院接受治療七日后,文某到醫院探視時,將胡某身上的呼吸管等醫療設備拔掉,同時阻止醫護人員對胡某進行救治,胡某于當日死亡。經法醫鑒定,胡某因被拔去呼吸管后所導致的呼吸停止而死亡。2010年深圳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文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檢察機關向二審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廣東省高院終審裁定,維持深圳中院的一審判決。[1]
案例2:2015年10月31日,阿林母親朱某在眉山城區一處人行道正常行走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倒,后被送往醫院搶救。經搶救,朱某恢復心跳,但需借助呼吸機維持呼吸,生命體癥處于腦死亡狀態。11月2日,阿林進入重癥監護室將母親朱某鼻子上的呼吸機管拔掉,并阻止醫護人員對朱某進行救治,朱某于當日被醫院宣布臨床死亡。經法醫鑒定,朱某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引發呼吸循環衰竭而死亡。公安機關以阿林涉嫌故意殺人罪立案偵查,并對阿林實施了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2]
案例1中的文某與案例2中阿林的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但二人的行為究竟是作為的故意殺人罪,還是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則存在著爭議。有觀點認為,醫生發現病人救助無望,而將維持被害人生命的呼吸機關掉的,評價的重點不在于行為人的身體動作,而在于醫生不履行對病人的救助義務,因此成立不作為犯;病人家屬關掉該呼吸機的,則屬于違反禁止剝奪他人生命規范的情形,成立作為犯。[3]但為什么醫生關閉呼吸機是不作為犯,而病人家屬關閉呼吸機就構成作為犯,該觀點只是以規范評價為由而一筆帶過。在通常情況下,病人家屬簽署放棄治療同意書,由醫生關閉呼吸機的,則病人家屬與醫生均不構成犯罪。可見,醫生的救助義務來源于家屬的救助義務,否則,醫生沒有必要征求病人家屬的意見后再關閉呼吸機。那么,在病人家屬與醫生同樣具有救助義務,同樣是關閉呼吸機的積極身體動作的前提下,二者究竟是構成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亦或是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呢?為什么關閉呼吸機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卻可以從輕判處緩刑呢?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需要以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為前提。作為與不作為區分的意義主要在于:(1)由于刑法以處罰作為犯為原則,以處罰不作為犯為例外,所以,作為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大于不作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行為人的行為能否構成犯罪。(2)對審查重點與判斷順序具有影響。在不作為犯中,審查的重點是行為人是否處于保證人地位;而作為犯中則不需要進行保證人地位的判斷,只需重點審查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即可。(3)一般而言,不作為犯的不法與責任要低于作為犯。[4]也正因為如此,德國刑法第13條第2款規定了不作為犯可以減輕處罰。而且,不作為犯的審查判斷一般情況下要遠比作為犯復雜得多,因此,在不真正不作為犯中應當如何認定該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成為重大課題。[5]具體來說,不作為犯除了要進行保證人地位的判斷之外,還要積極地判斷作為可能性、結果回避可能性、作為與不作為的等價性等。可見,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對于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審查重點與判斷順序、案件的正確量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到案例1和2而言,行為人若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則需要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然后再進行作為可能性、結果回避可能性、作為與不作為的等價性等方面的判斷;反之,則只需要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而且,如果認定行為人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因為不作為犯的不法與責任輕于作為犯,就有可能適用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予以量刑。若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作為的故意殺人罪,能否適用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予以量刑,則需要另辟蹊徑。因此,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可謂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直接關系到案件的正確定罪量刑。本文將結合案例1、2的討論,對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展開深入地研究和探討。
二、作為與不作為區分的主要學說及檢討
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在一般情形之下并不困難,通常有積極之身體動作即是作為,以消極身體動作聽任事件發展者是不作為。如,行為人用刀捅刺被害人胸部的行為,毫無疑問地是作為;母親不給嬰兒喂奶的行為也肯定是不作為。前者成立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后者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但在案例1、2中,行為人同一時間的行為究竟是屬于作為亦或不作為,則會存在判斷上的困難。我們既可以說,行為人拔掉患者呼吸管的行為是不履行救助義務的應為而不為的不作為,還可以說,行為人拔掉患者呼吸管的行為是提前結束他人生命的不應為而為的作為。可見,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在特殊場合可謂是非常困難,理論上對此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為與不作為區分的主要學說有:
1.身體動靜說。該說由因果行為論衍伸而出,將行為理解為身體的外部動作,在區分作為與不作為時強調身體在物理上的動和靜。如,德國學者貝林格將不作為定義為:“不使筋肉作相應運動。”[6]就身體動靜說而言,在大多數場合,作為犯表現為身體的動,而不作為犯則表現為身體的靜。但在某些場合,不作為犯又具有積極的身體活動,身體動靜說在此就喪失了用武之地。如,我國刑法第201條的逃稅罪,行為人應當繳納稅款而不繳納,就屬于應為而不為的不作為犯罪。但行為人為了不繳納稅款而通常有積極的身體活動,如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等,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在案例1、2中,行為人拔掉患者呼吸管的行為按照身體動靜說應當是作為,但因為行為人對患者負有救助義務,也可以被評價為不履行救助義務的不作為。因此,不能簡單地以身體的動靜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
2.因果關系基準說。該說認為,作為是引起了結果的行為,而不作為是沒有引起任何現象的行為。因此,作為和不作為的區分,應當根據行為自身對外界影響的角度來進行。從現象上看,作為是以積極的身體活動對外界產生影響,而不作為是以消極的身體活動放任外界的某種變動。因此,作為使外界發生一定的變動(結果),而不作為是放任外界發生一定的變動(結果)。換言之,作為對結果具有因果性(原因力),而不作為則不具有這種因果性。[7]因果關系基準說主要是從因果流程的角度,從實行行為與法益侵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作用力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該說存在的疑問是,行為對結果有無原因力有時會是難以確定的事;而且,根據該說只能以未遂犯處罰不作為犯,或者認為不作為犯是行為犯,這恐怕難言妥當。[8]
3.法益狀態說。該說認為,作為使法益狀態惡化,不作為使法益狀態沒有好轉。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主要取決于行為與外界所發生的法益侵害或危險之間的關系。換言之,在原本不會發展至法益侵害的場合,行為改變事態進程,使其指向法益侵害的,就是作為;在已經指向法益侵害的場合,行為不改變事態進程,任其發展為法益侵害的,就是不作為。[9]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或威脅法益,法益狀態說從犯罪本質的角度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無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某些場合則不能適用。如,拒不救援案,甲把繩索放到井底,然而就在乙抓到繩索之前,甲又把繩索抽回來,結果乙溺斃于井底。那么,甲的行為究竟是使法益狀態惡化,還是使法益狀態沒有好轉,就難以區分。顯然,法益狀態說在此場合未能給出明確的答案。
4.規范違反說。該說區分作為與不作為是以行為違反禁止性規范亦或命令性規范作為標準。我國刑法學的通說采取的就是規范違反說,同時輔以身體動靜說。通說認為,作為是指行為人以積極的身體活動實施的違反禁止性規范的危害行為;不作為是指行為人以消極的身體活動違反命令規范,能履行法律賦予其的義務而不履行的危害行為。[10]規范違反說作為我國刑法學的通說,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某些場合,規范違反說也難以得出肯定的結論。如,艾滋病感染案中,患有艾滋病的行為人與其伴侶發生性關系,而且其明知可能感染伴侶仍然放棄使用所要求的安全套,結果使伴侶受到了感染。在該案中,行為人沒有戴安全套的行為可謂是違反了命令規范,與性伴侶性交的行為可謂是違反了禁止規范,那么行為人的行為究竟是作為還是不作為呢,規范違反說對此顯然不能正面回答。
5.義務內容說。該說認為,當行為人的義務內容是不作為時,其違反義務內容的行為就是作為;當行為人的義務內容是作為時,其違反義務內容的行為就是不作為。詳言之,對于制造風險的行為而言,法律會賦予行為人不作為的義務,期待行為人不為一定的行為,而行為人違背不作為義務的行為就是作為;在既存風險的情形下,法律會將作為義務賦予行為人,期待行為人消滅風險的作為,而行為人違背作為義務的行為就是不作為。[10]義務內容說存在的疑問是,義務內容具有相對性,同時也沒有回答如何選取行為人的義務內容以區分作為與不作為。如,山羊毛案中,一個工廠主把受到炭疽桿菌污染的山羊毛發給工人進行加工,四個女工因此死亡。對此,人們既可以說,工廠主的義務內容是給羊毛消毒,也可以說工廠主的義務內容是不向工人提供未經消毒的羊毛,那么,工廠主向工人提供未消毒山羊毛的行為既可以評價為作為,也可以評價為不作為。
6.非難重點說。該說按照社會意義、譴責方向或者可譴責性的重點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占據了德國司法審判的主流觀點。該說源于德國學者梅茨格爾,強調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的區別不能根據具體案件的外部形態,而只能根據在法律上的指責針對的究竟是什么。換言之,這個區分“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評價問題”。[11]非難重點說顯然沒有回答何為譴責的重點,沒有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適當的標準。該說可謂是在沒有足夠基礎根據時就預先得出的結論。[12]例如,駕車未點燈案,行為人夜間駕駛汽車,因為未點燈視線不良而撞傷行人。當時的情形,如果點燈,可以確定不會肇事。那么存在的問題就是,既可以非難未點燈的行為(不作為),又可以非難其開車沖撞的行為(作為),那么何為非難的重點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7.規范期待說。作為的實質是行為人違反法律對其“不要做”的期待:只要不實施法律禁止的行為,行為人做其他事情都可以。不作為的實質是不實施法律期待其實施的行為。區分作為和不作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某一身體行動從規范評價的角度具有何種意義。雖然實施了某一行為,但規范期待行為人通過作為行為來保護法益,行為人仍然違背規范這一期待的,就是不作為。[3]107規范期待說面臨的問題在于,沒有正面回答什么時候規范期待行為人作為,什么時候規范期待行為人不作為。
此外,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的學說還有能量說、社會意義說、最終原因說、價值說等。[13]能量說以是否投入能量區分作為與不作為,投入能量的是作為,反之就是不作為,投入能量的同時會引起外界相應的變化。社會意義說根據行為的社會意義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如果行為的社會意義是引起結果就是作為,不防止結果的發生就是不作為。最終原因說根據行為與法益侵害結果的遠近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與結果最接近的原因是作為,就認定犯罪行為是作為,反之,則是不作為。價值說根據價值判斷區分作為與不作為。能量說其實是與身體動靜說相當的一種學說,積極的身體動作可謂是注入能量的作為,而消極的身體動作就是沒有注入能量的不作為。[14]既然如此,能量說也會面臨著與身體動靜說相同的問題。最終原因說與因果關系基準說一樣,均試圖從因果流程的角度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該說除了與因果關系基準說面臨同樣的問題外,還會面臨的疑問是,在某些場合離結果最近的原因即使是作為,也可能被評價為不作為。如,我國刑法第202條所規定的抗稅罪,離結果最近的原因是暴力、威脅行為,但抗稅罪通常又被認為是不作為犯。至于社會意義說、價值說而言,則與非難重點說一樣,可謂是也沒有提供適當的標準。
作為與不作為在大多數場合的區分可謂是一目了然,但在某些特殊場合可以說是非常困難。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大概有十余種學說,可謂是紛繁復雜,令人眼花繚亂。這些學說從不同角度對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了標準,但上述區分標準之間不一定是對立關系,有些學說只是表述上的不同,這些學說大體可以分為身體動靜、法益狀態、規范評價等三類。身體動靜屬于外在和形式的判斷標準,而法益狀態與規范評價則屬于內在和實質的判斷標準。身體動靜的標準主要是從身體的物理動靜以及行為引起外界變化等角度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具體包括身體動靜說、能量說等。因為是從物理動靜、外界變化等顯現于外的因素來判斷作為與不作為,比較容易觀察與判斷,并且能夠為大多數場合的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標準。但正如前文所述,身體動靜的判斷僅僅是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了外在與形式的標準,難免會得出不妥當的結論。在此情形下,便不得不依靠規范評價和法益狀態這兩個內在和實質的標準。規范違反說、非難重點說、義務內容說、規范期待說、社會意義說、價值說等學說的核心在于規范的評價,可謂是規范評價說不同角度的表述。例如,規范違反說根據行為違反禁止規范亦或命令規范對作為與不作為二者進行區分,義務內容說是從行為人違反作為義務亦或不作為義務的規范內容來區分二者,規范期待說是從規范期待行為人“要做”或“不要做”來區分二者,非難重點說是從規范譴責的重點來區分二者,可見,盡管名稱有所不同,都是從規范評價方面為作為與不作為提供判斷標準。規范評價說的爭點在于以什么樣的標準,亦即,規范的“基點”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例如,山羊毛案中,如果將規范的“基點”確定為工廠主有義務給羊毛消毒,或者說,法律期待工廠主給羊毛消毒,那么,工廠主向工人提供未經消毒的羊毛的行為,就可以被評價為不作為;如果將規范的“基點”確定為禁止工廠主向工人提供未經消毒的羊毛,那么,工廠主向工人提供未經消毒的羊毛的行為,就可以被評價為作為。因此,規范評價說面臨的主要問題就在于如何選擇規范的“基點”作為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的標準。因為規范評價難免會融入判斷者的主觀色彩和價值判斷,表現在規范“基點”的選擇上就會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局面,其結論就可能因人而異。也正因為如此,規范評價說內部的非難重點說、規范期待說等學說往往就面臨著沒有提供適當標準的質疑。因此,規范“基點”的選擇是規范評價說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果關系基準說、最終原因說雖然是從因果流程的角度出發,但最終落腳點仍然放在法益狀態的判斷上,因此,因果關系基準說、最終原因說和法益狀態說的核心一樣,在于法益狀態的判斷,可謂是法益狀態說不同角度的表述。因為法益侵害結果是實際存在的,無疑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單獨依據法益狀態惡化與好轉與否,顯然在某些場合不能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適當的標準。如前文所述的拒不救援案中,若不聯系行為人的作為義務,就會很難判斷法益狀態的惡化與好裝與否。規范違反說與法益狀態說無疑都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了內在和實質的標準,但這兩種學說應當以何種學說為準,同時彌補該學說的不足,也是作為與不作為區分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作為與不作為區分標準的確定
鑒于任何單一的作為與不作為區分標準都存在問題,綜合身體動靜、規范評價、法益狀態等標準,采取形式到實質、外在到內在的思考進路勢在必行。具體來說,作為與不作為區分的思路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形式和外在的判斷,第二步是內容和實質的判斷,因為在絕大多數場合形式和實質、外在與內在呈現出一致的狀態,所以,也就僅需進行第一步的判斷。換言之,第一步能夠得出妥當結論時,就無需進行第二步的檢驗。但以外顯的行為態樣有時會難以區分作為與不作為,尤其是在多重行為方式的場合,更是如此。[15]399因此,在部分場合當第一步的判斷無法得出妥當的結論時,就需要進行第二步的檢驗。可見,采取“兩步走”的思考進路,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能夠使判斷更加準確。第一步形式和外在的判斷中,主要根據身體動靜來區分作為與不作為,消極的身體不活動原則上屬于不作為,而積極的身體活動在大多數場合是作為,在小部分場合表現為不作為。當第一步的判斷得出作為犯的結論時,原則上就不需要再進行不作為的判斷。這是因為不作為是作為的補充型態,因此,只要是作為引起了構成要件結果,就應當直接以作為犯論處。[15]399當第一步的判斷難以得出肯定的結論時,就需要第二步采取內在和實質的判斷標準,即法益狀態說或者規范評價說。問題是,在第二步的判斷中,究竟以法益狀態說或是規范評價說哪種學說為標準,并彌補該學說的不足呢?
我們在了解作為與不作為區分困難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弄清不作為犯的本質,確定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究竟采取哪種實質的判斷標準。作為與不作為之所以難以區分,主要在于一個人的身體現象可以同時是作為和不作為。而且,人的身體現象永遠同時可能是無數多的作為,也是無數多的不作為。[10]448例如,甲男與乙女正在約會,同時可以說是甲男沒有與丙女正在約會。又如,甲正在跑步,從作為的角度而言,甲正在鍛煉身體,或者說甲正在減肥;但從不作為的角度而言,甲沒有讀書,也沒有寫作業。又如,駕車肇事案,行為人駕駛車輛撞倒路人致其死亡,當時的情形屬于行為人來得及剎車卻沒有剎車肇事的情形。從行為人不應當向前行駛而向前行駛的角度而言,屬于不應為而為的作為;從行為人應當剎車而不剎車的角度而言,屬于應為而不為的不作為。因此,行為人的行為既可以說是沒有踩剎車的不作為,還可以說成是駕車撞人的作為。在駕車肇事案中,我們選擇“沒有踩剎車”亦或“駕駛撞人”作為規范的“基點”,或者說是評價的視角,就會在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直接影響到行為人構成作為犯罪還是不作為犯罪。不真正不作為犯的存在,是刑法上的價值判斷和規范判斷方法的運用,即將以消極的不作為方式造成法益侵害的情形,規范地評價為和積極地作為犯的構成要件等價值的行為。[3]10可見,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終究是“規范評價”的問題,身體的不活動難言是作為,但積極的身體活動經過“規范評價”既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當積極的身體活動在作為與不作為之間難以區分時,就需要進行規范的評價。因此,規范評價說最終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提供實質的判斷標準,在作為與不作為判斷的第二步中,應當采取規范評價說。但規范評價說中規范“基點”的選擇可謂是重中之重,如何選擇規范的“基點”是規范評價說必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作為不是“什么也沒做”,而是 “沒有做所期待的行為”。[16]可見,不作為規范評價的核心是法律有無期待行為人實施相應的作為義務,當行為人應為而不為違反了作為義務,并導致了法益侵害結果發生時,就有可能構成不作為犯。因此,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是規范“基點”選擇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作為義務,就根本不需要討論“規范”基點的選擇問題。換言之,行為人只有具有相應的義務,才有可能說行為人是否實施了法律所期待行為人的行為,進而判斷不作為犯能否成立。例如,乘客強奸案,出租車司機甲見男乘客乙在汽車后排強奸被害人丙,而應甲的要求駕車繼續前行的。此時,甲基于法益的發生領域的支配而產生阻止義務,即甲負有阻止乙強奸丙的義務,當甲不履行阻止義務,即應為而不為,放任乙強奸丙時,就有可能成立乙強奸罪的不作為幫助犯。從該案中,我們可以看出不作為的核心在于行為人違反了規范所期待的義務,行為人究竟有什么積極的身體動作反而變得不重要了。關于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履行的義務,應當進行實質的判斷。不作為的實質義務來源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對結果發生原因支配地位而產生的監督義務,此時,行為人只有切斷危險源,才能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便具有切斷危險源的義務;第二種類型對結果發生進程的支配地位的保護義務,此時,法益出于無助或脆弱狀態,并依賴于特定人時,行為人就具有保護義務。第三種類型對結果發生領域支配地位所產生的阻止義務,此時,法益在特定領域陷于危險狀態,法益的保護依賴于特定領域的管理者,行為人便具有針對法益危險的阻止義務。例如,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甲駕駛車輛將被害人撞成重傷后,甲下車將被害人放在車上,但并未開車將被害人送往醫院搶救,反而是逃離現場,結果被害人由于未得到及時救治而死亡。在該案中,甲由于先前行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緊迫危險,此時行為人便具有了防止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義務。當甲不履行義務時,就有可能對乙的死亡結果成立不作為犯。
當行為人具有法律所期待行為人實施的義務,行為人應為而不為時就有可能成立不作為犯。此時,還有可能發生作為與不作為競合的現象,即,一個行為從一個角度而言是作為,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是不作為,這也就是作為與不作為區分困難的原因之一。此時,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行為人從違反禁止規范的角度而言是作為,從違反命令規范的角度而言是不作為,規范“基點”選擇命令規范亦或是禁止規范,直接決定了行為人構成作為犯亦或不作為犯。例如,案例1、2中,既存在履行救助義務的命令規范,又存在禁止縮短他人生命的禁止規范,因此,行為人拔掉病人呼吸管的行為既可以被評價為違反救助義務的命令規范,又可以被評價為違反禁止縮短他人生命的禁止規范。當規范“基點”選擇禁止規范時,行為人的行為就可能是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反之,規范“基點”選擇命令規范時,就是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但規范“基點”的選擇會帶有濃厚價值判斷的主觀色彩,其結論往往就會因人而異。為了避免判斷的恣意化,就應當選擇一個客觀的標準來約束規范“基點”的選擇。實行行為的實質屬性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現實危險,而不作為屬于實行行為,也應當具有侵害法益的現實危險。[17]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或威脅法益,不作為犯也應當如此。因此,在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上,應當在規范評價說的內部考慮法益狀態,區分侵害和威脅法益的行為究竟是作為與不作為。如果法益侵害結果直接由行為人的作為所導致,就可能成立作為犯;反之,就可能成立不作為犯。而且,法益具有客觀性和明確性,在規范評價說的內部考慮法益進行作為與作為的區分,必然能夠彌補規范評價說的不足。作為是主動設定指向結果的因果進程,而不作為是對已經存在因果進程的放任。[18]基于對指向結果的因果進程的設定,作為便是使法益狀態惡化的行為,而基于對已經存在因果進程的放任,不作為就是使法益狀態沒有好轉的行為。在前文所述的拒不救援案中,之所以法益狀態說沒有得出妥當的結論,原因就在于沒有進行不作為義務的判斷,即,前文所說的不作為犯義務的有無是規范“基點”選擇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該案中,甲對乙根本就不具有作為義務,所以就毋需進行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如果將該案稍加改動,甲將乙不慎撞到井中,此時,甲對乙便具有了保證人地位,甲將繩索抽回,顯然屬于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流程,是沒有使法益狀態好轉的不作為。
綜上,規范評價“基點”的確定應當考慮:(1)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行為人履行的義務。(2)行為人雖有作為義務,但行為人主動設定因果流程,使法益狀態惡化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禁止規范”,行為人的不應為而為構成作為犯。(3)行為人具有作為義務,并且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進程,沒有使法益狀態好轉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命令規范”,行為人的應為而不為構成不作為犯。具體到案例1、2中,被告人文某拔掉妻子胡某身上的呼吸管等醫療設備,被告人阿林拔掉套在母親鼻子上的呼吸機管的行為,采取第一步身體動靜的判斷難以得出作為或不作為的肯定結論時,就需要進行第二步的判斷。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是規范“基點”選擇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被告人文某與阿林無疑基于法規范而對被害人具有法益保護義務,即具有對結果發生進程的支配地位的保護義務。但進一步判斷時,我們會發現,此時被告人的行為發生了作為與不作為的競合,這就需要選擇規范的“基點”來判斷作為與不作為。案例1、2中,行為人拔呼吸管的行為顯然不屬于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進程,而是創設自己所控制的因果流程,并導致法益狀態的惡化,應當選擇“禁止規范”作為基點,將兩名被告人的行為評價為作為。至于兩名被告人在拔掉呼吸管等設備后,阻止醫生救助的行為,也應當屬于主動創設因果流程并導致法益狀態惡化的作為,與前面的拔呼吸管行為共同導致了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應當被整體評價為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如果案例1、2中,被告人不將被害人送往醫院救治,就屬于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進程,沒有使法益狀態好轉,就有可能被評價為不作為犯。同樣,醫生關閉呼吸機的行為也屬于創設自己所控制的因果流程,并導致法益狀態惡化的行為,也應當屬于作為。那么,為什么醫生在病人家屬同意的情況下關閉呼吸機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家屬等第三人擅自關閉呼吸機的行為就構成犯罪了呢?首先,應當肯定的是,使人的生命在自然死亡之前終結,就是殺人行為。我國目前對死亡標準的判斷采取的是呼吸停止、心臟停止跳動、瞳孔反射機能停止的死亡綜合標準說。因此,即使病人處于腦死亡的狀態,按照綜合標準說,關閉呼吸機使病人提前死亡的也屬于殺人行為。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家屬等關閉呼吸機的行為都是作為,該當于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至于醫生在家屬同意后就不構成犯罪的原因,本文的初步考慮是,醫生在家屬同意下關閉呼吸機雖然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但屬于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條款所規定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至于病人家屬擅自關閉呼吸機,甚至阻止醫護人員繼續救治病人的,顯然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還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被評價為犯罪科處相應的刑罰。至于案例1中的被告人雖然是以作為的形式實施的故意殺人行為,但仍以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處以緩刑,本文認為這一判決結果無疑是妥當的。即使不認定被告人是不作為犯罪,仍能夠說明法院為何從輕判處的理由。法益侵害的事實說明罪行的輕重程度并影響到刑罰的輕重,而法益侵害事實首先是指行為造成的結果。[19]因此,在量刑時要考慮行為對法益侵害結果的貢獻,貢獻越大,量刑就可能越重,反之,就可能越輕。在依靠呼吸機等設備維持生命的場合,可以說病人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否則就不會通過醫療設備來維持生命。因此,關閉呼吸機的行為實質上對病人死亡結果貢獻很小。而且,沒有意義的醫療行為,可能和生命的維持根本沒有因果關系,并且更可能徒增病人的痛苦以及社會的資源。[10]449這也反映出此類案件的一般預防必要性的減少,因此可以以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量刑,判處輕緩的刑罰。在案例1中,被告人文某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緩刑,即使不從不作為犯的角度,也能夠很好地說明法院為何會從輕判處。在案例2中,被告人的行為同樣可以被評價為作為的故意殺人,但法醫鑒定表明,被害人的死亡結果是由前一行為人的交通肇事行為所引起的,因此,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案例2中被告人的行為僅可能成立故意殺人罪的未遂。
四、結語
總之,本文對于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可謂是采取了綜合身體動靜、規范評價、法益狀態等標準的綜合說,身體動靜作為外在和形式的標準,規范評價與法益狀態作為內在和實質的標準,對作為與不作為的區分應當從形式到實質、外在到內在,采取“兩步走”分層次的遞進式思考進路。第一步形式和外在的判斷運用身體動靜說作為判斷標準,當第一步的判斷難以得出妥當的結論時,就需要第二步運用實質和內在的判斷——規范評價說。規范評價說中規范“基點”的選擇可謂是重中之重,但規范“基點”的選擇往往又沒有適當的標準,結論往往是因人而異,因案而異。因法益具有客觀性和明確性,在規范評價說的內部考慮法益狀態進行作為與作為的區分,必然能夠彌補規范評價說的不足,解決規范評價說空洞無物的弊端。規范評價“基點”的確定應當考慮:(1)行為人是否具有法律所期待行為人所履行的義務。如果行為人沒有義務,就不需要討論“規范”基點的選擇問題。基于實質的判斷,義務大體可以分為監督義務、阻止義務和保護義務,這三種義務無疑是確定規范評價基點的前提所在。換言之,行為人只有具有相應的義務,才有可能說行為人是否實施了法律所期待行為人履行的義務,進而判斷不作為犯能否成立。(2)在規范評價說的內部考慮法益狀態,區分侵害和威脅法益的行為究竟是作為還是不作為。如果法益侵害結果直接由行為人的作為所導致,就可能成立作為犯;反之,就可能成立不作為犯。行為人主動設定因果流程,使法益狀態惡化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禁止規范”,行為人的不應為而為構成作為犯;行為人放任已經存在的因果流程,沒有使法益狀態好轉時,規范的基點就在于“命令規范”,行為人的應為而不為就構成不作為犯。
[1] 深圳“拔管丈夫”被判緩刑[EB/OL].http://sc.sina.com.cn/news/m/2015-11-20/detail-ifxkxfvn8892163-p5.shtml,2016-10-15.
[2] 四川眉山“拔管弒母”案死者死因確認為車禍[EB/OL].http://news.163.com/16/0105/07/BCI3AKO800014AED.html,2016-10-15.
[3] 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4]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47.
[5]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27.
[6] 許成磊,高曉瑩.論刑法中不作為與作為的區分[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5):25-30.
[7] 黎宏.刑法學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0.
[8]松原芳博.刑法總論重要問題[M].王昭武,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68-69.
[9] 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5-67.
[10]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1] 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2卷)[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91-492.
[12] 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M].蔡桂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59.
[13] 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94.
[14] 劉斯凡.論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區分的兩重性——以真正不作為犯與不真正不作為犯的不對應性為切入點[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157-164.
[15]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399.
[16] 山口厚.刑法總論[M].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76-77.
[17] 陳興良.不作為犯的生成[J].中外法學,2012(4):665-682.
[18] 西田典之.刑法總論[M].王昭武,劉明祥,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6.
[19] 張明楷.責任刑與預防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75.
[20]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449.
(責任編輯:李瀟雨)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ct of Commission and the Act of Omission
ZHAO Jin-wei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ct of commission and the act of omission is importa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me, the emphasis of examination and the order of judgment, as well as the correct sentencing. The criterion of how to distinguish the act of commiss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physical movement, normative evaluation, legal interest and other standards, taking the two step from the form to the substance, external to internal, which is a step by step thinking approach. The first step using body movement as a judge standard, when it is difficult to draw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it is required to use the second standard——normative evaluation. The "basic point" is important to normative evaluation, and it should be related to two factors: obligation and legal interest. Namely, the actor has the obligation which the law expects him to fulfill, and whether the act of commission infringe the legal interest or not. The obligation of the actor is to determine the "basic point", 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upervision obligation, prevention obligation and protection obligation.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act of commission, the actor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set the casual processes, and deteriorating the legal interests, the “basic point” is “prohibition norms”. Then the actor's behavior is the act of commission. When the actor do not interfere the casual processes that has already existed, and not make the legal interest better, the “basic point“is “command norms”. Then the actor's behavior is the act of omission.
the act of commission; the act of omission; normative evaluation; legal interest, distinction
2016-11-26
趙金偉,男,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D914
A
1008-2603(2017)01-00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