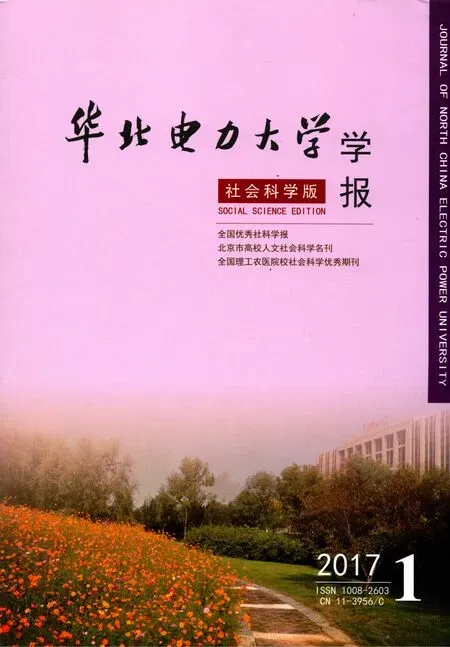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崔一非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
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崔一非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進入21世紀以來,許多西方比較文學學者針對全球化語境對“世界文學”概念進行了重新定義,弗朗哥·莫萊蒂的“世界文學體系”理論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種,但是在國內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本文從文學史觀、世界文學體系的定義、世界文學的研究方法三方面對這一理論進行研究,并對前人的批評進行綜述,具體概括其文學史觀的進化論特征、世界文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特征和研究方法上的宏觀和定量分析特點。
莫萊蒂;進化論;世界文學體系;定量研究
在全球化的語境里,文學的全球化問題將比較文學研究者帶回到歌德的“世界文學”——這一1827年提出的概念的使用中。本世紀初,以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以各自新的闡釋重提“世界文學”,借以探討文學的全球化過程中不同民族文學作品在全球范圍內的流通、翻譯等問題。相關術語如“星球文學”(由GayatriSpivak和Wai Chee Dimock提出)、“文學的世界體系”(由Emily Apter提出)、“世界文學空間”(由Pascale Casanova提出)等可視為這一舊概念的變體,都在試圖描繪這一全球化問題。這一被挪用的詞匯在21世紀顯然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和歌德的“將各民族文學統一起來成為一個偉大的綜合體”的理想(代價是各民族文學放棄自己的個性)并不相類。對于歌德而言,“世界文學”只意味著“歐洲文學”[1]。早在上世紀中葉的奧爾巴赫那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是隨著二戰后教育體制的變更、專業機構的解體以及“新”的非歐洲語言和文學的出現,歌德式的理想可能已經變得站不住腳。而在后結構主義思潮興起之后,這一名詞與生俱來的“歐洲中心主義”則在后殖民研究的語境中被加以修正,成為比較文學界討論的焦點。
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的“世界文學體系”便是這場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在發表于2000年的《世界文學猜想》和2003年的《世界文學猜想續篇》兩篇論文中提出了他的“世界文學”概念。對于莫萊蒂而言,“世界文學不能僅僅是文學要大于文學”。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對象,而是一個問題”——“一個需要用新的批評方法加以解決的問題。”具體而言,莫萊蒂是借用“樹和波浪”兩種歷史語言學常用的比喻來建構一種新的研究范式,這一范式是與他宏觀的、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史觀相聯結的。在本世紀以來諸多對“世界文學”的重新定義之中,莫萊蒂的“中心-邊緣”結構的定義并不像他的一些同行那樣強調“世界主義”,而是更多地繼承了馬克思的“世界市場”概念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概念。與其說這一對世界文學的定義是對歌德的世界文學觀的重提,不如說它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在如何研究世界文學的方法論上,莫萊蒂則一反傳統的批評方法,將統計學的定量研究引入文學研究,似乎提示我們一種大數據時代的理論轉向。而無論是世界文學體系理論還是方法論實踐,都引發了學界的激烈論爭,本文就試圖對其理論建構和爭議進行梳理。理解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理論,我們需要從這位小說史研究者的文學史觀著手,雖然莫萊蒂將世界文學簡化為“樹”和“波浪”,但是對世界文學更為具體的繪制則體現在他的宏觀的文學史模型中。
一、 進化論的文學史觀
莫萊蒂在一篇較為晚近的論文《進化、世界體系、世界文學》(Evolution, World System, Weltlituratur)(2005)中,提出了建立“新的世界文學形象”的兩種理想模式——“進化理論”和“世界體系分析”。這兩種模式同時也是作者多年研究一以貫之的基點:世界體系分析在專著《歐洲小說地圖:1800—1900》和論文《世界文學猜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進化理論則主要體現在著作《奇跡的先兆》(Signs Taken for Wonders)(1988)、《曲線圖、地圖、樹形圖》(Graphs, Maps, Trees)(2005)和論文《文學的屠宰場》(The Slaughterhouse of Literature)(2005)中。
莫萊蒂認為進化論和世界體系是兩個維度:進化論強調物種演變的形式多樣化,世界體系分析則在描繪擴散導致的相似性。進化論文學史觀的優點在于:以往文學研究的形式理論通常忽略了歷史,歷史研究則忽略了形式,而“對于進化論而言,文學的形式與歷史實在是一枚錢幣的兩面。[2]243”早在《奇跡的先兆》一書中的論文《論文學的進化》(On Literary Evolution)中,莫萊蒂比較了拉馬克主義和達爾文主義[3]。前者認為變異是直接的、定向的,后者則主張變異是隨機的、非定向的。對拉馬克而言,進化是一元論的、不可分的發展,單一的適應原則控制著選擇和變異;而對達爾文來說,它是個二元論的過程,由偶然支配的變異與由必然掌控的選擇之間的分裂是不可彌補的。在文學史領域中,形式與形式是像生物一樣存在著一種不斷爭奪生存空間的競爭關系。而在形式的競爭之中,最終何種形式會取勝,取決于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形式本身的適應性,而形式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否定之否定的關系,而是可能會發生斷裂和突變,某些形式可能因為在競爭中失敗而短暫性消失或者永久消失。作者認為將達爾文主義的文化進化論的主張應用到文學研究應該是有益的:如果文學史的變革不是目的論的,來探究這種假設的結果。這一思想在后來的《曲線圖、地圖、樹形圖》成為其文類演變史——曲線圖模型研究的主要方法。主導文類——作者借用庫恩的“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的說法稱之為“常規文學”(Normal Literature)[4]18,它們的更替機制背后是讀者群的更新——25-30年正是產生新一代讀者所用的時間,而這正是人類的代際間隔。對于各時期主流題材小說的更替的動力,作者引用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觀點“當一種舊的文學形式失去了它的藝術功用,新的文學形式就會出現來替代它。”[4]14具體而言,一種文學形式的藝術功用是如何衰落的?讀者趣味又是如何轉換的呢?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政治。政治不僅維持了這一更替周期,同時也成為打破這一更替“節奏”的主導因素,例如雅各賓小說(Jacobin Novels)等小說文類只持續了十年,是因為“‘政治’形式使敘事邏輯服從于短時期的節奏(tempo)[4]24”——如果小說吸引讀者的只是當下的政治現實,一旦時過境遷,該小說題材便迎來末日。
進化論的文學史觀早在泰納的《英國文學史》中就有典型的體現,19世紀后半期起,在社會科學領域甚至形成了達爾文主義思潮。莫萊蒂重新看到了它的價值,使它在本世紀在文學研究中復活。韋勒克曾言:“19世紀后半期,全球文學史的理想在進化論的影響下又復活了”。然而“進化論在現代文學史上卻沒有留下多少痕跡,顯然它把文學的演變描繪得與生物的進化過分相似,從而失去了信譽。全球文學史的理想隨之衰落。”[5]45莫萊蒂將進化論思想引入文學史研究無疑是容易引起憎惡的,這一文類學層面的科學主義的嘗試容易遭到同行的批評,就像1890年布呂納介的《文學體裁演化論》用機械的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文類的演進,使得此后在法國學界對文類學的討論“談虎色變”一樣。但是這一對文學演化的動力機制及變化規律的達爾文主義的思考未嘗帶給我們的啟發多于它的缺陷。
二、 世界文學體系論
上個世紀80年代,佛克馬等學者進行的文學經典的討論,使“世界文學”成為一個熱議的問題。而隨著達姆羅什的《朗文世界文學作品選》和《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isWorldLiterature?)的出版,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多元文化主義”和后殖民的文化研究盛行的語境下,當代學者對“世界文學”的定義不僅顯示了“去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也顯示了對其流動性和差異性的關注。
莫萊蒂認為當我們在嘗試解釋“世界文學”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兩個“世界文學”的概念,一個是18世紀之前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學),是“多種獨立的‘地方’的馬賽克式的拼貼;具有很強的內部多樣性;主要通過分化而產生新形式”,另一個是18世紀之后的——“世界文學體系”(literary world system),將18世紀作為界限源于莫萊蒂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以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為界,那是“國際圖書貿易的開端”[2]249。“聚合是文化史的基礎[2]245”,聚合與擴散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學形成“世界文學體系”。這兩種趨勢被莫萊蒂形象地總結為“樹”和“波浪”兩種模型,“樹”象征了民族文學的發展機制,“波浪”則象征了世界文學的傳播機制。這是歷史學家在分析世界范疇內,或在更大范圍內分析文化的時候兩種基本的認知比喻。“樹描述了從統一性到多樣性的發展:一棵樹有很多分支:印歐語系分化成十幾種不同語言,波浪卻相反:它吞噬了最初的多樣性的統一性。”[2]134樹狀發展需要地理的斷裂性,波浪則依賴于地理的連續性。文化史是樹和波浪組成的。大衛·達姆羅什曾對這一模型非常贊賞,認為如果“以弗蘭科·莫萊蒂提倡的方法將個體文本的詳細分析和如短篇小說這類題材延伸開來的‘波浪模式’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進行跨越國家傳統和帝國貿易路線的研究,將會“引出更多課題”[6]。而莫萊蒂與達姆羅什在研究世界文學的維度上有一些相同。在2003年的《什么是世界文學》中,達姆羅什提出:“世界文學必須在多重意義上予以理解……存在于多維空間中,它與以下四個參照系相關: 全球的、區域的、民族的、個人的。而且這些參照系會隨著時間而不停地變遷,如此時間便成為第五個維度。在時間的維度中,世界文學不斷地被賦形,并不斷地變形。”這使我們看到了莫萊蒂“世界文學體系”和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之間的關聯,對傳統的世界文學觀進行了挑戰,它們均超越了以文學經典為中心書寫世界文學史的傳統觀念,著眼于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的變異性。
莫萊蒂還進一步闡述了世界文學體系的特征——它是整體性和不平等性的結合體。“同資本主義一樣,世界文學本身也是不平等的整體……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學的發展通常受制于它們在整個體系中的位置。”和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類似,莫萊蒂認為國際文學體系內部也存在中心和邊緣之分,表面上這是一種市場機制的作用,實際上也是由世界政治力量的不均衡決定,“中心的小說不斷出口到半邊緣和邊緣區域”,并被樹為那里的“樣板”,這實際上是一種同化的力量:它把邊緣區域的文學吸引到中心小說的軌道上來,干涉了它們的自主發展。但邊緣對中心的反向影響“幾乎從未發生”。莫萊蒂接下來還說明了邊緣地區的文學所受到的外在影響與本民族傳統之間的具體作用形式——莫萊蒂認為這也是通往現代性的必經之路:“當一種文化開始向現代小說發展時,它總是外國形式與本土材料之間的妥協。”[2]130具體而言,邊緣地區在融入國際文學貿易以后的文學作品是“來自中心的一個情節和來自邊緣的一種風格”的化合。
這種中心-邊緣結構事實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學”的概念,是從世界市場和生產消費的世界性論述到精神生產上來,其表述為:“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共同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將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世界的文學”。這種表述的重心在于“世界”,而不是文學,更有學者指出這里的文學其實是廣義的“文化”。這里的“世界的文學”只不過是“他們對資產階級對世界歷史所帶來的結果所作的客觀描述而已”,與歌德式的詩學理想不能混為一談。莫萊蒂的“世界文學體系”便是以“世界市場”理論為基點的,如上文所述,他選擇18世紀為分界點進行小說研究,因為那是國際圖書貿易的開端;而在對主流小說文類的曲線圖分析中,他的判定依據便是圖書市場的流通量。其核心的“世界體系”概念同樣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對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忠實繼承,莫萊蒂借用了這一理論闡述了因文學作品的流通和圖書貿易形成的“文學的世界體系”。世界體系理論的最大特點是以世界體系為基本分析單位。沃勒斯坦認為,人類歷史雖然包含著各個不同的部落、種族、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歷史,但這些歷史從來不是孤立地發展的,總是相互聯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體系”。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形成以后日益擴展,“直至覆蓋了全球[7]1”。這一理論糅合了布羅代爾的“中心”與“邊緣”的空間二分法: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形成強國,邊緣區形成了弱國,強國之間競爭形成了歷史上“爭霸”運動,弱國對強國的反抗斗爭是為“反帝運動”和“反體系運動”。莫萊蒂引述了托馬斯·帕維爾在《小說思考》中的觀點,認為分化是小說歷史上前15個世紀的驅動力,而自18世紀以來才是聚合的。“文學的世界體系”這一說法的成立正是建立在這種文化“聚合”的意義上,因此新的世界文學——“世界文學體系”是以1800年為起點的(當然,這是一個象征性的說法)。而文類、風格從中心國家和地區到邊緣的流動也無疑應和了“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二分法,這一觀點則受到了后殖民學者的批判。
三、 世界文學的宏觀與定量研究方法
在方法論上,莫萊蒂對傳統的文學批評范式進行了革命式的反叛。首先,他提倡宏觀分析,認為“讀得‘多’是件好事,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8],“過去的小說理論都把小說縮減為一種基本形式(現實主義、對話體、愛情故事、元小說……)”,因為只注重對經典或曰主導文類的批評,它們抹去了文學史的十分之九——對于作者而言,這是個巨大的損失。進而,他獨辟蹊徑地提出“遠距離閱讀”的批評方法。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是一個帶有與“細讀”(Close Reading)截然對立的含義的概念。我們不能籠統地將它稱為“遠距離閱讀法”的原因在于,與其視其為一條方法、策略,不如說它是一種概念——一種將關注點由從特殊到普遍、由特別的個案轉向更廣闊的事實(the large mass of facts)[4]3的思維方式,把研究的焦點從“故事”轉移到了“創作背景”(生產和流通)。在《世界文學猜想》中,作者提出了以“遠距離閱讀”取代“細讀”的宏觀分析的觀點。
而“遠距離閱讀”是必定要與統計學意義上的定量研究結合的。莫萊蒂在2005年出版《曲線圖、地圖、樹形圖——文學史的抽象模型(Graphs, Maps, 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一書中提供了他的宏觀文學史建構在西歐小說范圍內的試驗模型。如書名所示,這本書分為曲線圖、地圖和樹形圖三部分,以小說這一文體為例,分別介紹了量化的(quantitative)、空間的(spatial)和形態學的(morphological)三種文學圖表。不同于一般文本批評,這一做法的關鍵是以大量統計數據為代表的實證的采集,涉及統計學、地理學和生物學模型的相關知識。例如,他在書的第一章通過統計歐洲18至19世紀各個時期的各小說題材的生產數量,發掘了主流小說亞文類(subgenre)演變的潛藏規律,以建立“讀者的社會政治地理學(a sociopolitical geography of readers)”。
從莫萊蒂在書中展開的“書籍史”等研究來看,他提倡的以“遠距離閱讀”取代文本“細讀”實際上主要是受到人文學科的一個新趨勢——“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影響,這是一門以統計學為主導的文理結合的學科,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一個新的分支。“數字人文”雖然得名不長,但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的量化研究在西方已經有一定的歷史,起步于1850年[9]518。目前在歐美國家已經形成多家獨立的研究機構和一個國際聯盟——“數字人文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而莫萊蒂則是斯坦福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進入信息時代,來自自然科學的定量分析的方法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輔助工具,如目前已廣泛運用的“統計文體學”(stylometry)、“作者歸屬”研究(authorship attribution)等。數字人文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對海量文獻的處理”,關注流通廣泛的語料,這種文理結合的研究方法已經延伸到文學、歷史等諸多人文學科。借助技術手段搜集并整理大量數據,從中發現文學流通和發展的歷史性和地域性規律——這一以宏觀分析和定量分析為特征、以統計數據為支撐的研究方法正在文學研究領域發展開來,Matt Jockers新近出版的《宏觀分析》(Macro-analysis)便是這一領域發展以來的重要代表作。David Hoover認為這種研究手段在傳統的文學研究領域發揮最好,但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它也在開拓新的領域。在有效利用大量的電子文本和自然語言語料庫成為可能之后,定量分析已成為一種“閱讀”成千上萬的文本的新方法,“甚至有壓倒傳統閱讀模式的可能”[9]519。這一觀點與莫萊蒂不謀而合。“遠距離閱讀”便是一個提倡將文學研究交給計算機的概念,因為數字傳媒時代顯然已經不同于過去的印刷時代,不僅書籍在出版的數量上超出我們的想象,而且每天生產出來的不計其數的網絡文本更是令人眼花繚亂。傳統的研究范式似乎已不能滿足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莫萊蒂的這種跨學科的嘗試,無疑是為解決這種困局的一次探索,在“大數據”時代試驗將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結合。但同時,由于這一標榜“科學”、“理性”的信息處理技術與傳統的審美批評如隔山岳,以定量分析為核心方法的文學研究也在不停面對質疑之聲。
四、 學者們對莫萊蒂理論的回應
(一)關于進化論的文學史觀
莫萊蒂進化論的文學史觀與作為生物學家的好友阿爾貝托·皮亞扎(Alberto Piazza)的影響不無關聯,皮亞扎曾在《曲線圖、地圖、樹形圖》一書的《跋》中對莫萊蒂的這種做法進行了細致分析。皮亞扎指出莫萊蒂在認識到“空間的斷裂和形態創新之間的關系”這一點非常值得肯定。他認為莫萊蒂將翻譯視為與自然選擇、遺傳漂變(genetic drift)最為相近的文學過程,這種文學傳播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形式的移植,而這種可轉移性在生物基因和文學進化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同時進化論的模式也限制了莫萊蒂的視野。皮亞扎認為樹形圖模型對文學研究而言并不是一個最理想的框架,因為它框定了一個線性模式,而復雜的網狀模型似乎才更能服人——因為在文學和生物學中,“非線性才是慣例而不是個案”[10]107,在《曲線圖、地圖、樹形圖》的對主流文類研究中,有圖表顯現出了一種文類循環的現象(即一種文類在經歷一定周期之后再次成為主流文類的現象),而在定量研究中往往會忽略這一點,這也是所有涉及定量模型的知識領域的局限所在。此外,他還指出在作為寫作策略的線索演變樹形圖中,要論證“突變”是否由自然選擇決定,莫萊蒂的問題在于線索的選取和完整性上,為了避免循環論證,對偵探小說及其線索的選取上必須做到盡可能完整和彼此獨立。
將進化論引入文學研究是莫萊蒂的一個巨大的創新,它拾起了一項幾乎被文學研究者遺忘的理論。Joseph Caroll就曾指出生物學的進化論是被文學理論廣泛忽視的概念[12],阿普特也指出達爾文進化論在文學研究中歷來聲譽不佳[13],自19 世紀以來,進化論作為文學研究方法已是昨日黃花。就其功能而言,莫萊蒂認為“它在歷史進程的基礎上闡釋了現有形式非凡的多樣性和復雜性”[2]243,結合了文學理論一直沒有做到的形式與歷史研究的結合。而將進化論與“世界體系”結合則更具啟發性,如上文所述,它描繪了文化史的聚合和分化兩種主要形態。
然而自然科學的概念與文學研究的結合很難嚴絲合縫。“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進化論,都具有經濟學或是生物學的科學依據,但他們的不足之處在于以理性觀念來批評文學藝術的審美現象,導致了文學本體批評的審美特性的缺失。然而,就進化論本身而言,像皮亞扎所說的那樣,莫萊蒂的文學進化論是一項推動人們“改善閱讀進化論的視野的動力[11]113”。
(二)關于“世界文學體系”的定義問題
莫萊蒂關于“世界文學體系”的論述是基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觀點進入對現代以后的“世界文學”的重新定義,這一定義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艾米麗·阿普特(Emily Apter)認為這種理論的核心并不只是提倡一種歷史觀念,而是要建構新的歷史理論體系[14]。它的創新之處不僅在于提出了一種宏觀的理論框架,還引入了俄國形式主義托馬舍夫斯基的“情節”與時代的敘事風格(這種觀念其實一定程度上來自于盧卡契等人)兩種觀念,使得這種文學進化論更加細化,對盧卡奇和一般形式主義有一定超越。
關于是否可以“世界體系”概念是否適用于世界文學研究上,帕斯卡爾·卡薩諾瓦表達出了質疑。在《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中,她提出了與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不同的“世界結構”的概念,并特別指出“世界體系”“不太適合文化生產的空間”。她雖然贊同莫萊蒂對文學世界體系的整體性和不平等性的歸納,但同時也認為“中心-邊緣”這種二分法“模糊”了不平等性,使其變得“中立、委婉”,“沒能對依賴程度提供準確的度量”[14]114,因此她更傾向于表述為“統治-被統治”的關系。早在《文字的世界共和國》中,卡薩諾瓦就表現出了文學文化政治的興趣,她運用“權利關系”來闡釋了“文學世界”的大國與小國、中心與邊緣之分。顯然,“世界體系”和“世界結構”兩種概念體現了莫萊蒂和卡薩諾瓦興趣點的分野——莫萊蒂的工作重點只是客觀描述這種不平衡和差異性,而卡薩諾瓦則將焦點轉向。
在對“中心-邊緣”的劃分上,丹麥學者馬茲·羅森達爾·湯姆森(MadsRosendahl Thomsen)則提出了另一種批評,他認為“中心的觀點是一種簡化”,“中心-邊緣模式”將焦點集中在“作品的生產和分配上”——掩飾了文學史長期以來創造的事實,而“莫萊蒂沒有將臨時主導的概念深入到文學地理的領域,而停留在單一文化的研究中”[15]252。湯姆森因而提出了“臨時分中心”的概念,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世紀60到80年代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為代表的俄國小說的繁榮,就“在世界文學史上構成了一個臨時分中心”。湯姆森實際上是看到了世界文學體系的流動性,無論它本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還是一種與殖民主義相關的權力體系,在20世紀,文學的進化都顯現出了一種更為復雜的態勢——既有卡薩諾瓦所定義的難以動搖的世界文化首都巴黎,也有不同階段的臨時分中心。這種觀點在我們進一步探討“世界文學經典”的新內涵的時候也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更尖銳的批評則來自于后殖民理論層面。史書美(Shu-Mei Shih)認為,在反體制反中心的后結構主義浪潮中,莫萊蒂的“中心—邊緣”論述仿佛是對體制的渴望的回潮——“體制像被壓抑的力量一樣彈回來了”[16]。莫萊蒂對西歐以外的文學所知甚少,但這并不妨礙他將西方以外的復雜世界置入“整體化”的論述之中。史書美還指出莫萊蒂的這個論斷也不符合中國文學的情況。對于中國文學而言,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區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十世紀初期,短篇小說取代長篇小說的霸權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史進一步指出我們因此應該修正杰姆遜的觀點:即所謂“長篇小說是現代全球化的文學形式”,而莫萊蒂關于長篇小說的論斷就是以杰姆遜的觀點為基礎的。
埃弗雷·克里斯塔爾(Efrain Kristal)也批評了莫萊蒂整體化的說法,他以西班牙語的美洲文學舉例,這類文學并不是以長篇小說文類為主,所以莫萊蒂獨尊長篇小說的看法并不能放之四海皆準[17]。對小說這一單一文類的研究也受到了普倫德加斯特的質疑:詩歌也遵循與小說同樣的規律嗎?[18]莫萊蒂對此做出回應:以現代小說的興起來闡述世界體系的作用,小說僅是“一個例子,不是模式”[8]136。克里斯塔爾又質疑了其單一向度的“中心—邊緣”傳播的模式——西班牙語的美洲文學的跨文化交流現象并非是從“中心”走向“邊緣”的單行道,而是另有更為復雜的交流方式。莫萊蒂則反駁了形式的多方向的移動,至少據他對于歐洲小說的了解,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形式是根本不運動的,“(不經過中心)從一個邊緣到另一個邊緣的移動幾乎從未聽說過;從邊緣到中心的運動不那么罕見,但仍然是不常見的”。只有“中心到邊緣的移動”[31]最為頻繁。
而關于文化混血就只是“外國情節、本土角色,再加上本土的敘事聲音”的歸納也未免失之于機械化。按照史書美的觀點,這種歸納“預設了一種‘沖擊力/沖擊力的接受者’的二元關系,將西方視為主動的文化孕生者,而將非西方視為被動的文化接受者——而這種預設極易被反駁,正如克里斯塔爾所說:“文學的動線未必一定是單行道”。
誠然,作為一位意大利裔的學者,莫萊蒂從歐洲大陸來到美國,在北美這片多元文化主義的土地上,“中心—邊緣”結構容易被視為“白人政治”。伴隨著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世界文學”在美國被預設了一種平等、民主的內涵,一種“政治正確”的世界文學的闡釋的典型應該是斯皮瓦克所倡導的“星球化”(planetarity)的思維模式:克服他者的眼光,與區域研究(area study)相結合。而比較文學這一承擔了“非殖民”理想的學科在后殖民語境下的尷尬之處,也是被重新定義的“世界文學”所承擔“世界主義”的理想付出的代價。但是我們也應反思“世界文學”是否可以忽視“中心”而盲目追求一種平等和“大同”,“中心”真的消失了嗎?換言之,我們的學科是否可能被“政治正確性”所綁架。
而換一個角度,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理論來源于他對馬克思的世界市場理論的繼承。莫萊蒂并不著眼于文學內部批評,而更關注文化和文學市場。他認為文學是“作為社會關系的抽象形式”[8]132——這可能會招致一個強烈的質疑:莫萊蒂更關心的是“世界”還是“文學”。在《世界文學猜想》中,他明確提出:“形式分析就其自身簡單的方式而言也是對權力的分析”[8]134。而在《歐洲小說地圖(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999)、《世道常情——歐洲文化中的成長小說(The Way of the World—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2000)一再強調社會政治因素是主流文類變化的決定性動力(force)。如馬克思對世界文學的定義,莫萊蒂的定義更像是對客觀現實的呈現,而非歌德式的“世界文學”的烏托邦理想。在這一意義上,莫萊蒂的“世界文學”事實上更接近于杰姆遜的“全球化文學”概念,一種相對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對世界范圍內文學形式流通的描繪體系。
(三)關于世界文學的宏觀與定量分析
在宏觀分析方面,代表性評價來自華裔學者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她肯定了這種將遠距離閱讀應用于文類批評的做法,但是她不認為這種方法是作者所說的那樣是“以少為多”、“凝縮(reduction)”的典型,相反,她更愿意將它視為“一個擴充的過程”[19],一個較傳統做法而言更廣闊的文學史視野。她肯定了莫萊蒂的比較形態學(comparative morphology)的觀點,以可形式化的法則為旨歸,盡管在我們過去的認識中,以對文本細節的犧牲為代價構建一個宏觀的文學視野是不值得的。雖然如此,但是它確實為文學研究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文學領域是不完整的”,它需要的是一個“基礎盡可能廣泛、更可能細致、寧可過度隨機也不要過度一致”的檔案,并“維持一個充實的、不斷累積的和不必要統一的記錄”。
在量化研究上,學界既既有肯定也有質詢。這一方法的典型研究成果是莫萊蒂的書籍史研究。它主要以一定時期小說的生產和流通數量為統計對象,來梳理出不同時期的主流文類,分析出政治變革在主流文類演變中的體現。許多學者認為這一研究非常具有啟發性,認為它“在數字和文本細讀之間潛在地提供了一個中間立場”。Germaine Warkentin就高度評價了這一文學與歷史學研究結合的成果,認為莫萊蒂的書籍史研究優長之處在于不僅考察了文學生產和流通,而且這一工作還是針對特定文類進行的[20]。而Katie Trumpener指出了莫萊蒂極端的科學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一方面,研究過分注重數據統計和圖表繪制,而較少看重“人的作用”。莫萊蒂在書中夸大了一個“客觀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他的書籍史研究只有文類,而沒有一個作家的名字,仿佛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是哪些作家主導了這些小說題材的演變。同時也沒有一個小說的名字被提及——他的興趣點在于描述一個系統性的、宏觀的轉變,任何特定文本都似乎變得毫不相關。另一方面,單純以圖書市場為參考物實際上使研究者走向了民粹主義——他理所當然地將18世紀的小說建立在“以中產階級生活為核心”[21]的位置上,而精英階級、紳士階層則并沒有被提及,這使得這一分析過于簡單化——事實上,按照Trumpener的看法,文學文化受復雜的歷史和制度因素的影響,往往是無章可循的,是不能僅依靠統計圖表分析其規律的。
對于莫萊蒂推崇以“遠距離閱讀”代替文本細讀的做法,大衛·達姆羅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表達了擔憂:這種在沒有直接閱讀經驗的情況下撰寫世界文學史是很危險的[22]25。John Holbo則從學科的建設方面評價了這種新的研究手段,他使用了一個諷刺性的比喻:“如果文學研究接受了定量研究的轉向,它不過是荒謬的托馬斯·葛擂硬般的實證主義罷了[23]4”。“會把定量的支持者導向儀式化般的表圖、地圖和樹形圖批量甚至是過量的制作,他們將會錯失文學作品其闡釋的、審美的價值。”這位學者便是論文集ReadingGraphs,Maps,Trees—ResponsetoFrancoMoretti的主編。一方面他認為這種矯枉過正的實證主義做法是對審美批評的扼殺,另一方面他也為它未來在人文學科的發展感到樂觀,因為它增進了文學研究領域的“同行合作”。長期以來“缺乏合作”已經成為“人文學科研究的標志”,而“定量研究的工作只能是合作的……需要無止境的搜集數據。”然而,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并不能等而視之——不能要求文學研究的教授們跟數學教授們一樣接受同行的研究結論。
五、總結
而莫萊蒂的“世界文學體系”作為重構世界文學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概念,其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跨學科的特征是獨出心裁的,尤其是在研究范式的更新上。斯皮瓦克指出:“其理論承諾了種種精良的參考工具。通過使人文學科科學化,進而實現合法化。[24]125”這實際上肯定了莫萊蒂在學科體制化的努力。 2014年,莫萊蒂的新書《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批評界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在馬克·歐康奈爾(Mark O’Connell)的紐約書評中,他的世界文學理論被高度評價為一種新的范式(paradigm)——計算批評(computational criticism)。人文學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進行研究范式的更新,正如理查德·羅蒂所言:“從來沒有一種健康的人文學科能夠歷經一二代之后保持不變的。[25]85”莫萊蒂的世界文學理論是否將會成為本世紀的楷模尚不能立下結論,然而這種新范式為我們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視野是確定無疑的。
[1] Finney G. Of Walls and Windows: What Germ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n Offer Each Other[J].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97:261
[2] 莫萊蒂. 進化、世界體系、世界文學. 尹星譯[M]//達姆羅什,陳永國,尹星. 新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本[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42-250.
[3] Moretti F. On Literary Evolution.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Forms[M]. Translated by Susan Fischer, David Forgacs and David Mill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88:262-278.
[4] Moretti F.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M]. Verso, 2005.
[5]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M]. 劉象愚,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6] 達姆羅什. 后經典、超經典時代的世界文學[J].汪小玲,譯.中國比較文學,2007(1):6-18.
[7]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現代世界體系: 16 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 第一卷[M]. 羅榮渠,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8] (美)弗蘭克·莫萊蒂. 世界文學猜想/世界文學猜想(續篇)[M]//尹星譯//劉洪濤,尹星.世界文學理論讀本.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23-143.
[9] Schreibman S & Siemens R eds.ACompaniontoDigitalHumanities[M]. John Wiley & Sons, 2008.
[10] Piazza A. Evolution at Close Range[J]. afterword to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History by Franco Moretti. London: Verso, 2007: 95-113.
[11] Carroll J. 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J]. Human Nature, 1995, 6(2): 119-134.
[12] Apter E. Literary World-system. 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 Ed. David Damrosch.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9:46-64.
[13] 阿普特. 文學的世界體系[M]//尹星,譯.劉洪濤,尹星.世界文學理論讀本.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43-159.
[14] 卡薩諾瓦.作為一個世界的文學.尹星譯[M]. //劉洪濤,尹星. 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06-123.
[15] 湯姆森. 國際經典中的焦點轉換[M]//尹星譯.達姆羅什,陳永國,尹星. 新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50-278.
[16] 史書美.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J].清華學報,(臺灣清華大學),2004(1): 1-29.
[17] KristalE. “Considering Coldly…”:A Response to Franco Moretti[J]. New Left Review, 2002(3):73-74.
[18] PrendergastC. Negotiating World Literature[J]. New Left Review, 2001(2):100-121.
[19] Dimock W. Genre as World System: Epic and Novel on Four Continents [J]. Narrative, 2005, 14(1): 85-101.
[20] Warkentin, G. Review: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J]. The Library 7.3 (Sep 2006): 342-344.
[21] Trumpener K. Critical Response I. Paratext and Genre System: A Response to Franco Moretti[J]. Critical Inquiry, 2009, 36(1): 159-171.
[22] Damrosch 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 HolboJ. Graphs, Maps, Trees, Fruits of The MLA,//ReadingGraphs,Maps,Trees—ResponsetoFrancoMoretti[M]. John Holboeds. Parlor Press, 2011:3-14.
[24] 斯皮瓦克. 一門學科之死[M]. 張旭,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25] 理查德·羅蒂. 回顧“文學理論”[M]//(美)蘇源熙編.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80-85.
(責任編輯:王 荻)
A Study on Moretti′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orld literature
CUI Yi-f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Coming to the 21st century, a lot of western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ve given redefinitions of "world literature" coping with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mong which Franco Moretti′s "LiteraryWorld-system" is an important one but hasn′t caught enough attention in China. Focusing on his theories, this paper is a study based on hi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world-system and his research methods of world literature, with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former critique and comments. In conclusion, my study gives a concrete depiction of the inclination of Darwinism in hi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thought of Marxism in his literary world-syst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ro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his research methods.
Moretti; Darwinism; literary world-system;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6-08-1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理論研究”(項目編號:14JJD750008)。
崔一非,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I109.5
A
1008-2603(2017)01-01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