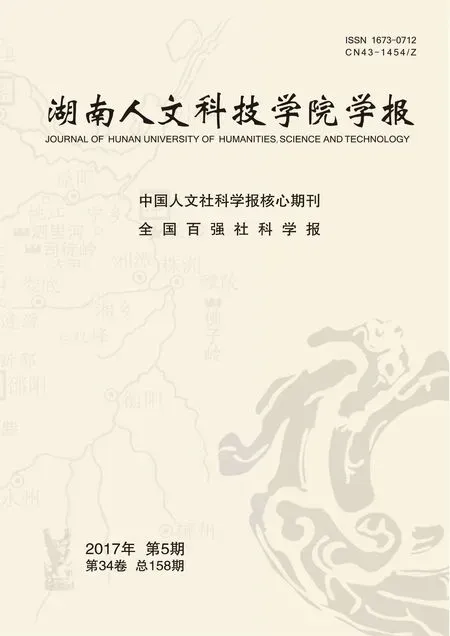被凝視與反凝視:論昆德拉小說中的兩類女性群像
趙 謙
(安徽商貿職業(yè)技術學院 人文外語系, 安徽 蕪湖 241002)
被凝視與反凝視:論昆德拉小說中的兩類女性群像
趙 謙
(安徽商貿職業(yè)技術學院 人文外語系, 安徽 蕪湖 241002)
在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敘事中,女性角色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以凝視理論為研究視閾,分析昆氏的小說作品,發(fā)現其中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一類是被凝視的女性群像,她們因自身的怯懦而甘愿受虐,在男性的凝視下逐漸喪失了自我存在感;另一類則是反凝視的女性群體,她們蔑視男權社會的道德倫理,用前衛(wèi)出格的言行來對抗男性的凝視,顯現出強烈的女權意識。男權社會的壓制和女性之間的矛盾沖突是造成她們悲劇的主要因素。只有女性同胞團結一致,才能構建與男性平等對話的和諧關系。
被凝視;反凝視;米蘭·昆德拉;女性群像
米蘭·昆德拉是頗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作家之一,梳理昆氏全部的小說文本,發(fā)現其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成被凝視和反凝視兩大群像。第一類女性群像習慣了逆來順受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淪為男性的附屬品。而第二類群像則不甘被男性壓制,她們用自己的方式對抗著不公的世界。以凝視理論為研究視閾,分析昆氏小說中的兩類女性群像,不僅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作品中的女性敘事模式,也能為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兩性矛盾提供啟示。
一、被凝視:逆來順受的女性群像
在傳統(tǒng)的男權社會中,“男人觀看女人,女人觀看被觀看的自己。”[1]弗洛伊德認為:“女人由于自己的體格和社會壓制她們的攻擊性,這便有助于發(fā)展強烈的被虐待沖動。”[2]在昆德拉的小說中,存在著許多被迫受虐的女性形象,她們性格軟弱,在男性凝視的目光下失去了主體性意識,成為男性們的玩偶。在《玩笑》中,柔弱的露茜童年時被幾個男性玩伴誘騙,他們在一處偏僻的地方逼她將衣服脫光,肆無忌憚地凝視她的胴體,隨后輪番將其強奸。因為畏懼周圍人的流言蜚語,無助的露茜選擇了隱忍,但這一痛苦的經歷卻始終困擾著她的心靈,她的一生都籠罩在陰影之中。《慢》中的T夫人是一位侯爵的妻子,嫁入豪門原本是很多女性夢寐以求的事,但這并未給她帶來想象中的幸福生活。侯爵整日在外面花天酒地,而孤獨的T夫人猶如一只困在牢籠中的金絲雀,內心的苦痛無人傾訴。因此,當她遇見騎士后,才會冒著極大的風險與他共度了難忘的一夜。然而,在一個男性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T夫人和騎士的愛情注定是沒有明天的,而她今后也必將繼續(xù)在侯爵的凝視下茍活,直至生命逝去。同樣,《笑忘錄》中的塔米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特蕾莎等女性,也在男性們的凝視下成為被控制的對象,死亡也成為她們自我解脫的唯一方式。
當然,除了上述被迫受凝視的女性之外,也有部分女性心甘情愿地希望得到男性的凝視,并將其視作女性的一種能力。對于這些女性而言,“成為男性‘凝視’的焦點成為了獲得男性認可甚至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有效途徑。在男性凝視的目光下,女性獲得了某種滿足感與存在感。”[3]在小說《慢》中,伊瑪居拉塔年輕時是一位絕色美人。她將美貌作為征服男性的資本,以此來獲得他們凝視的目光。在異性的討好與追求中,伊瑪居拉塔感到了滿足與快樂。
同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特蕾莎的母親曾先后被9名男士追求過,她用各種方法來考驗求愛者,希望從中選擇出一位優(yōu)秀的人生伴侶。《玩笑》中的埃萊娜大學時是男生們公認的校花,她沉浸于被異性關注的幸福感覺,最終從凝視她的男性中選擇了優(yōu)秀的澤馬內克。波伏娃提出:“由于女人從未真誠的接受過這個世界,她隨時準備對它采取一種受挫的態(tài)度。”[4]過分在意男性凝視目光的女性,在年老色衰后常常會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失落感與挫敗感,甚至由此導致精神的抑郁,《身份》中的香黛兒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小說開篇,她在海灘上散步時,發(fā)現了一個事實,“男人永遠不會再回過頭來看她”[5]。之后,小說圍繞著“身份”這一話題展開敘述,但直至結尾,香黛兒始終無法再次獲取男性們的關注,精神也陷入到了異化的狀態(tài)。
小說《慢》中,貝爾克曾經瘋狂地追求過伊瑪居拉塔,因為他相貌平庸而屢遭拒絕和嘲諷。多年以后,貝爾克獲得了成功,成為電視臺訪談節(jié)目的特邀嘉賓。而此時,伊瑪居拉塔已是一個中年婦女。她期待能夠借采訪貝爾克的機會與他重續(xù)前緣,不想卻被對方狠狠地奚落了一番。時光流逝、容顏變老,這是人世間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玩笑》中的埃萊娜步入中年之后,因為容顏和體態(tài)的變化而遭到丈夫的嫌棄。澤馬內克不愿與她相處,終日與年輕的女學生廝混在一起。心有不甘的埃萊娜決心找回失去的愛情,也因此落入路德維克設計的圈套之中。在《好笑的愛》收錄的故事《座談會》中,護士伊麗莎白為了吸引男性們凝視的目光,精神狀態(tài)變得極度失衡,以至于最終制造了一場裸體自殺的鬧劇。陳光霓指出:“男人凝視,而女人就是被凝視被控制的對象,這是一種權力運作的方式。”[6]昆德拉作品中的第一類女性群體正是在男權思想的操控下失去應有的話語權,成為男性的附屬品。
二、反凝視:為權利抗爭的女性群像
新女權主義者力圖“在對父權制思想文化體系進行批判的同時,號召女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重新以女性的視角審視人類文化的各個領域”[7]。在她們看來,女性的被凝視不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男性看和女性被看’的關系也轉換為‘女性看和男性被看’的關系”[8]。在昆德拉的小說中,也有一些女性無視男權社會的道德約束,用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來對抗男性們的凝視。她們“掙脫了男性話語灌輸體制下的‘他者’客體身份,以自己被釋放了的身體對女性本身重新獲得了認知”[9],這便是昆氏小說中的第二類女性群像。
在《不朽》中,洛拉完全無視男權社會為女性定下的道德準則。她不斷地變換男友,并用她飼養(yǎng)的貓來凝視和審查他們,稍有不滿便將他們掃地出門。更有甚者,洛拉愛上了自己的姐夫,也為此與姐姐阿涅絲撕破了臉。在阿涅絲遭遇車禍喪生之后,她不顧社會輿論對她的譴責,毅然決定為了愛情和姐夫生活在一起。洛拉以無畏的勇氣對抗男權社會的壓制,彰顯了強烈的女權意識,是新女權主義的一個典型代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薩比娜性格獨立、我行我素,也是一位反男性凝視的女性代表。在她看來,女性和男性一樣,也有享受性愛的自由和權利。在這一理念的驅使下,她同時與不同的男性交往,只為獲得性愛帶來的刺激和快感,完全不在意對方是否會和她結婚。在與托馬斯偷情時,薩比娜喜歡透過鏡子來凝視他,以此來獲取與對方平等的地位。托馬斯一生獵艷無數,絕大多數女性都在他的凝視下對他唯命是從。還有一個高個子的丑女人,她沒有順從托馬斯的命令,竟然反過來命令他脫掉衣服。這一反凝視的行為,也讓女權主義者為之拍手稱快。
《慶祝無意義》中阿蘭的母親因年少無知,和不喜歡的男性發(fā)生了關系并因此懷孕。按照常理,她應該和那個男人結婚,在懊惱和怨恨中虛度今后的人生,然而倔強的她沒有向命運屈服。自殺未遂后,她選擇生下阿蘭,然后離開那個男人,重新去找尋屬于自己的幸福。《無知》中的伊萊娜在前夫離世后,嫁給了對她關懷備至的古斯塔夫。她清楚自己并不愛古斯塔夫,與他結婚主要是出于心中對他的感激。強烈的女性意識讓伊萊娜無法過一種相夫教子的平靜生活,她背著丈夫與心儀的約瑟夫私會,這也折射出她對于男權社會倫理道德的反叛。在《笑忘錄》中,芭芭拉是一名女權主義的代言人。她在別墅中舉辦了一次面向青年男女的裸體聚會。聚會中,女性們一改往日被男性凝視的慣例,大膽地嘗試凝視男性。昆氏小說中反凝視的女性們用自己的言行,對男權社會發(fā)出質問與吶喊,顯現出新時代女性對于追求與男性平等待遇的強烈渴求,也反映了昆德拉對于女權主義思想的認同與理解。
三、內部的矛盾與沖突:女性悲劇的成因
“昆德拉筆下的女性開始于輕的美麗,終止于重的殘酷”[10],小說中無論是被凝視的女性還是反凝視的女性,她們的人生都以悲劇而告終。對于多數評論將昆氏小說中女性們的悲劇歸結于她們自身的弱小和男權意識的強大,作者僅表示部分贊同。李銀河指出:“蔑視女性的人不光在男人中有,而且在女人中也有。”[11]昆氏小說中女性們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由她們的內部矛盾所導致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告別圓舞曲》中,幾名男性闖進了女子溫泉浴室,聲稱要拍攝電影片段。這一冒失的舉動,侵犯了女性的隱私權,踐踏了她們的尊嚴,因此遭到了少女奧爾佳的強烈抗議。這本應是一場女性群體維護自我尊嚴的抗爭,然而奧爾佳的行為非但未得到浴室中其它中年女性的支持,反而遭到了她們無情地嘲諷,無奈的奧爾佳只能獨自憤然離去。為什么奧爾佳挺身而出,想要維護女性的尊嚴,結果卻遭到一群中年女性的攻擊呢?對此,昆德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她們(容顏變老的中年女性)極其憎惡年輕的女性,希望展現她們在性別上已然無用的肉體,來嘲弄和侮辱女性的裸體。她們想通過自己毫無優(yōu)雅可言的肉體來復仇,來損害女性之美的榮耀。”[12]此外,《無知》中強勢母親對伊萊娜的壓制、《笑忘錄》中婆婆對塔米娜的無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母親對特蕾莎的虐待及《不朽》中的洛拉和阿涅絲的反目,都凸顯出女性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在男權思想的壓制和女性內部矛盾的雙重作用下,昆氏筆下女性們的反抗多以失敗而告終,等待她們的只能是悲劇的人生。張春梅指出:“兩性本身應多質疑以往權利話語的合理性,在懷疑中建構適合兩性健康發(fā)展的平臺。”[13]
昆德拉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揭示了現實世界中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質疑男權社會壓制女性的種種行為,表達了他對女性同胞們的人文關懷與同情。兩性關系是昆德拉一直在思考的論題,筆者以為,男女之間本無高低,“平等”才是兩性和諧發(fā)展的基礎和關鍵。男女之間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體諒、共同發(fā)展,這樣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四、結語
女性角色在昆氏小說的敘述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她們凝集了昆氏對于女性的態(tài)度與認知,對于理解其作品中的哲學內涵頗具啟示作用。縱觀當前的研究成果發(fā)現,學者們對于昆氏小說中女性形象的研究缺乏整體性的全景視閾。因此,從全景視閾來解讀昆氏小說中的兩類女性群像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昆氏對于女性的態(tài)度與看法,也能為分析其小說提供新的視角。
[1]懷特.后女權主義[M].王麗,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74.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91.
[3]趙謙.凝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女性主義解讀[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5(3):44.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686.
[5]米蘭·昆德拉.身份[M].邱瑞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15.
[6]陳光霓.凝視:莎樂美主體性的建構與解構[J].外國文學研究,2013(2):53.
[7]吳慶宏.弗吉尼亞·伍爾夫與女權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57.
[8]周賓.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80.
[9]張李娜,史小建.女性身體言說身份困境:再論昆德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名作欣賞,2011(8):139.
[10]崔明路,張學仁.昆德拉之重[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159.
[11]李銀河.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潮[J].哲學研究,1996(5):66.
[12]米蘭·昆德拉.告別圓舞曲[M].余中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66.
[13]張春梅.男性中心主義的沒落:重新解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156.
GazingandAnti-Gazing:TwoKindsofFemaleImagesExistedinKundera′sNovels
ZHAOQian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English,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Women characters 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narration of Milan Kundera′s novels. Analysis of Milan Kundera′s novels through the literary theory of gazing, two types of female images can be found. The first women group lost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the gaze of men because of their cowardice. On the contrary, the second group disdained the moral ethics of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they showed a strong femal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Besides man′s power, women′s inner contradictions also contribute to their tragedies. Thus, only with firm cooperation among women could they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n the society.
gazing; anti-gazing; Milan Kundera; female images
2017-06-1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米蘭·昆德拉小說中的符號隱喻研究”(SK2017A0661)
趙謙(1982—),男,安徽蕪湖人,安徽商貿職業(yè)技術學院人文外語系講師,碩士,研究方向:世界文學。
I106
A
1673-0712(2017)05-0014-03
(責任編校:舒陽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