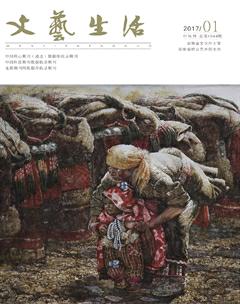淺論師陀《果園城記》——三類人物群像與果園城
郭琨
摘 ? 要:《果園城記》是師陀歷時八年所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幾乎是與抗日戰爭時間相重合。《果園城記》的最初版本共包括十八篇短篇小說。這些短篇小說雖獨立成篇,但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都以“果園城”為表現對象加以展現。其中,作者塑造了許多人物形象,本文將其分為留守者、離去—歸來者和跋涉者三類群像,試從不同人物類型入手,分析他們與果園城的關系。
關鍵詞:留守者;離去—歸來者;跋涉者;果園城
中圖分類號:I207.427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02-0009-01
1936年7月底,師陀在從北平去往上海的途中去了朋友祖居的小城住過一段時間,因而萌發了創作動機。1938年9月,師陀在上海完成了該集的第一篇小說《果園城》。師陀說“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一個活的人”①。
一、留守者與果園城
(一)生活無虞者
如孟林太太、素姑、徐大爺、徐大娘、朱魁爺。孟林太太每天照例在她的老宅中睡午覺,屋里的鐘即使停了也不會影響她的生活。對于她來說,果園城安靜悠閑,甚至懶惰。但果園城還是孤獨單調的。素姑在她十二至二十九歲間,已經為自己繡好了足夠的衣服,為孟林太太繡好了壽衣;每天來她家中的人都是固定的——送水的、賣絨花的。當她周圍與她同齡的、甚至比她小的女孩兒都出嫁后,她的生活變得除孤獨外更添了些凄涼。徐大媽也是孤獨的。她每天期盼著兒子的來信,可是她卻不知道兒子早已客死他鄉。知道實情的徐大爺在承受孤獨的同時,還要承受失去兒子、欺騙老伴兒的痛苦。徐氏夫婦在看到“我”時無比的激動,在送別“我”時無比的不舍,他們的舉動全是因為“我”是與他們過去的記憶、與他們的兒子有相關聯系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
朱魁爺有很多出仕在外的機會,但他不愿意離開果園城。他把自己的家庭和果園城都劃歸在自己的管轄范圍之內,只不過二者的統治方法有所差異。在家庭中他采取的是專制中最專制的方法,兒子、妻子都必須完全服從于他的意志之下;走出家庭,進入果園城,他則是“比頂和善還要和善”,以這種方式鞏固他對于果園城的統治。但是朱魁爺的權柄在民國十六年被打破,他的四太太跟家里的車夫私奔,他的土地被沒收、宅子被封,朱魁爺也到省城避難。當他再次回到果園城時,他的權勢已不復從前。太太們對他的反對象征著他在家中的權勢的崩潰。從此,朱魁爺將自己鎖進宅子中,果園城由他所掌控的城,成為他孤獨終老的城。
(二)為生計操勞者
如說書人、老張、賣煤油人、郵差先生。對于他們而言,果園城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故鄉。賣煤油人“只要摸摸他就知道是誰家的,甚至是誰用的”②煤油燈;郵差先生即使不認識寄信人,但他們每次遷移了地點他都知道。假使有沒帶郵票又忘記帶錢的人來寄信,他也會貼上郵票,因為他相信寄信人一定會把錢送來。他們身上有著樸實、溫情和對果園城熟悉的一面。但同時,果園城還有它殘酷的一面。窮苦的說書人死后只能穿著破長衫、裹著破蘆席葬到亂葬崗,而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老張半生勞苦僅值一塊錢,被趕出布政大門的他,終日以乞討為生,最后在馬夫人做壽當天死在布政第臨街的墻腳。
留守者眼中的果園城是這類“亞細亞”式的小城,城中人經歷“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則,一種散漫的單調生活使人們慢慢的變成懶散,人們也就漸漸習慣于不用思索”③。他們與其說在一天天的生活,不如說在反復過著一天的生活更為貼切。這種城保存著古老中國最初的面貌,它還有著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如老張對于布政第的愚忠,是千百年來仆從之于東家的關系的延續。而朱魁爺則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提到的“長老統治”者。他作為手持權柄的鄉紳,與官員一起代表著果園城的“公理”。從師陀把說書人稱為“世人特準的撒謊家”④可以看出,他對于這些類似于果園城的城是批判的。但同時師陀又描寫了諸如賣煤油人、郵差先生這類人的存在,他們展現出的恰巧是小城具有人情味兒,充滿溫情的、平和的一面。這樣交織著冷與暖、新與舊等諸多矛盾的小城正是近現代經濟還未侵入前的中國小城的真實寫照。
二、離去—歸來者與果園城
離去—歸來者是指出生于果園城,待到青少年時以讀書為契機得以走出果園城,畢業后又回到果園城的人,可分為無所學者和有所學者。
(一)無所學者
如劉卓然、胡鳳梧。劉卓然和胡鳳梧從小就被嬌寵,溺愛而沒有對父母等親人的尊敬和愛,劉卓然在父親死后的第三天就結了婚,胡鳳梧則是在孩童時就恐嚇自己的妹妹要把她嫁給下人,更不用說對家族發展的責任感。因此,他們到了省城讀書后就更肆無忌憚的開始了他們了享樂之旅。學無所成的他們回家后繼續著享樂的生活,錢不夠就變賣祖宗基業,最后劉卓然只能圍著一條麻袋,過著乞丐的生活,靠做“巡閱使”編造故事,騙取錢財為生。胡鳳梧在變賣完家產之后,在土匪興起的年代做起了肉票中間人,最終因貪婪被土匪槍殺。
(二)有所學者
如葛天民、油三妹、傲骨。葛天民從農業學校畢業后選擇回到故鄉建立農場。農場經費缺乏時,甚至更困難時,他都沒有放棄。然而,當農場有了經費時,他卻被迫辭職。葛天民所表現出來的無欲無求、隨遇而安,只是他的自我欺騙。果園城的封閉、落后成為了扼殺他理想的地方。油三妹是進步學生的代表,當她成為果園城的一名小學教員后,她漸漸體會到了壓抑和孤獨,。單調和壓抑之下,她最終以服食藤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傲骨畢業后成為一名中學教員,他以為得到了一次試練的機會,可周圍都是些“只知道拍馬、吃酒、打牌、吊膀、欺騙”⑤的同事。傲骨最后丟掉了教員的工作,回到了果園城,成為了人們口中那個滿腹牢騷的人。對于有所學者來說,果園城保守落后、缺乏變革意識,并對這些有著新思想、新知識的人充滿著排斥。
三、跋涉者與果園城
跋涉者是曾經在果園城生活過,因為種種原因離開果園城的人。他們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故地重游,或者永遠不再回來。小張和徐立剛都是因為革命理想而離開果園城的,徐立剛客死他鄉,而小張因任務回到過故鄉。其余的跋涉者大多是因為果園城有他童年美好的記憶,對于他們而言果園城是他們的精神家園。
“我”就是在童年記憶的驅使下,再次回到果園城的。此時,素姑已經變得枯干憔悴;朱魁爺和胡左馬劉也早已衰敗;賀文龍已經放棄了成為作家的夢想,曾經的女同學大都經歷了“嫁了并且死了”的結局。孟安卿十二年后重回果園城,發現賣梨糕的小販改賣紙煙了,姨母身子還扎實著,而自己卻已經被果園城人完全遺忘了。大劉姐看到往日熱鬧的中心已經由十字街轉移到了火車站,手藝精湛的錫匠因為眼睛誤入了鉛,成了一位盲人乞丐。而對果園城再無牽掛的孟季卿則再沒回去過。
師陀塑造跋涉者形象與其自身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師陀本人就是一個跋涉者,他出生于河南杞縣,高中畢業后到北平,后又到上海。故鄉是深埋在跋涉者心中的一顆種子,師陀在描寫了跋涉者回到果園城所見物是人非而產生的深深的失望、惆悵的情緒中又加入了些活潑靈動的生氣。師陀稱“我憑著印象寫這些小故事,希望匯總起來,讓人看見那個黑暗、痛苦、絕望、該被詛咒的社會。又因為它畢竟是中國的土地,畢竟住著許多痛苦但又是極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鄉的果園城來把它裝飾得美點,特地請漁夫的兒子和水鬼阿嚏來給它增加點生氣”⑥。
注釋:
①②③④⑤師陀.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師陀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269,361,284,355,329.
⑥劉增杰.果園城記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師陀研究資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99.
參考文獻:
[1]師陀.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師陀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3]錢理群.試論蘆焚的“果園城”世界[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01).
[4]劉增杰.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師陀研究資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