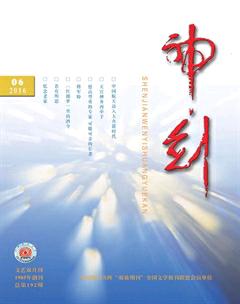要好故事,更要經典文本
對品質的追求源自對生活的體認
傅逸塵:近段時間,隨著由你原著并編劇的電視劇《麻雀》的熱播,關于諜戰的話題又開始在網絡和新媒體上流行起來。在各種討論中,我注意到一個關鍵詞,那就是品質。在剛剛閉幕的第十三屆中國長春電影節上,眾多圈內人士共同發起了“聚焦質量,共贏未來”的倡議,也是對近年來影視劇市場亂象叢生、爛片橫行的一種反撥和回應。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麻雀》,你有著怎樣的定位和期待?
海飛:我想先說一說為什么會有《麻雀》。首先我喜歡“麻雀”這個名詞,盡管麻雀在飛禽中是屬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種,但是我覺得“麻雀”兩字里,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在我眼里,一切潛伏都將是人性的潛伏,我必須找到一種不起眼卻暗流涌動的符號,那么麻雀最貼切。然后我想做的是一部燒腦戲,步步為營、驚心動魄,主人公分分秒秒都命懸一線,一定要有那種懸崖之上走鋼絲的味道。于是在兩年多前,先有了一個發表于《人民文學》上的中篇小說《麻雀》,接著有了改編的劇本。而我心中所想的是,這個劇需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那么前提就是你所說的:品質。所以細節真實、邏輯合理、情感動人,是必須做到的。
傅逸塵:品質的保障,除了以大制作為基礎,還需要在基礎的細節方面用心營造。現在很多軍事題材影視劇,其實從資本的投入來看都是大制作,但是觀影效果卻并不一定和資金投入成正比,原因就在于生活質地方面出了問題。尤其是年代戲,主創們如果不下功夫去研究歷史,研究當年的生活場景和風俗習慣,就會顯得虛假,觀眾也會跳戲。
海飛:你說得很對,所以《麻雀》這部戲,就要從這些案頭性、基礎性的工作做起。無論是服裝,道具,化妝等等,都需要力求向那個時代最真實的一面靠攏。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上海是一個有著眾多洋人集聚的城市,所以西洋音樂,西洋味道,永遠充斥在其中。當時黃包車上的車牌號碼,是幾位數,這個需要道具部門去查的。那時候汪偽政府用的旗,和蔣氏政府是略有區別的。電話號碼是幾位數,也是需要做功課去了解的。我甚至認為,民國時期的辦公桌該是什么樣的,就得用什么樣的。那時候的旗袍,那時候的手提包,那時候的背景音樂等等,都需要符合20世紀40年代初的特征。甚至是槍械,如果我們找不到合適的槍械,我們完全可以改掉劇本中使用的槍械。比如“掌心雷”,這就是一種射程極短的槍,便于攜帶,小得能完全握在“掌心”中。這十分適合沈秋霞這樣一個穿呢子大衣的女特工使用。
比如特工機關的服裝,只要看過電影《色戒》你就會知道,易先生從不穿軍裝,部下也全是黑衣特工。汪偽特工是沒有制式軍服的,就像我們的便衣警察一樣。同樣,在同一個時期的陪都重慶,軍統人員配發軍裝,因為他們屬于軍人序列,但是機關工作人員和軍統特工執行任務時,也是不穿軍服的。比如女性工作人員,統一旗袍,而且是陰丹士林旗袍。這是我采訪過大陸最后一名女軍統王慶蓮,她告訴我的。比如上海街頭的電車,開車人是穿公司制服的,還戴著制式帽子。比如石庫門,在上海是有大量石庫門的,石庫門是一種奇怪的房子,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也不像江南的臺門屋,而且還含著那么一點兒西洋的味道。但是卻有小天井,會客室,還有老虎窗。說白了,其實是中西合璧的一種房子,“亭子間”就是石庫門所特有的。石庫門正門門楣上一般會有磚雕的字,比如“同福里”,或者“秋風渡”。比如劇中出現的《語絲》雜志,是可以查到封面樣式的。而服務員應該穿的服裝,郵筒、菜場、廣告墻的模樣,都需要先考證,再制作。至于在劇本中出現的音樂,路名,涉及的人名和提到的事件,比如明星電影公司,比如演員白楊或者黎錦暉創辦的演藝學校,比如周璇的歌曲,哪怕是咖啡館和飯店,在劇本創作的過程中,都已經經過了詳細考證。我的意思是,在此劇的拍攝過程中,也要如此的嚴謹。在我眼里,劇中的劉蘭芝、扁頭,說話會是帶上海腔調的,但這種腔調不能過多,只適合劇本中設定的人物使用。而畢忠良和陳深,作為戲量多的重要角色,最多偶爾使用一兩個上海腔的詞。畢竟我們要面對的是全國觀眾。
傅逸塵:事實上,作為中篇小說的《麻雀》,其中也是做了大篇幅的心理描寫的,對于人物情感的鋪墊和描摹非常細膩。這些文學性較強的元素,到了電視劇本中,會不會被擠占和壓縮呢?
海飛:你說的這個問題很關鍵,在劇中我是要盡量保留小說中的韻味,那種對于人情人性的細膩鋪排。所以,在劇本創作過程中,使用了許多場景描述和人物內心的描述,這是為了有助于導演和演員找到感覺。每個人物,首先是在編劇心里活起來,成長,扎根在編劇腦海里的。所以這個劇,需要的是原著小說及劇本中營造的那種氛圍,換句話說,就是要具文學性的。我們盤點一下有口碑的影視劇,其實都具有文學性。一個眼神,一片落葉,街頭人群密集,突然響起又突然靜止的嘈雜之聲,以及火車穿過了平原,晃蕩的車廂里四目相對等等,是需要恰到好處的表現和表演的。甚至對白的急與緩,輕與重,從容與緊迫,都需要在故事進展中同步掌握。麻雀是需要“演”的,無論是“話中有話”,還是肢體語言,或者是情緒渲染等各方面,都已經在劇本中各有體現。也就是說,演員是需要盡力去領悟琢磨劇本,然后去達到最佳的表演狀態。但是有一條,我覺得這個劇中斗智斗勇的主要角色,表演需要內斂。
總之,本劇的制作過程中,細節真實、邏輯合理、情感動人,是必須要盡力做到的。這不是槍火劇,也不是鬧劇,在劇中不可能出現狗血,獵奇,血腥,感觀刺激等低級的吸引觀眾的畫面。這是一部靜戲,一部充滿質感的劇。情節可以是層層推進,可以是劍拔弩張,一波接著一波,節奏也不用慢下來。但是暗戰雙方的表象都必須是波瀾不驚。仿佛我們看到的是平靜的湖面,而每個人的內心,都如同湖底下澎湃而涌動的暗流。
溢出的文學支撐影視的繁盛-
傅逸塵:最早接觸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說,在整個70后作家群中,你的個人風格顯明而出挑。然而從《旗袍》開始,短短幾年間,《旗袍2》《大西南剿匪記》《從將軍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鐵面歌女》《代號十三釵》《隋唐英雄》《花紅花火》,一部部影視劇的接連推出,使得“海飛現象”成為橫跨文學與影視兩界的熱門話題。正在熱播的《麻雀》,在我看來是你諜戰劇創作中文學性極強的一部。從中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是一種極有難度的寫作啊。
海飛:說到難度,首先當然來自文體的轉換。但是對編劇而言,最大的難度還是來自于對品質的追求。好的諜戰劇,要的是心理緊張,而不是槍聲大作,所謂的含而不發。比如各種用刑以后血肉模糊的慘狀,遠不如在走廊上聽到撕心裂肺的叫聲來得讓人心驚。比如主人公面臨危機時的種種考驗,必須在瞬間去化解,說白了是一場智力大比拼,說白了也是一場場的闖關游戲。特別要說的是,兩難是最令人糾結的,在以往的種種諜戰劇中,我們總是忽略了“難”的程度,所有主人公面臨的問題,總會輕易地迎刃而解。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是一種自我放低的做法。如果往左走,危險。往右走,是另一種危險。而停步或退步走,是更大的危險。這時候主人公要怎么走?那么這樣的劇,才會是觀眾需要的。那種把人心“拎”起來的感覺,要經常性出現。劇本中對緊張和懸念的橋段已有充分表現,拍攝時就要掌握節奏了。也就是在展現危機時的“松緊”程度,是短時間化解,還是把時間和懸念、緊張感拉長,這需要恰到好處的把握。
傅逸塵: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風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質的小說文本,再轉化為影視劇產品。無論是小說文本還是電視劇劇本,在故事的層面都非常精彩、扎實,似乎編織“好看”故事對你而言并不困難。很顯然,你在劇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學抱負。
海飛:小說有無數種。小說幾乎就是一個讓人迷戀的妖怪或者仙女。當下的許多小說,過度沉迷在自我中,各種情緒在小說中滋生,雷同得如同復印。“好看”小說,只是小說中的一種,比其他的小說更容易傳播。但是,就我而言,創作過程中并未有那種為了傳播而傳播的意識。莫言曾把獲諾獎時的演講標題取為:講故事的人。可見講好故事是難中之難。四大名著,無一不是經過了數百年檢驗的好故事。當然,講故事的技術有高有低,如何融合思想、語言、結構等,都是一個巨大的難題。這就是作家會碰到所謂的瓶頸問題。我始終覺得,好小說應該是一個汪洋恣肆的故事,這故事是泥沙,但是夾在文學的“水”中,滾滾而來,瞬間擊中讀者的閱讀神經。我覺得至少在一個時期以內,我會在這條道路中前行,像一個安靜的說書人。客觀來說,優秀的小說家大規模投身影視編劇,成就了中國影視近三十年來的繁盛與輝煌。但這種源自文學溢出效應的支撐正在迅速衰減。
類型是呈現生活橫切面的舞臺
傅逸塵:整體而言,你的創作有著強烈的煙火氣息,擅長在日常生活的流態中描摹活色生香卻又感傷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歷史的輪廓和面影;你的劇本通常都聚焦個體的情感糾葛和命運軌跡,在或明或暗的戰場上檢視人性的復雜和純粹。對于個人化的風格,你有怎樣的追求?
海飛:說到風格,我承認對復雜人性的解讀與描摹充滿熱情,極度迷戀。我一直認為,小說有無數種風格及其所必須承載的使命。各種類型的小說中,我更傾向于用文字講述人間悲歡。我喜歡把小說中的“人”放低。在那個動蕩不安的焦慮的年代,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說或者一個劇本,把主人公放得更低些,就有更大的創作空間和虛構的可能性。我們誰也不知道,闖王李白成手下有一個音樂愛好者,如果有,他是怎么樣的人生。我們也不會知道,上海起士林咖啡館里一個廚師,他經歷了怎樣的跌宕人生。而那個年代發生的事件,那個年代的服裝,公共設施,地名,必須真實。我認為能做到這樣,創作小說的態度,就足夠嚴謹。我們不能知道那時候的霧霾到底有多少指數,至少也得準確寫出,那時候到底有沒有發生某件大事。
我為什么迷戀這樣的小說風格。這不是小情緒,也不是語言狂歡,是在展現讓人動容和歌哭的人生,呈現一種年代風起云涌的生活畫卷。每個作者的創作方向都不一樣。我希望我是站在一本打開的真實紀事的書面前,幻想那個年代發生的種種悲歡。我愿意是一個復述者或者聆聽者,甚至愿意和劇中人,一起細數一件大衣上細密的針腳。因此,在創作中,我首先想到的是要高度還原上海生活。我本人對上海十分有好感,是因為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上海永遠是一個最適合發生故事的地方。因為上海有黃浦江,還有和黃浦江交匯的蘇州河,所謂大江大河,浪里有多少的恩怨情仇。從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上海灘》《刀鋒1937》等劇中,我們就可以感受到。呢子大衣、歌舞廳、叮叮響著的電車,哐當當響著的電梯,黃包車和小汽車夾雜在人群車流中,西餐廳不輸于現在的堂皇與雅麗,以及賽馬場、球場、影劇院等時尚場所……我們的場景不需要設置這些,但是我們在制作、拍攝、演出的過程中,每個人心中就是要裝著那么一個陳舊而華麗的上海。而更進一步,如果我們著眼細節去打造一部劇,那么弄堂里其實是會隱隱地響起“梔子花,白蘭花,五分洋鈿買一朵”的叫賣聲的,這樣的聲音是約定俗成的,也許網上也能搜得到這樣的音頻。所有的一切,會構成一種考究的“腔調”,這也恰恰是上海人最講究的地方。上海魚龍混雜,是一個巨大的移民城市,尤以江浙人為多。而煙熏火燎的生活,是最真實的彼時人間。仔細看舊上海照片,會發現弄堂里,一根竹竿橫跨弄堂兩邊,其實是有人在曬著棉被或衣服的……
對諜戰的探索連著對精神的勘測
傅逸塵:一段時間以來,各種雷劇橫行,不僅倒了觀眾的胃口,也給人這樣一種錯覺:劇本是一群人關在賓館房間里、純憑想象甚至“胡編亂造”攢出來的。然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多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有著原型,你怎樣看待生活真實和虛構想象之間的關系?
海飛:原型和虛構并存吧,基本的人物心理、常識性的生活邏輯以及涉及史實的部分必須真實。比如《回家》這部作品,其中涉及的地名全部真實,在創作開始的時候,我就畫了一張路線圖,給主人公設定了一條真實的回家之路。小說中所提到的大事件相對真實,如日軍從寧波登陸,里浦慘案等。在創作之前,我曾經看到過一個視頻,寧波姜堰敬老院的一位抗戰老兵,在喝下一碗黃酒后,高唱《滿江紅》,這讓我十分動容,仿佛在歌聲背后聽到了當年的槍炮之聲。而日本軍人在戰時的種種細節,我都是從一些日本畫冊、書籍中了解,我沉迷在這種對故舊事物的窺探中,并因此感到無比的快樂。
傅逸塵:諜戰題材目前似乎已經進入了瓶頸,下一步還會有怎樣的發展空間,你會在哪些方面進行探索或者創新?
海飛:現在的很多諜戰或者推理劇,都陷入了一種模式。我想尋找一點“新”的東西,所謂不破不立,所謂不出新,寧不寫。我迷戀那種舒緩之中顯現的緊張。打個比方,電影《風聲》中,是有那種強烈的壓迫感的。就是誰都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么。那么《麻雀》也需要是,不停地設套和解套,而且這個設的必須是雙重的套,讓你解起來無比困難。如果是槍火劇,十分簡單,一槍就干掉了你。這并不令觀眾期待,他們想要的恰恰是,下一分鐘是誰死
未曾聞到一點槍聲,但是分分秒秒都充滿著殺戮。所以《麻雀》的風格要獨特深沉、鏡頭遼闊、畫面大氣、音樂洋氣,讓人覺得這是有品質的大片,展現的是最真實的上海灘特工精英的舐血生涯。
傅逸塵:用最通俗的故事表達最崇高的精神,創作主體對諜戰劇的探索,從深層次看是對幽微人性心理和復雜精神空間的勘測,亦是對時代主流價值的建構。
海飛:你說的沒錯。我是一個有著強烈軍旅情結的退伍老兵,每次看到軍旅題材影視劇,都熱血沸騰,仿佛讓我回到那段軍旅生涯。情懷是很重要的,很多創作者認為情懷兩個字大而無當,看不到摸不著。還有一些編劇認為,情懷是空的,講好故事就行了。其實不是,情懷是一種精神,一部戲沒有情懷,會松垮下來。劇中主人公沒有情懷,那就是緊張機械的故事堆砌。而創作者心中沒有情懷,作品也會是蒼白的。當初寫完《麻雀》小說的時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我替陳深在小說中活了一把,而且我的心中有了一種莊重感,甚至為逝去的英雄在心底里默哀。而在小說改為劇本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強了情感糾葛,以及設計各種扣和解開各種扣。其實我們這個時代,一直都是在尋找英雄,需要著英雄。
“諜戰”作為一種題材類型,會一直存在并永無止境。諜戰劇不光展現驚心動魄的革命往事,也要傳達一種“唯祖國與信仰不可辜負”的崇高感,這種向上的,催人奮進并且感召著人的血火青春與瑰麗人生中,蘊含著我們這個時代亟須補充的精神鈣質。
責任編輯/劉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