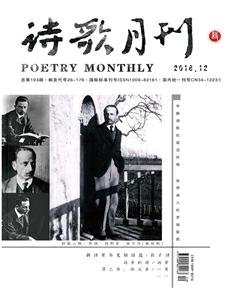周統寬
艾滋病患者之死
他死了
像條斂巴發霉的蘿卜
火葬場
沒多收得他父母一分錢紅包
一把火就把他燒掉了
他父母用最便宜的刨花板骨灰盒
帶回了村外的亂墳崗
他們就兩個人
那個父親負責挖坑
挖得不是很深
那個母親負責抱著在那等
下葬時
我看他們
像腌蘿卜酸一樣
放一層蘿卜又放一層鹽
他父親放了兩封炮
他母親偷偷哭了兩聲
行刑前的呼救
太陽很好
我踩著單車上班
在紅光路口等紅燈
我雙腳撐地
我看見前面的一輛摩托車
二十三只鴨子
都被捆綁雙腳
倒掛在后架上
它們都拼命地抬著頭
遠離地面
看著我
嘎嘎叫
黑貓白貓
白貓將抓到的耗子
標記為白色
黑貓將抓到的耗子
標記為黑色
在這之前,我以為
白貓只抓白耗子
黑貓只抓黑耗子
月亮彎著腰刷不去我的淚痕
有一種愛叫碰瓷
一碰對她眼淚就流出來
我早已把她的名字
從我的心里擦去
但跌落的粉末
仍像梨花一樣白
撲到我的胸口
你看它一條裂紋已裂到底
仍滴水不漏
但你沒有看見
我的雙手像兩個鋦子
緊緊地扣入裂紋的兩側
月亮彎著腰
怎么刷也刷不去
黏在裂紋里的漬漬淚痕
今夜我要跟月亮分床睡
昨晚我跟月亮聊了一夜的夜總會
她不緊不慢地聽了一夜
直到黎明把小烏擠出鳥窩
她躲過西山蒙頭就睡
免得挨太陽的白眼或云朵的譏笑
昨晚沒得睡
今晚眼皮太累
你自個兒瞧瞧
徹夜未眠的燈
照亮大街小巷的角落
也找不到一串想家的稻穗
池子里盡是火辣辣的
直勾勾的眼和白花花的腿
今晚我要跟月亮分床睡
我要去守取那幾畝旱田水
我的陽臺有一支打氣筒
單車早就沒有了
打氣筒仍留著
我把它留在陽臺的一角
一天
黃昏騎著單車來到我的樓下
我讓她等一會兒
轉身就去陽臺
拿著氣筒跑下樓
我給她的單車打了兩手氣
她滿臉通紅
雙手推著龍頭
踩著左邊的腳踏板上車
笑笑盈地走了
我記得那天是一月七號
我不能再用一片瓦來形容那片天空
我那土里土氣的小名
被我換成了吃國家糧的糧本
我那攆進十八弄的小數民族身份
被我上世紀八十年代換成了高考加分
慶祝高中考取中專的喜報
貼滿母校教務處的宣傳窗
放炮慶祝喜獲貧困縣的籍貫不變
我那命犯桃花的性別也不變
掐不出大富大貴的生辰八字更加不能變
我抖落竹筒里的一簽命運
一畝三分的稻田抽穗出產值的濃煙
我不能再用一片瓦來形容那片天空
麻雀小小的翅膀矮矮地飛不出霧霾
敲對腦殼——低垂的稗穗
我走之底的腳印是多余的
總是這樣不由自主來到這里
月亮斜靠著掉灰的墻
雙手插進口袋
向我投來不屑的眼神
你走過的石板橋
已拒絕和我來往
二狗子家里的狗非常稱職的
出來叫了兩聲又彎了回去
二妞媽又在廚房里
傳出了剁豬菜的聲音
橋下的流水
依然按著姓氏筆畫有序地流去
水草順著偏旁部首的起筆筆形排列
我走之底的腳印是多余的
魚是唯一能在水里透氣的人
一滴淚也是一片海
潮濕的火焰熄滅了
魚不長翅膀
拋棄了天空在海里翱翔
我在楚國都城郢等魯班
借我一把鋸子
伐倒下一個時代的倒影
我要從陳舊的木頭里
拔出你生銹的釘子
把刨子向前推進
沒有會走動的岸
只會有倒下的帆
魚在海底下深呼吸
嘲笑死神和陽光
嘲笑飛機汽車輪船
嘲笑衛星定位的航母
還有冒充魚類的潛艇和魚雷
魚目明亮
魚尾擺過明擺著的事實
鼓起腮吹出一串大國博弈的泡泡
漫過審時度勢的悲傷和人類失聯的良心
離刀遠點
每天從廚房外面進
從三國里頭出
刀光檢閱著劍影
在每一個節點安營扎寨
殺雞殺鴨殺鴿子
敬猴敬鬼敬神仙
切土豆切蘿卜白菜
切那個沒肝沒肺的雞肋
高過廟堂之高的滾背刀
撿掉了楊修提前收拾好的包袱
刮骨療毒的只有華佗一個
處西川之遠的青龍偃月
一刀斷送了再也哭不回來的江山
冷灰擠破了灶頭
阿斗離劉邦有多遠
我就想離咸陽有多遠
周統寬,男,壯族,1966年生于廣西融安縣,著有詩集《枯水期的魚》。作品散見《廣西文學》《詩歌月刊》《紅豆》《太河》《南國詩報》《北歐時報》和《常青藤詩刊》等,另有詩作入選《華語詩歌年鑒》(2013-2014卷)《21世紀世界華人詩歌精選》等重要詩歌選本,廣西《麻雀》詩刊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