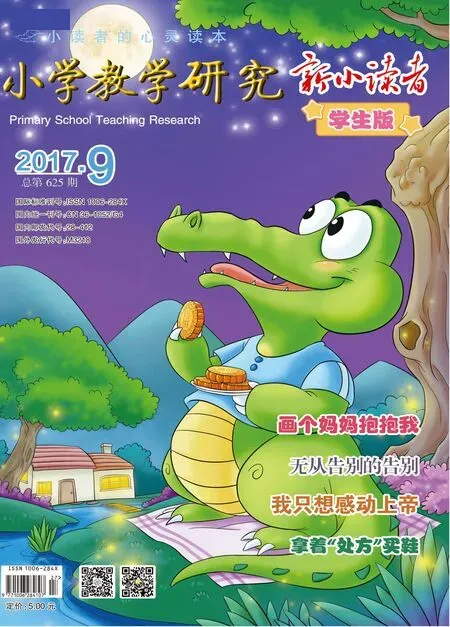10歲那年,我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文/李崢嶸
10歲那年,我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文/李崢嶸
10歲以前,我是一個很乖卻常受欺負的小孩。
進入新班級,我的第一個障礙就是聽不懂同學說話。我的父母是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這座小城工作的,我既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會講當地方言。我用老家話自我介紹時,引來哄堂大笑。
大人不知道,在孩子的世界里,和別人不一樣是很容易受到排擠的。我家距離學校最遠,沒有人和我同路。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打。父母問我怎么回事,我說是自己摔的。最嚴重的一次是課間頭磕到水泥欄桿上,流了一腦門的血。老師把我和距離我最近的鼻涕男叫到了辦公室。鼻涕男的父親就在學校修操場,拎著滴答著水泥的鏟刀就進來了。男生殺豬一般尖叫:“不是我!不是我!是別人推他的!”第二天我包著頭上學,那個男生也包著頭。
比流血更可怕的是沒有朋友。為了得到同齡人的認同,孩子可以做任何事。我想著法兒討好大家。
我的語文和數學考試成績都是第一,但是唱歌跑調、跳舞找不到節奏、體育成績倒數,文體委員總是使勁地揪我的辮子,說:“你真笨,你真笨!”但我仍想和她做朋友。
我用美工刀割掉了自己的小辮子,對媽媽說,每天梳頭太麻煩了。媽媽說,好,女孩子就應該把心思放在學習上。媽媽修理了我的短發,把我的劉海剪得短短的,像狗啃過一樣。于是文體委員給我取了一個外號“馬桶蓋”。
三年級后,可能長大了一些,聽話的我也得到了老師的喜愛。我負責一些班級工作——每天把不交作業和遲到者的名單匯報給老師,但正是這項工作讓有些同學非常討厭我。
有一天,我在鉛筆盒里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再告我的狀,你弟弟的小命難保。”當時我的心口好像被鐵錘猛敲了一下。我第一次鼓起勇氣,站在班主任面前。交紙條的時候,我的手一直在發抖。放學前,老師讓我站起來念了這張紙條。老師向全班同學說:“敢寫還不敢留名字,能干啊,竟然還學黑社會威脅人!”
我注意到一個男生抖得像個電動篩子。我突然覺得他很可憐,就在那一瞬間,我意識到原來欺負別人的人也是可憐、膽怯的。
這件事后,我開朗了許多,我不再做“膽小鬼”,也不去故意討好別人,反而意外地交到了朋友。
燕子是插班生,她比我大兩歲,體育成績特別好,但考試、背書總是倒數。老師要我幫助她,我會花一上午時間陪她背書。她不能一次背下全文,我就讓她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背。她也會帶我去運動。800米測試,燕子對我說:“你看著我的后背,跟著我跑。”她原本可以跑第一的,但特意放慢了腳步。我盯著她的后背竭盡全力地奔跑。那次她沒有得第一,而我不再是最后一名了。
有一天,她也剪了跟我一樣的發型。我說:“你也是‘馬桶蓋’!”她說:“是啊,我覺得很好看。”
10歲那年,我第一次交到了朋友。
(歸雁生摘自《家教世界·創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