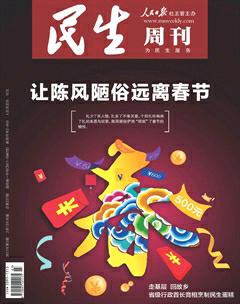河北衡水“造”園記
“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植物園是必備的一個條件,所以領導很著急。”
剛剛過去的春節假期,45歲的司立軍過得并不輕松。身為衡水市桃城區彭杜村鄉黨委委員,“我大年三十、正月初三都在單位,因為吳杜村。”“做夢還在做吳杜工作呢。”
司立軍所說的吳杜村是彭杜村鄉下轄的42個行政村之一,司立軍是包村干部。2016年,由于衡水市政府計劃在該村2000余畝耕地上建造植物園,這個有450余戶人家的村莊便開始躁動起來。
在衡水市植物園的建造鏈條里,彭杜村鄉政府僅負責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規勸村民在土地流轉合同上簽字,把耕地騰出來搞建設。“鄉鎮工作的壓力難以想象,受各方面制約。”看似不復雜的工作,卻讓司立軍感到頭疼。但他告訴《民生周刊》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做好。”
今年春節前夕,整個吳杜村未簽土地流轉協議的村民有數十戶之多,如今,僅剩10戶村民。
村民吳長有(化名)在臘月二十八那天在土地流轉合同上簽字。在此之前,由于不想將自己的耕地流轉,吳長有等多位村民曾在植物園平整土地過程中進行阻攔,甚至將施工方的一輛小汽車掀翻,吳長有等人也因此被拘留。
拘留期間,“區里和市里讓簽字(簽訂土地流轉合同)放人,不簽不放人。”吳長有家屬告訴記者,土地流轉應為村民的自愿行為,政府不應強制。他們認為這次流轉行為并不合法,政府涉嫌以租代征,既違反了國家政策,又會使耕地遭到破壞,因此他們也一度選擇不簽字,不退讓。
“但是為了過個團圓年,我們只好簽字將人保出來。”吳長有家屬說,“胳膊擰不過大腿,吳長有還在取保候審階段,我們以后不會再擋著他們施工了。”盡管如此,吳長有等村民依舊沒鬧明白,政府建設植物園為何不合法征用土地而是流轉農民的耕地?農民自己的土地又為什么自己不能做主?
吳杜村的土地流轉
2016年三四月份,建設衡水市植物園的消息傳進了吳杜村。
村民們陸續得知,植物園地址選定在桃城區彭杜村鄉等兩個鄉鎮,項目建設涉及4個村莊的土地,絕大部分集中在吳杜村。彭杜村鄉黨委委員司立軍和桃城區住建局副局長許吉震認為“離衡水湖近”是植物園選址的主要考量因素。
村民吳上飛(化名)此前聽說過幾公里外的北田、大趙常等村莊因為耕地被第二屆河北省園博會項目征用,村民每畝地得到了近20萬元的征地補償款,所以建設植物園的消息讓吳上飛等村民很興奮,也很期待。
然而,隨著植物園項目正式進駐吳杜村,項目占用土地的方式卻讓吳上飛高興不起來。那天村干部用村里的喇叭通知村民前往村委會,“說是有事相告,去了以后被告知為了植物園建設,村委會要和村民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吳上飛當時就開始思考為何要用流轉的方式用地,而不是他所期待的“一次性征用”。數月過去,這個問題他依然沒搞清楚。
在村民提供的《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合同書》上,記者看到“經甲乙雙方自愿協商,乙方(村民)同意將承包地由甲方(吳杜村委會)統一流轉用于市植物園建設,特簽訂本合同”。“既然合同上寫的是‘自愿協商,我當然可以選擇不流轉土地。”吳上飛說。
合同里還寫明流轉費用是每畝地每年2000元,每三年支付費用,流轉期限至2029年。吳上飛向記者坦言,單純從土地流轉角度看,2000元每畝的流轉費用并不算低,“種莊稼的話每年每畝地也就收入1000多元錢。”可盡管如此,吳上飛還是不打算將土地流轉出去。
除了無法得到理想中的一次性征地補償款,讓吳上飛等村民采取觀望、反對態度的原因還有“村集體的經濟狀況我們最清楚,和村委會簽合同無法保證今后的流轉費用能按時支付,被破壞的土地也無法繼續耕種”。
流轉系因為征地指標受限
正是吳上飛等人的“不合作”態度,使得原本計劃在2016年五一期間開工,今年竣工的衡水市植物園建設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尷尬局面。
對于部分村民的顧慮,甚至是反對,司立軍反省“還是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沒做到位”。為了加快土地流轉進度,根據吳杜村實際情況,經濱湖新區管委會、彭杜村鄉人民政府研究決定對衡水市植物園土地流轉有關事項做了補充說明,大意為土地流轉費由三年支付改為一次性支付。
至于農民的耕地是否會因建設行為而遭到破壞的問題,桃城區住建局副局長許吉震告訴記者,“公園本身以種植花草樹木為主,假定公園今后失去了意義,再恢復耕種也沒什么問題。”
可是,在衡水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衡水市植物園建設項目進行的批復中明確說明,項目建設內容包括建設植物專類園、花房藝術中心、展覽溫室、濱水植物科普館、植物研究中心以及配套基礎設施,包括大門、小橋、木棧道、景觀購置物、噴泉、園區道路、廣場、廁所。
既然要修建道路和建筑,衡水市植物園在經過了立項、規劃選址等程序之后為何不繼續開展土地征用行為?
司立軍和許吉震都表示植物園的土地流轉及建設工作都是按照衡水市政府的要求執行的。“要說征用的話,估計市里的用地指標也挺緊張,所以考慮到這點,就用流轉的形式慢慢消化。如果村民也有這個意愿,就把公園先建起來。”許吉震認為整個吳杜村僅有少數村民不同意流轉,“提了很多不現實的要求。”
負責土地流轉工作的司立軍也告訴記者,“衡水市植物園是市重點項目,屬于民心工程,土地流轉是市里制定的方案,鄉鎮沒有權力改變。”司立軍說植物園參照了其他項目的用地模式,“第二屆河北省園博會是省里的項目,6年前就開始流轉土地,2016年有了征地指標才辦理征地程序。而植物園未來也是這樣進行,等市里土地指標夠了就開始征地。這些事村民都知道。”
衡水的創城壓力
既然沒有用地指標,項目為何還要強行落地?
2017年1月20日,在衡水市桃城區政府的一間會議室里,區住建局副局長許吉震告訴記者,“建造衡水市植物園的目的,是衡水市領導想著盡早創建國家級園林城市。因為河北省除了衡水,其他地級市都是園林城市,所以領導壓力很大。”
一段時間以來,衡水市的整體經濟常年徘徊在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后三位。一位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直言:“衡水市一無資源、二無政策,最著名的教育也無法變現。”衡水的經濟到底該如何發展一直在考驗著當地的執政者。
在衡水市一些領導看來,創建國家園林城市似乎為該市加快經濟社會和中心城市發展、縮小與先進城市差距提供了機遇。
據了解,國家園林城市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園林城市標準》評選出的分布均衡、結構合理、功能完善、景觀優美,人居生態環境清新舒適、安全宜人的城市,是國內重要的城市品牌之一。
如果有了這個品牌,或許將會增加衡水市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品位、增強城市凝聚力和吸引力,從而聚集更多的有利于衡水發展的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推動衡水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而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植物園是必備的一個條件,所以領導很著急。”許吉震說。
2016年2月17日下午,衡水市市長辦公會上議定了植物園的相關事項。會議指出,“建設植物園是市委、市政府為改善衡水市生態環境、完善城市功能、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決定實施的一項重大城市基礎設施工程,規劃選址已經市規委會研究確定,各級部門要統一思想、提高意識,結合創建國家園林城市,加快推進植物園建設工作。”
關于建設植物園的重要性,在一份項目簡介上也有相關描述,“植物園項目的建設符合國家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符合衡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的要求,符合衡水市創建國家級園林城市的總體目標的要求,加快了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的步伐。”
蹊蹺的土地流轉金
按照彭杜村鄉黨委委員司立軍和桃城區住建局副局長許吉震的分析,衡水市植物園用地之所以選擇土地流轉,除了用地指標緊張,也是出于政府財力緊張的考慮。在植物園的立項批復中明確項目估算投資6億元,由桃城區財政投入。
“為了解決建設資金問題,市政府決定植物園采用PPP模式。”許吉震告訴記者,目前項目的投資人經過招標程序選出一家名為東方園林的公司,“共6個億的投資,政府出30%建設資金,剩余的走社會資本。”
盡管政府財力緊張,但是流轉農民土地的款項已經到位。司立軍估算如今已經撥付的流轉金已逾2000萬元。“錢由桃城區財政局撥到區住建局,再由區住建局發到鄉里,最后由鄉政府直接發給村戶。”
一位研究農村土地的人士表示,“從未聽說政府為項目出資流轉土地的事情。按理說土地流轉金不在建設資金范圍內,所以土地流轉金是以何名目進行的財政預算就是一個問題。”
對此,桃城區財政局副局長趙文藝告訴記者,“植物園是市里的項目交給桃城區運作,2016年區財政局收到市里撥的5000萬元,并已分兩次撥給區住建局3500萬元,撥款名義為地上物補償和土地流轉。這錢是上面給的資金,不需要區本級財政做預算。以什么名義收,就以什么名義撥。”
關于衡水市植物園土地流轉和土地流轉金的預算及使用等問題,桃城區各受訪單位都表示是按市里的要求辦事。是否果真如此,這些問題或許還需要衡水市政府來回答。
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位于衡水市寶云寺附近的寶云公園也和植物園采取相同的用地模式,目前該項目也處于土地流轉階段,“有些村民不同意,所以公園一直未建起來。”寶云寺附近的一家小超市老板說。
前文提到的市長工作會上,市領導提出要充分體現“植物園是公園中的精品”這一理念和指導思想,力爭把衡水植物園打造成“冀中南區域最幸福的植物園”。而如今,該項目由于用地問題仍未正式開工建設。
不知在做通了吳杜村村民土地流轉工作后,在這片土地上是否真的會給村民帶來幸福?
關于衡水市在爭創國家園林城市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本刊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