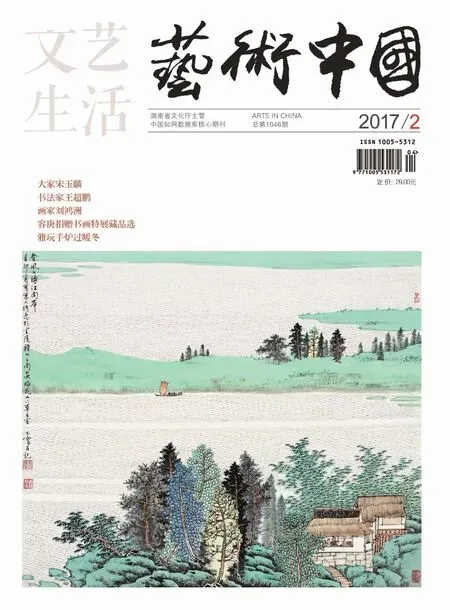小墨盒與大世界
——兼談中國人認知世界的觀念變遷
◆汪霍山(重慶)
小墨盒與大世界
——兼談中國人認知世界的觀念變遷
◆汪霍山(重慶)

在我收藏的銅墨盒中,有兩方盒面上刻有世界地圖。其中一方僅刻有中國所在的東半球,而另一方則有東、西半球全圖。這兩方墨盒上雖未留下年款,但從形制、銅質及譯文習慣看,應均出于晚清。晚清墨盒上刻有世界地圖,從一個側面反映著近代中國人“從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的世界觀的變遷。
中國人傳統的世界觀不僅認為,中國在地理上處于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認為中華文明也是世界上最高級的、普世性的文明。“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換言之,就是以華夷眼光看待世界,華夷之辨呈現的諸夏列邦和鄰國之間,以文化、文明發展的程度為依據的“天下”秩序。南蠻、東夷、西戎、北狄,都暗含“中國”之中心論的心態。所以到16世紀,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系基本上是以“宗主國對番邦”為架構的,以此形成“懷柔對朝貢”的外交政策主調,確實有一種“胸懷天下”的情懷,充滿“文化自信”。
大約在中國的明代,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和環球航行,西方人逐漸形成了完態的近代世界觀。十六世紀中葉,隨著耶穌會傳教士和貿易商人來華,世界地理知識作為西學的一部分傳入中國。最具代表意義的是1584年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制作并印引了《山海輿地全圖》,第一次將近代西方地理知識和世界地圖完整介紹給中國人。其后又有艾儒略譯的中文版《職方外紀》,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等等。這些知識都是當時中國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在當時確實也引起不小的轟動,以李之藻、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對這些新知識表現出很大興趣與熱情。僅在1584-1608年間,就在中國出現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十二種版本。可以說這時候就有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界被打開了,他們率先打破“中國中心論”的世界觀,李之藻慨嘆:“地如此其人也,而其存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三百年間,中國人對世界觀的變革,也僅限于少數知識精英。特別是康熙禁教以后,西方的新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很少,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隔絕仍很嚴重。世界地圖在明清時期的傳播并沒成為中國人常識觀念的一部分,中國人不愿意接受西方傳來世界地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化心態的認識障礙,一方面與異域的交往和對世界的的了解不斷擴展,同時卻固守“華夏中心”的觀念,認為自己不僅在詩書禮儀方面,而且在地理方位上也應屬地球(“天下”)之中心。
真正讓中國人震動并徹底改變中華世界觀的力量,最終是西洋人的堅船利炮。當鴉片戰爭爆發,東西兩個世界首次在軍事上遭遇時,身處前沿的林則徐描述道:“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英國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中國閉關自守,與外面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從此被打破了。此時,士大夫中的開明志士對探求的外部世界表現出極大興趣和急迫感,發出了“開眼看世界”的疾呼。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近代出現了第一批介紹和研究世界地理以及歷史文化的著作,真正揭開了近代中國人了解世界、學習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國人在慢慢接受世界地圖的同時,也漸漸意識到西方人并非古之夷狄,開始接受并承認與中華文明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文明——西方文明。而其后幾十年里,中西地理坐標和精神坐標都發生了倒轉,昔日的夷狄如今卻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曾經處在天下中心的傳統中華文明,反而在民族國家并立的新世界里被排斥在四方野蠻之地。
馬克思曾經說過:“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在相當長的歷史中,中華文明都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然而,曾經發達不代表永遠發達,歷史的輝煌不能掩蓋中國近代的恥辱。當我們穿過歷史嵐靄回顧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變化時,我們所感悟到的,除了從“天下”到“世界”的觀念變遷外,不是也能聽到當今時代發展的鏗鏘步伐嗎?
再回到銅墨盒。銅墨盒是盛裝墨汁之器,最早出現在清嘉慶道光年間,盛行于光緒和民國時期。一方詩書畫藝術與鐫刻工藝俱佳的墨盒,是當時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追捧和尋覓的寵珍。銅墨盒刻畫的題材,大多為有文人情趣的詩書畫,同時廣泛地涉及交誼、饋贈、獎勵、紀事、紀念、銘志等諸多方面。晚清墨盒上出現世界地圖,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方地理知識對中華傳統世界觀的沖擊,映射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探求與愿望。有意思的是,這方刻有東、西半球地圖并標有“夢公自鑄”的墨盒,藏友中竟發現有內容一模一樣、但刻工略有區別的另一方。我推斷,很可能是這位“夢公”當年訂制了一批送人。可見傳播新地理知識與文明,已成為當年知識分子中流傳的一種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