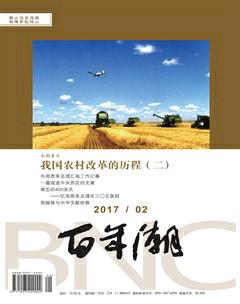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時的決策調整
王中新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苦諫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聯共抗日無望的情況下,將蔣介石及其隨行大批軍政要員扣押,此即聞名中外的西安事變。因為事變來得突然,加之詳情不清,中共中央最初只能憑借以往的政治經驗和對國際國內形勢的一般了解來判定應變決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信息紛至沓來,事件實質逐漸清晰,中共中央隨即在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基礎上對處理事變的方案進行了靈活及時的調整。
一
西安事變發生的12日清晨,張學良就致電中共中央,通報扣壓蔣介石有關情況并征詢“有何高見”。由于西安事變的發生對于中共中央來說很是突然,加之張、楊兩將軍要求速復“高見”,中共中央必須盡快做出明確表態,拿出解決方案,時間十分緊迫。
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一次會議,討論應對策略。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的性質與兩廣事變不同,是抗日的、革命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的背景,完全站在反對“剿共”的立場,對我們的態度是友好的,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蔣控制的局面,這對爭取蔣的內部和資產階級是有利的。為此,他提出在政治上維護張、楊,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影響全國。但是他同時也提出要在人民面前揭露蔣介石的罪惡,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這表明毛澤東這時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借西安事變來推動全國形成以西安為中心的抗戰局面。
周恩來在會上分析了國內外各種勢力可能對事變出現的種種反應及其錯綜復雜的關系,認為事變爆發后,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變,在沿海地區增兵。這樣一來,就會加劇英美與日本的矛盾,英美將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間派,蘇聯則會在英美之后表態支持我們。在分析的基礎上,他提出:中央要圍繞防止日本變南京為傀儡政權這一中心而制定對策。我們在政治上不要與南京對立;要穩定及爭取黃埔系、CC系、元老派、歐美派,推動這些派別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就是要爭取林森、孫科、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深入發動群眾運動,鞏固西北“三位一體”的聯合;還要在抗日援綏的旗幟下聯合閻錫山、劉湘和西南桂系,以造成對華東的包圍。鑒于中央軍已逼近潼關,周恩來提出:在軍事上我們要準備作戰,但在政治上不與南京政府對立。周恩來的發言得到張聞天、博古的響應。張聞天說,我們要盡力鞏固自己的力量,爭取時間,把西安、蘭州控制在自己手中;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分化與孤立, 不采取與南京政府對立方針,要發動群眾緊緊威逼南京。博古發言也贊同周恩來的觀點,提出在政權形式上,不要采取與南京對立的方式。周恩來等人的提議得到會議的認同,決定在政治上不與南京對立,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權,“不把抗日與反蔣并列”。
但會議在如何處置蔣介石問題上并未形成一致意見。關于這一點從隨后中共中央致國民黨電文就可以明確看出。1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率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電文中,仍要求南京政府“罷免蔣氏,交國人裁判”。從字面上看,“國人”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不僅包括工人、農民和紅軍,也包括大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統治代表,比較“交人民公審”要后退了一步。但它的實質是要將蔣介石排除在外,蔣的命運就是等待“審判”。
上述事實表明,在事變之初即12日至17日前,我黨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以為張楊抗日救國的義舉,必獲廣泛而普遍的支持。不僅廣大民眾會伸出援助之手,地方實力派將紛紛響應,甚至連南京政府大部分也會拋棄蔣介石,轉而贊成事變并轉移到西安方面來。基于判斷,中共為解決西安事變設想了以西安為抗日中心來領導全國的方案。為了實現上述方案,中共制定了對有關各方的具體政策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力支持張、楊。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北方局及上海和西安等地的黨組織,動員人民群眾起來支持張、楊。13日,中共中央即決定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大計。同時,在軍事上給張、楊以有力援助,即以紅軍一部鉗制在寧夏、陜北一帶的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曾萬鐘等部,確保張、楊后方安全,紅軍主力則迅速南下,靠攏張、楊,“壯其膽而振其氣”,協助張、楊防御南京軍隊進攻西安。
二是爭取地方實力派支持張、楊。中共中央在14日致北方局的電報中說:“必須多方面的活動駐華北名人及地方實力派,特別是閻、傅起來響應張、楊的抗日主張。”同時,毛澤東等致電張、楊,建議“極力爭取閻錫山先生及全國其他愛國將領加入,推閻錫山先生為全國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16 日,毛澤東致電閻錫山,請其出面調停寧陜雙方,實則想爭取閻支持張、楊。
三是爭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數轉到西安方面來。周恩來為此提出的“在政治上不與南京對立”的重要策略,獲得中共大多數領導人贊同,并始終為我黨所遵循。為爭取南京政府,中共中央在許多具體做法上煞費苦心。如13日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均不主張在西安建立名義上的政府,并分別提出在西安建立抗日援綏委員會和抗日救國會作為全國抗日的領導機構,張聞天則提出要爭取南京正統,其用意都在于避免與南京政府對立。
四是“罷蔣”“審蔣”。必須指出,中共中央的除蔣方針,主要不是基于感情報復,而是要試圖消除蔣介石的政治影響,以促成全國統一抗戰局面。通過向全國揭露蔣介石對外妥協賣國、對內鎮壓人民的罪行來號召全國民眾起來支持張、楊,推動地方實力派積極響應張、楊,促使南京政府失去重心,加劇分化并轉移到西安方面來,以利于國防政府的組建及以后全國抗日的進行。然而,以上方案是建立在對形勢樂觀估計之上的方案,事實證明是難以實現的。
二
周恩來17日到西安后,中共中央開始比較廣泛而全面地了解到國內外各方動態,從而及時地對有關決策尤其是對蔣介石的態度和處置辦法,做出相應的調整。
17日下午,周恩來乘飛機抵達西安,當晚即與張學良會見并進行深入的長談。從中,周恩來不僅獲知蔣介石被扣后各方的反應和動態,也清楚了張學良本人的態度。張說,據他個人看,現在逼蔣抗日最有可能。他表示,只要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該放蔣,并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因此,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并中央,提議:“為緩和蔣系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面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應當指出,周的提議主要是基于策略考慮,即以蔣之安全為籌碼,阻止或延緩南京方面討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同時分化南京政府,其除蔣方針并未真正改變。
接電后,中共中央則進一步把周恩來的策略考慮轉化為實質的主張,于18 日通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呼吁和平解決事變。通電指出:“貴黨欲救援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不(所)能奏效,實屬顯然”,“即對于救援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通電還建議國民黨立即實行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等五項具體措施。通電最后申明:“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當不成問題……”顯然,中共此時已把對待和處置蔣介石的問題與事變的和平解決聯系起來,并由除蔣轉為保蔣安全了。
18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并中央,報告了南京政府內部的爭斗和地方實力派的反應,以及蔣介石態度有所好轉,從而使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有關各方的情況。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并向南京政府和西安張、楊方面發出通電,明確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推動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形成的方針。同時,自19日通電起,中共作為事變調停者的姿態愈益凸現,并進一步將和平解決的方針化為新的具體方案。如中共19日通電,已不再過多譴責和批判蔣介石的錯誤政策,只是概括提及“南京的‘安內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續”,更多的是強調西安與南京間的共同點,謂“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南京諸公,步驟較緩”,除了親日派外,“亦非毫無愛國者”。該電強調:“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通電還主張由南京召集和平會議,會議地址選在南京。毫無疑問,中共已放棄以西安為抗日中心來領導全國的方案,轉而在團結抗日的前提下,承認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至于對蔣介石的處置,中共盡管未明確表態,但從改稱蔣介石為“先生”和“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基本綱領來看,釋蔣的結論已呼之欲出。
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明確提出中共的和談和釋蔣方案,在團結抗日的前提下,更加明確地承認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24日,中共、西安與南京三方代表談判時,周恩來說,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并表示除蔣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合適的人。當晚,周恩來見蔣介石時,再次表示:“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這樣,西安事變發生六天之后,為了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形成,中共中央在團結抗日的前提下,由主張“審蔣”變為“保蔣安全”以至主張“釋蔣”,繼而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當然,這種承認是以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讓步為條件的,也就是說,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必須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共則現實地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
三
中共中央之所以對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作上述的調整和轉變,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在于中共對當時的形勢有了更為現實、更為客觀的認識,特別是周恩來到西安后,了解到真實情況并反饋回中共中央,為中共中央合理地調整決策提供了必不可缺的依據:
第一,蔣介石被扣,在客觀上造成了西安與南京的敵對局面。南京政府16日已下令“討伐”張學良,并派飛機轟炸華縣、渭南等地;17日楊虎城部主力之一馮欽哉師動搖,中央軍已進占潼關,大戰迫在眉睫;其時,日本和國內一些報刊以及西安“雷電社”電臺對西北被“赤化”的報道和宣傳,正為南京“討伐”西安派推波助瀾。此時,中共中央也意識到事變本身已造成南京與西安間的嚴重對立,甚至有爆發大規模內戰的危險。毛澤東在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因為這一發動采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于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因此,這一發動又妨礙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
第二,相當多的地方實力派明確譴責張、楊,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討伐”西安以營救蔣介石。如湖南省主席何健13日致電何應欽說:“健愿率三湘健兒,撲殺國賊,如何行止,惟中央之命是從。”其他如廣東黃慕松、寧夏馬鴻逵、云南龍云等也持相同立場。就連與中共和張、楊有密切聯系而被寄予厚望的地方實力派,也基本上持觀望、游移、同情、中立的態度,并沒有明確支持和響應張、楊。閻錫山于14日復電張學良,提出一連串疑問,究竟是責備,還是提醒,讓人捉摸不透。李宗仁、白崇禧等16日通電全國,主張政治解決西安事變,一致對外,反對內戰。從總體上看,地方實力派基本上是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領導地位的。
第三,除西安地區和中共蘇區外,全國各階層的大部分民眾和社會輿論雖然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但卻不同程度地譴責了西安事變,要求釋放蔣介石。14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蔣夢麟等,上海商界名流杜月笙、王曉籟,以及上海商會、上海市173個同業公會都致電張學良,要求釋放蔣介石。15日,由上海《申報》牽頭,全國200余家新聞媒體機構聯名發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要求張、楊即日恢復蔣介石自由,安全護送其出境。
第四,親日派的動向異常,南京政府可能變為日本傀儡。13日,當時被中共視為親日派的何應欽當上了南京的“討逆軍”總司令,手握調動和指揮軍隊的大權。不過,中共此時雖然對親日派甚為警惕,但認為何應欽意在救蔣,而蔣尚在西安,估計何對進攻西安不能不有所顧忌。18日,周恩來向中央報告了親日派的動向:“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應欽、汪精衛)……汪將回國。”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新的信息,認為親日派勾結日本,有“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企圖奪取蔣系中派,造成大內亂”。在中共看來,如果何的內戰陰謀得逞,勢必控制南京政府,并建立親日政權。鑒于親日派的動向和時局的極端危險性,中共不能不使其決策向有利于團結抗日的方向調整和轉變。
第五,蔣本人有了抗日的愿望和要求,加之蔣在國民黨和軍隊還有較大的威信,當時也只有蔣才能左右國民黨內部的復雜派系。蔣介石被捉之初,態度極為對立,立場十分僵硬,動輒訓斥張楊,拒不與張楊商談抗日問題。然而,蔣在被囚的現實面前,“并沒有一直頑固下去,而是逐漸省悟”。14日,端納飛陜見蔣,蔣的態度稍有好轉。17日,蔣同意張學良和蔣百里所請,派蔣鼎文持其手令回寧,暫時制止了南京的討伐行動。18日,周恩來向中央電告蔣的變化,謂“蔣開始態度強硬,現轉取調和,企圖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和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中共中央從這些信息中認識到,蔣仍有贊成團結抗日的可能。此后,蔣的態度繼續變化,同意和平談判并作出口頭承諾,中共中央從團結抗日大局出發,就由“保蔣安全”發展為“釋蔣”“擁蔣”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自然要強調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其基本方案也只能是在團結抗日的前提下,現實地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化解南京與西安間的對立,避免爆發大規模的內戰,并進而促成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形成。
實踐證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中,隨著事態進程不斷據實調整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確、堅定果決的,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進抗日統一戰線在全國范圍內的形成和抗日高潮的到來,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編輯 葉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