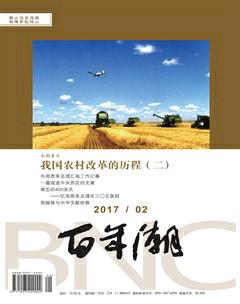郭沫若與魯迅(外二則)
魯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的風云人物。他們生前,也曾有過相交、相見的愿望,可惜卻未謀一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斗爭。
1928年初,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造社的成員寫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論戰中,魯迅與郭沫若針鋒相對。郭沫若的筆調刻薄,對魯迅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到了1932年8月,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受到不少人的贊同。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上海出現了萬人空巷的悼念活動,包括那些曾經和郭沫若一起反魯迅的創造社的成員,也被魯迅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紛紛舉行哀悼。正在日本的郭沫若連夜寫了《民族的杰作——悼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兩篇悼文中都對魯迅以高度的評價,表達了他對魯迅的崇敬之情。
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題寫了一副對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郭沫若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并且還一個勁兒地呼喊:“大哉魯迅!魯迅之前未有魯迅,魯迅之后無數魯迅。”
1937年,郭沫若由日本回國,他先后寫了三首悼魯迅的詩,成為擁護魯迅的主將。
(摘自《民國那些年(1911—1924)你所不知道的秘史逸聞》,團結出版社2015年版)
黨中央進入北平的第一個駐地——香山
位于北平西郊的香山,林木繁茂,地理位置隱秘,1920年,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在此開辦香山慈幼院,用來收養孤兒,所以留有3000多間房屋。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進駐這里。熊希齡建立香山慈幼院時,還修建了一座別墅,因為有兩股清泉從山石中潺潺流下,所以為它取名“雙清別墅”。毛澤東在雙清別墅度過了在北平的第一個夜晚。從雙清別墅西側北門出去,有一條小路通向“來青軒”,這里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的住所,劉少奇一家住東屋,朱德和任弼時住北房,由任弼時的住房往西向上走幾步,就是周恩來的住所。來青軒的東北方向,也就是現在香山飯店的所在地,中央政策研究室、新華社總編輯部、中央軍委作戰第一局設在這里。再往北,是“多云亭”,中央宣傳部的所在地。多云亭的東北方是香山慈幼院,是中辦的機要處。慈幼院西側的昭廟是中辦的秘書處。最北端碧云寺是馬列學院。為了防止敵機空襲,還在香山制高點“鬼見愁”布設了高射炮陣地。毛澤東等五大書記進駐香山后,這里就成了中共中央指揮所,保密工作更加嚴密,對外稱“勞動大學”,還有一些青年到此來報考這所大學,弄得警衛人員左右為難。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到了中南海,開始在香山、中南海兩處辦公。9月中旬,毛澤東正式遷居中南海,“勞動大學”也就完成了它的特殊使命。
(摘編《絕密檔案背后的傳奇(一)》,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張愛萍領導整頓七機部230廠
1975年,剛剛恢復工作、被任命為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到七機部所屬的230廠蹲點。230廠是開發研制陀螺儀的單位,控制導彈平衡最核心的設備出自于它。然而此時,它卻成了七機部“卡脖子”的環節。地下室原本應該是全封閉、恒濕、恒溫無塵車間,結果一下去,竟矗立著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張愛萍諷刺說: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鐘乳石長到工廠里來了!工人們說他們是“8923部隊”,就是上午八九點上班,下午兩三點下班;以后又改叫“8200部隊”,干脆上午8點、下午2點來,點個卯就走……
面對此情此景,張愛萍旗幟鮮明:一是發動群眾,批倒派性;二是組織解決,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對靠造反起家、專搞派性的造反派頭頭,堅決解除他們的職務。在七機部兩個月,張愛萍共講了52次話,去掉8個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個新講話。而且,他講話從來不用稿子,“開始我們按慣例給首長準備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說,你們照著念不就行了,還讓我講什么!”嚇得我們都不知說什么好。他從兜里拿出一張臺歷紙,一講就是兩個小時”。他下到車間,經常連一碗水都沒有,在臺上講演時,下面工人就用大瓷碗端水給他喝。他很豪爽,一飲而盡,下面的人就給他鼓掌。開始,大家還在遠遠地觀望,后來,一傳十、十傳百,他一來,大家就搶著擠進去聽。工人們給他端凳子,讓他坐著說,他反倒站在凳子上講。大會、小會,他走到哪兒,人們跟到哪兒。他的紅旗車一到,群眾就圍上來遞申訴信。他也沒有警衛員,司機老安幫他代收這些信。他嚴格地要求干部:“發生了問題找誰?找領導!”“車間里沒有開水喝,誰去打?車間主任去打!……拿桶打!”他溫和地引導群眾:“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號。聽其言,觀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
(摘編《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