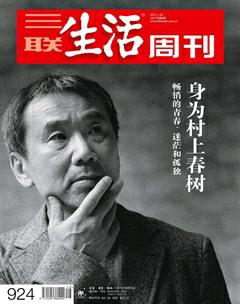2017柏林,開幕片《姜戈》和藝術家的政治
陳憑軒
“二戰”和大屠殺一向是柏林電影節偏愛的話題,可能是受德國社會不斷反思“二戰”的大環境影響,又或許是柏林相對于其他電影節政治性較強的原因。2月9日開幕的2017年柏林電影節,開幕片《姜戈》(Django)仍以“二戰”和種族問題為背景,不過是從我們最熟悉的猶太人大屠殺轉向了吉卜賽人的遭遇。這個傳統上居無定所的民族因其獨特的生活習慣和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在西方歷史上素來受到歧視。“二戰”期間重視“血統純潔性”的納粹對他們也進行了系統性的謀殺,但因居住習慣、人口數量、缺乏話語和權力資源等原因,他們的故事往往不為人知。
影片講述法國吉卜賽裔爵士樂手姜戈·萊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二戰”中與德軍和法國抵抗組織的糾葛。萊因哈特是吉卜賽爵士(法文jazz manouche,英文又稱swing,即搖擺爵士)的創始人,“二戰”期間他正值聲名的全盛期,在巴黎的演出場場爆滿。占領軍當局安排他到德國巡演遭到拒絕,姜戈處境危險,在地下抵抗組織的幫助下逃到萊芒湖(俗稱日內瓦湖)畔的多濃(Thonon),意欲伺機渡湖逃入瑞士境內。
早已過上優渥都市生活的姜戈一家在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又重新回到吉卜賽親戚的營地。由于德軍對湖面嚴密監控,他們偷渡的日期一再推遲。在法國抵抗組織的要求下,姜戈答應為當地德軍晚宴演出,自由不羈的吉卜賽爵士讓德國士兵放松了警惕,抵抗組織趁機幫助一名受傷的英國飛行員偷渡到瑞士,并對德軍鐵路進行了破壞活動。然而當德軍洗劫吉卜賽人營地的時候,法國人都別過了頭去。
世代承繼的偏見和歧視沒有因為戰爭的到來而煙消云散,沒有因為共同的敵人而得到和解。戰爭的大恐怖之下,種族的偏見仍在延續,將吉卜賽人和猶太人一樣推到了苦難的最前沿。因為吉卜賽人口主要集中在法國、南歐和東歐,法國警察在針對吉卜賽人的清洗行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為生活在納粹淫威之下的受害者,卻借機變本加厲地欺壓更弱勢的群體。
《姜戈》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面向當下現實的影片。記者會上,導演艾蒂安·科馬爾(Etienne Comar)提到,希特勒掌權和法國戰敗,為法國社會中潛伏著的歧視的暗流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出口,各種仇恨和丑惡就勢洶涌而出。這很容易被理解為是對當下特朗普美國的一種暗喻。
但這樣的政治影射并非有意為之,科馬爾說,他的初衷是要拍攝一個音樂家的傳記片,將其放在歷史的大環境下。后來他意識到,要避開政治話題是不可能的,因為“藝術(包括音樂)在黑暗中為人們帶來對自由的希望,當獨裁者攻擊自由時,他們往往也攻擊藝術”。搖擺爵士樂以它開放、多元、不屈的精神,讓獨裁者們坐立不安。片中對姜戈演出進行“審查”的德國軍官很懂音樂,向他提出了諸多要求,以使它符合政治和宣傳需要,然而這種“規訓”閹割了一個音樂類型的個性。對于吉卜賽人來說,這種音樂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生命力的象征和源泉,對于其音樂的閹割也是磨滅其民族性的一種企圖。
今天的吉卜賽人仍有一小部分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他們住在自己的營地里,仍然在經濟和社會發生問題的時候被當作替罪羊。為了讓影片更真實,《姜戈》的主創曾深入一個吉卜賽營地,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導演說,雖然到后來,他自己和阿爾及利亞裔的男主角勒達·卡代布(Reda Kateb)已經成為幾個吉卜賽家庭的座上賓,但最初的抵觸和冷漠始終提醒他們,民族之間的隔閡并未消除。
科馬爾反復強調自己拍的是一部藝術性的傳記片,也就意味著有很多歷史上的空白需要填補。影片以姜戈唯一的古典樂創作《吉卜賽兄弟安魂曲》(Requiem pour mes frères tziganes)的演奏收尾,這是姜戈在流亡期間和戰后為其死難的族人所作,樂曲大量使用宗教音樂元素,在歷史上也只演出過一次。除了開頭非常著名的管風琴部分,這部作品并沒有完整流傳下來,多半是因為吉卜賽樂人不喜書寫的習慣。于是導演邀請了澳大利亞音樂人沃倫·埃利斯(Warren Ellis)按照姜戈的風格重新作曲。埃利斯與姜戈一樣未受過學院正統音樂教育,他的音樂生涯始于搖滾,也是那一代叛逆反抗的音樂類型。但安魂曲涉及音樂在讓人向往自由和代表民族性之外的另一個功能:通過將苦難崇高化來慰藉人心。男主卡代布引用馬提尼克后殖民主義學者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的話說,彌撒的功能之一便是讓人逃避現實的痛楚,在心靈受到撫慰以后放棄抗爭,是殖民者的一種工具。所以在片中使用《吉卜賽兄弟安魂曲》的時候,科馬爾非常注意強化心靈慰藉而淡化精神麻痹:在一般宗教音樂讓人凝視圣像的時候,他把鏡頭對準了主人公姜戈本人——這是一支人向人致敬、默哀的圣樂,人站在神壇的中央,是萬物的尺度。
片中有一處細節,講述“二戰”中處于德軍占領下的巴黎,有地下放映場所可以看到英國人嘲諷納粹德國宣傳的作品。在《姜戈》里能看到的是英國電影人對德國意識形態片搞笑的重新剪輯,又配上象征反叛的搖擺爵士樂,讓極權的宣傳變得荒誕不經。導演說,他不喜歡發表政治演說,也不喜歡藝術家直接參與政治,但他同意藝術本身可以是政治的,而藝術家的觀點應該通過藝術來表達:“我們用自己的藝術、自己的作品來回答時代的問題。”
這或許也是影片能被選為柏林開幕片的原因。之前盛傳名導馬利克的《拉黛貢德》(Radegund,暫定2018)有可能是今年的開幕片,因為這是他以《細細的紅線》(The Thin Red Line,1998)獲柏林金熊獎后第一次重拾“二戰”題材,因此大家都以為是板上釘釘了。不料這位金熊、金棕櫚雙料得主并沒有來柏林,可能他是想去今年戛納的七十大壽,或者直接送類型片電影節,也可能真的是因為制作緩慢要等到明年。
《姜戈》則是艾蒂安·科馬爾的導演處女作。一部處女作被選為頂級電影節的開幕片,還是有點令人震驚。在做導演之前,科馬爾是法國影壇極為成功的制片人,他制作的影片有兩年前的戛納大熱片《我的國王》(Mon roi,2015,戛納最佳女演員獎),講述阿爾及利亞基督教僧侶困境的《人與神》(Des hommes et des dieux,2010,戛納評委會大獎),以及20世紀法國的西班牙移民故事《六樓的女人》(Les Femmes du 6e étage,2010)。他制片人生涯的巔峰無疑是2014年的《廷巴克圖》(Timbuktu),這部毛里塔尼亞影片呈現了馬里通布圖在被宗教極端分子控制后,平民的遭遇和沉默的抗爭,在戛納主競賽首映后又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還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七項法國電影愷撒獎,對于一部根本就不說法語的片子來說也是頭一遭。
或許正是這樣豐富而具有全球視野的制片人生涯,加上《姜戈》影片中的政治信息,讓柏林最終決定以它開幕。電影節主席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說,本屆柏林選片的主題是“多元”(diversity),戰爭民族、東方西方、性別性向、傳統現代,在這個特朗普掌權唯一超級大國的世界里,2017年的柏林選片是一種“抗議”(protest)。在北美頒獎季圍繞政治話題展開的同時,作為2017年歐洲電影節中第一個大頭,柏林為全世界電影藝術家定下了未來四年的基調:繼續反思、揭露、表現人類歷史上所有不寬容的思想和行為,在內容和形式上追求個性化風格和自由的表達。在多元價值受到政治威脅的黑暗時刻,藝術的明燈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