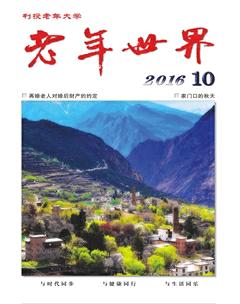長征路上走出的紅軍博士
孟蘭英
他是我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紅軍博士,他參加了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作戰,親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經歷戰役戰斗數十次,出生入死,屢建功勛……
涂通今,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醫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留學蘇聯的醫學博士,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這么多頭銜集于一身,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了。而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病房里,來訪者所面對的,是又一個奇跡。涂通今老人,這位至今還健在的紅軍長征的親歷者、見證者、幸存者,安靜地躺在病床上,歲月崢嶸,時光荏苒,102載的人生經歷在他那飽經滄桑的臉頰上留下了一道道的皺紋,從中折射出這位百歲老人數十載從軍生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品德,以及勤勉不倦、著書育人,深得同行贊許和晚輩敬重的崇高風范……
聆聽毛澤東演講,從此立志當紅軍
在紅軍歷史上,一共出現了3位博士,涂通今是目前唯一健在者。涂通今1914年出生于福建長汀縣涂坊鎮。當年,在父母的拼命支撐和同族資助下,涂通今讀了5年私塾3年高小,最后從國語講習所畢業。
1929年,當紅軍二次入閩路過長汀縣涂坊鄉時,15歲的涂通今擠進人群,那是他第一次聆聽了毛澤東的演講。涂通今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那是1929年10月,鄉親們在豐收后歡慶農歷九月的時候,毛委員路過涂坊鄉,他就住在同街的藥店里,還在群眾集會上講了話,號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用革命武裝粉碎反革命武裝。一位偉人充滿感召力、凝聚力的舉手投足、慷慨陳詞,使一個從小就背誦孫中山遺囑,天天盼著“耕者有其田”的窮孩子,深深地認同了革命的遠景。那次演講時間雖不長,但卻激起涂通今想當紅軍的愿望。
幾經努力,1932年,在任區蘇維埃代表的父親的支持下,涂通今毅然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當時,蘇區正處于反“圍剿”斗爭期間,戰斗中傷員的不斷增加使得紅軍對于醫護人員的需求凸顯,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涂通今參軍后立即被分配到福建軍區后方總醫院。入院第二天有個考試,題目是“為什么要學看護?”乍一看題,涂通今這個高小畢業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間,他想起醫院大門上的一副對聯:“為救護前方歸來的英勇將士,為培養無產階級的醫學人才”,憑著這個記憶,他把這句話一字不落地寫在答卷上。發榜時,他居然名列第一!
在做了8個月的看護工作后,涂通今被選送到位于江西興國縣茶嶺的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學習。這里是他接受正規醫學教育的起點。也就是在紅軍衛生學校的緊張學習期間,涂通今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10月涂通今考入紅軍衛生學校第二期,學員近30名。1933年,紅軍衛生學校和傅連暲的紅色醫務學校合并。1933年涂通今畢業后,任紅3師8團軍醫。從長征開始到抗日戰爭爆發,涂通今一直在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從事醫務工作。
下定決心跟紅軍走出一片新天地
從軍之初,血氣方剛的涂通今要求扛槍打仗上前線。沒想到,上級派他去醫院報到,分配他救治傷員,學習看護。他服從了組織的安排,從此走上了醫學之路,在70年的從醫生涯里,他挽救了數不清的生命,用另一種方式“戎馬一生”……
“他見過太多的生死,卻還是很難冷靜地面對死亡,那些因傷勢過重、無法救治而倒在他懷里的同伴,一直是他心里的一個坎。”涂通今的兒子涂西華感嘆道。
1934年9月30日,紅九軍團從福建長汀縣鐘屋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涂通今作為隨隊軍醫出征。出發前,聞訊趕來的家人捎來了他父母的意愿,希望長子脫下戎裝,解甲歸田。此時20歲的涂通今經過了多次反“圍剿”鏖戰后,已經下定決心要跟隨紅軍走出一片新天地。他婉拒了父母,朝著與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走去——從農民走向將軍,從私塾學童走向留蘇博士。
險象環生的長征路上,涂通今不僅要對抗敵人、保存自己,更要照料傷員。涂通今回憶說:“我們紅九軍團由羅炳輝率領,在長征中處于右后衛位置,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收容主力部隊掉隊的傷病員。遇有敵情時,紅軍常常要急行軍或強行軍,有時候一天一夜趕百多里路,體弱掉隊的很多。如果發生戰斗,還會有大批傷員下來,我們醫務人員就要舍生忘死地把傷員搶救保護下來。”
他還說:“當時的救治條件現在真是無法想象,能夠找到一塊門板搭一個手術臺就很不錯了,手術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沒有繃帶就把被子撕成條。還得有人舉著油燈照明。那時藥品和醫療器械都是無價之寶,消毒滅菌和抗感染的藥物更是極少,長征途中只能做一些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縫合、取子彈、取骨片這樣的處置和小手術,至于斷肢和內臟手術,根本就做不了。我救護過的傷員不計其數。現在看來,有不少同志由于沒有得到手術和輸血輸液的機會,本可以得救的,卻失去了生命。”
過雪山草地時,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造成的痛苦和犧牲,卻并不亞于戰斗中的傷亡。對此,涂將軍有著切膚之痛。
“再苦再累,我們醫護人員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馬虎。每日到達宿營地后,首先選擇一塊比較干燥的山坡,搭起帳篷支上爐灶,撿來干牛糞點上火,消毒醫療器材,給病人看病、換藥、發藥,包括傷病員燙腳、開飯,我們醫務人員也盡力幫他們做。有一次,我們正準備搭帳篷拾牛糞,忽然天氣驟變,雨水冰雹齊下,十幾人個個澆得像落湯雞,牛糞打濕了,火也點不著了,我們真是傷心著急啊。風雨一過,滿天星斗,我們又開始工作了。休息對我們來說有時真比吃飯還重要。”
有一次行軍恍惚,涂通今一腳踏空掉下懸崖,幸好一棵樹接住了他,才免于一死。每當憶及這段經歷,涂通今總是心潮起伏、無法平靜。良久,他總會淡淡地說:“長征之苦,使人難忘。”
紅軍博士、神外專家、知識分子典范
1949年10月1日,涂通今又一次聆聽到了毛主席的演講,那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了的時候。
每次回憶到這里,涂通今總是哽咽,說不下去,因為有數不清的戰友倒在了征途中,沒能親眼看到他們為之付出生命而換來的新中國正在世界之林冉冉升起。
1949年,涂通今任四野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四野入關后,他擔任中南軍區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組建華中醫學院,兼任院長、黨委書記。
1951年8月初,涂通今接到上級通知,要他盡快移交工作,準備赴蘇聯留學。放下電話,涂通今一陣驚喜之余又有一絲惆悵。有機會繼續深造當然是他的愿望,但這也意味著要遠赴異國他鄉另起爐灶,重新開始學生生活,這對于一個年近40歲的人來講,與其說是機會,倒不如說是一場挑戰。1951年9月,涂通今走進了莫斯科布爾科登神經外科研究所,他的任務是學習神經外科,為歸國后創建我國神經外科作準備。與涂通今同往學習的紅軍干部還有錢信忠、潘世征,他們分別學習保健組織學和普通外科。當大家得知他是參加過長征的紅軍戰士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有人還不斷呼喚著毛澤東的名字,這讓涂通今深感自豪。
開局順利,但接下來的挑戰頗具難度。語言、專業……種種難題擺在他面前,人到中年,要重新學一門語言,掌握復雜的神經外科并不容易,不僅拼體力,更要拼腦力。
涂通今在蘇聯學習期間,熟練掌握了俄語,在神經外科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1955年取得副博士學位。之后又進入了蘇聯醫學科學院特別系學習。
涂通今于1956年回國。先后任第四軍醫大學副校長、校長,總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1971年后,任解放軍總醫院代理院長,主持全院工作。
早在 1956年,涂通今就在第四軍醫大學組建了神經外科。他在臨床實踐中開展的從小腦幕上入路切除聽神經瘤、延腦三叉神經脊髓束切斷術以治療三叉神經痛、第三腦室后部腦瘤切除術等,填補了國內空白,開創了我國神經外科的新局面。
20年后,當他離開四醫大時,已是“桃李布三軍”,他創建了軍隊醫院第一個神經外科,為全軍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經外科骨干。為我國的醫學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周恩來總理曾贊揚涂通今,稱他是我們國家的紅軍博士,是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
如今的醫療條件比起長征時已不知強了多少倍。現在,涂通今的手雖然已不能再舉起手術刀,無法再繼續治病救人了,但他們那一代所開創的事業正在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