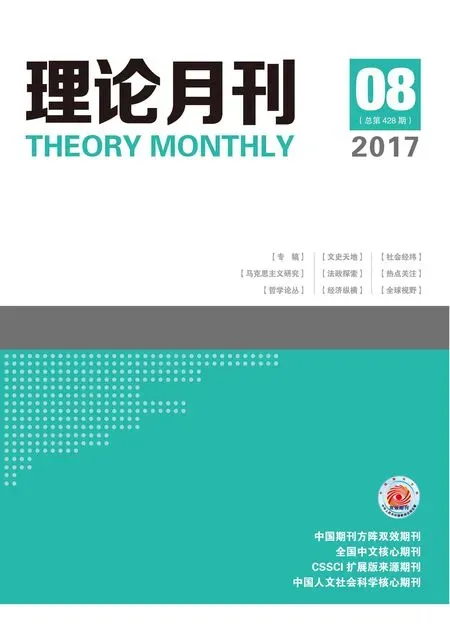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
——基于陸海屬性的視角
□劉明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
——基于陸海屬性的視角
□劉明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天津 300387)
根據陸海屬性,南亞七國分屬海島型、內陸型和陸海復合型。陸海屬性在地緣因素上影響著南亞國家的權力需求、綜合實力和地區定位,進而影響著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即認知程度、反應態度、行為深度和結構強度。相對而言,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作為海島型國家,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認知程度高、反映態度積極、行為深度觸及核心、關系結構強度牢固,參與活性要高于不丹和尼泊爾這兩個內陸型國家,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陸海復合型國家由于陸海屬性同中有異,在參與活性上也各有特點。對此,中國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南亞國家自我決策中的印度因素,二是南亞國家參與活性可能產生的雙重影響。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亞;陸海屬性;參與活性
在歷史發展的縱軸視閾下,南亞次大陸深入印度洋的地形特點與印度洋四通八達的便利條件,使得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與南亞國家通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互通往來,建立了最初的海上關系。在東西方交往中,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等南亞國家在商貿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等方面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轉、補給和樞紐功能。可以說,南亞航線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條重要支線。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在多個外交場合和重大會議中闡釋這一倡議,邀請世界各國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一道共建,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南亞地區的區位特征、南亞國家的物產文化以及中國和南亞國家源遠流長的交往歷史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從戰略布局的視角來看,南亞地區是“一帶一路”的交匯地帶,也是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點地區;從周邊外交的視角來看,南亞國家不僅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首要合作伙伴,更是首要受益對象。
毋庸置疑,無論基于歷史還是現實,南亞地區都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路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南亞國家作為獨立行為主體,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并不等同,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的角色扮演也不盡相同。究其根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南亞國家的陸海屬性并不相同。基于地緣政治概念的界定,陸海屬性的劃分主要依據陸海地緣結構,如陸海度值、陸海邊界線和鄰國屬性;陸海地理區位,如經緯定位、地形地勢和氣候條件;以及陸海文明成分。據此,南亞七國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海島型國家,包括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二類是內陸型國家,包括不丹和尼泊爾;三類是陸海復合型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南亞國家的陸海屬性存在差異,決定了各國對海權的天然需求有強弱之分,在海權的發展邏輯上有先后之別,在地區事務中的權力運用和利益獲取上也存在非對等性。南亞各國對海權的適時謀劃和戰略運用影響著國家定位和發展水平,反映其天然稟賦和地緣特征,同時又引導著該國的政策取向和戰略走向。南亞國家的陸海屬性及其內在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認知程度(是充分?是片面?)、反應態度(是積極?是消極?)、行為深度(是觸及核心?是浮于表面?)和結構強度(是牢固?是松散?),即所謂的參與活性(是高?是低?)。
1 海島型國家: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
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作為南亞熱帶島國,位于印度洋的有利位置,擁有大面積領水,多良港、多海峽,通道位置重要,豐富的海洋資源和發達的海洋經濟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保障。對于海島型國家而言,海洋的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海島型國家,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對海洋的依存度較高,對海權的需求較為強烈。特別是面對其所在的印度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深知印度洋的自然資源豐富、能源供給充足、市場份額巨大,是自然資源、能源和市場的來源地和聚集地,同時又是世界經貿往來和遠海通道安全的樞紐地帶。因此,印度洋成為兩國密切關注和戰略謀劃的地緣焦點和重點地區。
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中國同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的關系發展與海上絲綢之路有不解之緣。在古代,中國和斯里蘭卡的交往密切,到明代達到鼎盛,大量考古實物研究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活動的歷史事實[1]。中國和馬爾代夫的國家間關系可以追溯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曾兩次途經馬爾代夫,帶動了中馬友好往來和交流。長期的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使得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對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認知、文化認同及其與中國的傳統友誼較為深厚。
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積極回應并表達強烈的參與意愿。中國和斯里蘭卡共同致力于“加強海洋、經貿、基礎設施建設、防務、旅游等領域交流合作,共同推進海上絲綢之路復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2],馬爾代夫也表示支持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宣稱其外交政策向東看,希望發揮自身地緣優勢,借鑒中國的經驗發展自由貿易區[3]。
基于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較為充分的認知程度和積極的反映態度,中國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背景下的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斯里蘭卡、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總統、總理訪華,促進政治互信和經濟合作;中國投資斯里蘭卡素有“東方十字路口”之稱的科倫坡以及漢班托塔深水港,加強港口建設和互聯互通;中國和馬爾代夫合作建設馬累—機場島跨海大橋,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中國與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簽署經濟貿易合作協議,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深化經貿合作與投資;中國人民銀行和斯里蘭卡央行簽署代理投資協議,擴大金融領域合作;中國國防部長訪問斯里蘭卡,加強軍事領域合作;中國與斯里蘭卡深化在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合作,促進民心相通;中國夢攜手“馬欣達愿景”,打造命運共同體。
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兩國擁有利用海洋資源的天然性、探索海洋權力的自發性以及謀劃海洋戰略的一貫性,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其“發展需求和發展戰略高度契合”[4]。理論和實踐均表明,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行為深度觸及國家主要利益,與中國的關系結構相對牢固,可以說,兩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相對較高。
2 內陸型國家:不丹和尼泊爾
不丹和尼泊爾作為南亞地區的內陸小國,遠離海岸,地緣條件的單一性決定其生產生活和戰略重心均倚重陸地,社會發展水平有限,地區影響力甚微。
不丹夾于中印兩國之間,受喜馬拉雅山脈阻隔,多山地叢林,“孤立”和“封閉”成為不丹歷史的主色調。但是,歷史上的不丹并未因陸地文明的保守內斂而免于動亂、戰爭、入侵和殖民。上世紀60年代,不丹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有選擇性地參與南亞地區性事務[5];80年代,不丹實行“不丹化”民族政策,迫使尼泊爾族人融入不丹族文化體系,民族問題凸顯[6];90年代,不丹在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上基本實現了獨立自主[7]。
獨立后的不丹,雖然在國際舞臺上有選擇地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并未與中國、美國等世界主要大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雖然不丹在對外交往中追求獨立自主和國際合作,但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使不丹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仍然對印度有較高的依賴性。雖然擁有國際法明確規定的海洋權利,但是不丹并不急于走向海洋;國民幸福指數、民族、宗教和文化問題才是不丹國內政治的主導因素。
尼泊爾在陸海屬性的表象上與不丹大體相似。作為內陸小國,尼泊爾的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對外關系受制于地緣因素,與鄰國印度在自然稟賦、綜合國力和地區定位等諸多方面差距懸殊,同樣對印度具有較高的經濟依存度。隨著“西藏問題的復雜化、印度謀求南亞的霸權地位、美國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加強”,尼泊爾因其特殊的地緣價值開始受到關注[8]。對此,尼泊爾在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方面也作出了相應調整,與中國從友好合作升級為全面伙伴關系,與印度從特殊關系走向正常國家間關系,與美國從相互敵對走向有限接觸,除此之外,尼泊爾還在國際組織交往活動中由“重在參與”走向“積極介入”[9]。
作為中國的友好鄰邦,尼泊爾和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良好的國家間關系以及思想文化交流與合作,中尼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也成為國家間解決邊界問題的成功范例。近年來,尼泊爾在政治上表露親中姿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獲得中國長期援助,在安全領域上與中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但是,尼泊爾在對外交往層面采取均勢外交政策,在友好中立的框架內游走于中印兩國之間,甚至被印度視為遏制中國在南亞地區擴散影響力的重要支點[10]。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有尼泊爾學者和媒體表示,希望尼泊爾可以參與到“一帶一路”中來并因此獲益。然而,尼泊爾與印度的地緣關系復雜、綜合國力相差懸殊,長期在穩定國內局勢和發展經濟方面有求于印度,同時,印度也意圖對尼泊爾施加影響并借機遏制中國[11]。因此,尼泊爾雖有意參與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但鑒于上述條件局限和因素制約,其參與深度容易浮于表面,與中國的關系結構相對松散。雖然尼泊爾在海洋領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相對較低,但是,在陸地方面,“一帶一路”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給尼泊爾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合作平臺。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成果清單中,中尼兩國簽署了跨境經濟合作區合作諒解備忘錄和經濟合作協議,在政策溝通和貿易暢通方面取得了初步進展。
3 陸海復合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既擁有陸海雙重優勢,又面臨陸海雙重安全困境,無論是經濟建設與文化發展、還是長遠戰略與階段策略等行為選擇,都在不同程度上尋求和維持著陸權和海權的某種平衡。雖然同為陸海復合型國家,但由于領陸和領水范圍、陸海邊界線、地形地貌以及與鄰國關系各有特點,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在權力追求、利益分配和戰略演變等方面也同中有異。
在南亞政治格局中,印度一直居于主導地位,無論是在地緣結構、地理區位還是資源分布、文明積淀等方面,印度都是南亞地區的佼佼者。“作為南亞的頭號大國,不僅在幅員、人口、資源、軍事力量和發展水平等方面在南亞地區具有絕對優勢,而且還居于南亞的中心,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中具有主導地位,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發展和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2]通過對比中國和印度的陸海屬性發現,中印兩國雖然同為陸海復合型國家,但在地緣結構上存在著較大差異:印度半島呈楔形,直插入印度洋,而中國沿海呈弧形,受到三大島鏈的束縛和海洋劃界、島嶼爭端問題的困擾,缺乏直接面向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地緣結構特征影響著國家戰略取向。與中國防御性戰略不同,印度長期奉行進攻性戰略,近年來更是提出了旨在建立“印度主導的海洋世界”的“季節計劃”,確保和維護其從南亞次大陸到印度洋地區的主導地位始終如一。印度的涉絲計劃和通道戰略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制中國的戰略應對,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構成一定沖擊。
南亞地緣政治特征決定了印度面臨來自陸地和海洋的雙重威脅,印度作為陸海復合型國家具有先天缺陷是其面臨安全戰略困境的根本性決定因素[13]。基于上述認知,印度深知統籌陸海整體戰略的重要性,更加警惕南亞地區域外大國的介入,防止印度陷入兩難境地。加之,印度對中國崛起、中國影響力、中印關系以及中國對印認知的感知上存在著權力政治的思維定勢,極大地影響了其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客觀判斷。印度似乎并不認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意在加強貿易、促進合作,而不過是拓展空間、擠壓印度的策略罷了,甚至認為中國“別有用心”。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印兩國各自基于同類陸海屬性有著相似的權力需求和發展戰略,但在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分配上卻又是相悖的,導致印度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中難以取得觸及核心的實質性進展,參與活性并不高。
巴基斯坦是南亞地區的重要國家,地緣結構優越,擁有卡拉奇港、加西姆港和瓜達爾港等若干個戰略性港口。近年來,巴基斯坦身陷戰略困境,面臨“內憂外患”:國內呈現出“危機國家”的癥狀,對外與印度、美國等大國摩擦不斷[14]。印巴沖突的長期化和復雜化是威脅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風險因素,印巴和平進程在“和平共識、克什米爾問題、軍事、反恐和經貿領域取得積極進展”的同時,仍然受制于“印巴核因素、印度崛起以及美國反恐戰爭、美國與印巴關系等”諸多內部或外部因素[15]。“9·11”事件后,巴基斯坦積極配合美國反恐,美巴關系驟然升溫,但是,由于美巴關系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分歧難以解決,因此,美巴同盟關系基礎薄弱,反恐合作面臨危機[16]。正是緣于政治危機和恐怖主義,巴基斯坦日漸成為南亞地區安全格局的重塑者。
巴基斯坦與中國的關系具有特殊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從1996年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到2005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巴兩國的外交關系、經貿往來、文化交流和民間友好關系長期深度發展,成為睦鄰友好關系的典范。同時,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卡拉奇和拉合爾分別與中國的北京、上海、陜西西安結為意在和平友誼、共同發展的友好城市關系。中巴關系發展的歷史與實踐證明,中巴兩國和兩國人民是全天候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作為地理上中亞和我國新疆南下進入印度洋、西亞進入南亞的戰略通道,巴基斯坦有望成為該地區新的物流與港口運輸中心,從而在南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7]近年來,中國和巴基斯坦致力于共建中巴經濟走廊,打通從中國喀什到阿拉伯海的新通道。當前,在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背景下,中巴兩國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經濟貿易合作協議、項目貸款和融資合作協議,促進政策溝通、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中國投資建設瓜達爾港和卡拉奇港,設立自由貿易區,建設公路、鐵路、機場和能源管道,促進基礎設施聯通;開發卡西姆港燃煤電站、大沃風電等項目,開展海上合作對話,在港口建設、海上合作和互聯互通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中巴兩國致力于在“加強政策對話和戰略溝通,在航行安全、海軍合作、海警交流、海洋科研與救援等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為建設安全、和諧的海洋而共同努力”,中巴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也被稱之為“地區和平穩定之錨”[18]。中巴兩國基于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行為深度觸及兩國核心利益和主要利益;加之,“中國在南亞的安全戰略支點在巴基斯坦,而這個國家的對華政策是不可能受到印度左右的”[19],可以說,中巴關系穩定與印巴關系沖突、美巴關系薄弱并存,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結構相對牢固。概言之,巴基斯坦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較高。
孟加拉國海洋邊界線短,海陸度值低,多河流沖積平原,經濟欠發達,民族和宗教問題突出。從地理位置上看,孟加拉國三面被印度包圍、一面向海,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與印度差距較大,受到印度的種種制約。隨著印度的南亞政策由“英迪拉主義”轉向“古杰拉爾主義”,美國“亞太再平衡”和“新絲綢之路”戰略的實施以及“一帶一路”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推進,孟加拉國地緣戰略地位凸顯[20]。
孟加拉國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建交之后兩國關系迅速發展。當前,在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的背景下,孟加拉國與中國簽署經濟貿易合作協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深化海洋安全和能源合作。中國投資建設吉大港,投資建設從達卡站到杰索爾的帕德瑪大橋鐵路連接線項目,聯通泛亞鐵路通道,用于改善孟加拉國西部和西南部地區交通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21]。但是,與此同時,孟加拉國與印度、美國和日本等其他大國在港口、軍事、經濟和資源等方面的合作也很密切,甚至逼停中孟索納迪亞港項目。因此,只能說,孟加拉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行為可能觸及核心問題或主要利益,進而說明與中國的關系結構不夠牢固,參與活性中等。
4 南亞國家自我決策中的印度因素與參與活性的雙重影響
南亞國家的地緣特征全面、陸海屬性多元、地區定位有別、發展水平不等,對海洋的向往和對海權的追求因自身條件而異,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這是基于南亞國家的陸海屬性作出的基本判斷,也是南亞國家自我決策的過程:南亞國家根據自身陸海屬性作出符合國家利益的理性行為和合理決策,突出表現為南亞國家中的海島型國家和陸海復合型國家對印度洋海權的謀求和對海洋權益的維護。對于南亞國家而言,能否順應國情、世情作出明智的國內國際決策在很大程度上關乎其國內發展和國際交往的得失。
然而,南亞國家在自我決策的過程中,難免受到南亞地區大國印度因素的外在影響。一方面,南亞其他國家與印度的關系存在著較高程度的權力依賴,因此,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態度和行動上,南亞其他國家或多或少要考慮印度因素:作為鄰國,南亞其他國家與印度的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的依存度相對較高,主要通過加強與印度之間的雙邊合作或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實現本國的發展;作為南亞地區大國,印度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態度和表現不一,很大程度上可能導致南亞其他國家舉棋不定或者受到印度擺布。特別是印度缺席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未來印度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亞路段進程中的地位作用和角色扮演撲朔迷離。
另一方面,作為陸海復合型國家,印度在處理與南亞其他國家之間關系的過程中堅持旨在平衡的全方位外交。冷戰時期,印度強調其周邊鄰國的認同,反對他國介入南亞事務;冷戰結束后,印度積極改善與南亞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加強區域合作,穩定地區局勢;莫迪上臺后,奉行“鄰國是首要”的外交戰略,“不僅意識到與巴基斯坦進行戰略性接觸的重要性,同時重視改善與孟加拉國、尼泊爾和斯里蘭卡之間的關系,旨在為充滿活力的地區主義奠定基礎”[22]。中國、印度與南亞其他國家之間關系的親疏遠近不僅影響著南亞地區的政治生態和權力秩序,而且影響著中國和印度在南亞地區的權力維持和利益尋求,權力慣性或權力轉移將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產生防范性或者共容性等直接影響。
除此之外,還要特別注意的是,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可能產生的或積極、或消極的雙重影響。根據衡量指標,南亞國家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認知程度是充分還是片面、反應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行為深度是觸及核心還是浮于表面、結構強度是牢固還是松散,共同決定了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是高還是低。而在國家行為和國家心理層面,上述衡量指標都有可能成為南亞國家認知和判斷中國其他事務、行為或政策的因素和依據。
具體而言,參與活性高的國家對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認知充分、反應積極、觸及核心、結構牢固,這有助于深化其對中國“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認同與肯定,避免其對中國崛起產生偏見、戒心甚至離心;而參與活性低的國家,尤其是對中國缺少全面認知和理性判斷、甚至缺乏信任的國家,認同度相對較低、反應消極、浮于表面、結構松散,這很有可能加深其對中國崛起的和平性質和發展模式的錯誤判斷,對中國在權力秩序和地區格局的國際定位、角色扮演和實際影響高估或低估,以及對中國進入印度洋動因進行臆測。因此,要深化認知程度、內化積極態度、外化行為深度、提升結構強度,充分激發南亞國家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活性。
[1]姜波.從泉州到錫蘭山:明代中國與斯里蘭卡的交往[J].學術月刊,2013(7):138-145.
[2]習近平在斯里蘭卡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做同舟共濟的逐夢伙伴[N].人民日報,2014-09-17(02).
[3]ATUL ANEJA.Maldives Set To Formally Endorse Maritime Silk Route[EB/OL].The Hindu,http:// 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maldives-setto-formally-endorse-maritime-silk-route/ article6700672.ece,2014-12-17.
[4]廖萌.斯里蘭卡參與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考慮及前景[J].亞太經濟,2015(3):62-67.
[5]朱在明,等.當代不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時宏遠.試析不丹的民族問題[J].世界民族,2011(1):27-33.
[7]劉建.不丹的對外關系[J].南亞研究,2006(2):51-55.
[8]趙暢.從均勢角度看尼泊爾小國外交[J].學術探索,2011(8):33-38.
[9]徐亮.共和國時期尼泊爾外交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5.
[10]謝士法,邢紅梅.游走于中印之間:尼泊爾對外政策的基本走向[J].當代世界,2010(7):49-51.
[11]王艷芬.試析尼印《和平與友好條約》簽訂的歷史背景[J].史學月刊,2008(11):97-102.
[12]李云霞,樊祎冰.印度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中的主導地位及其影響[J].東南亞南亞研究,2013(2):52.
[13]宋德星.南亞地緣政治構造與印度的安全戰略[J].南亞研究,2004(1):20-26.
[14]杜冰.巴基斯坦的困境與前景[J].現代國際關系,2012(3):24-30.
[15]周紹雪.新時期印巴和平進程的演進與前景[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3(5):108- 112;李群英.印巴關系緩和現狀與前景[J].現代國際關系,2011(6):19-35.
[16]孫現樸.美巴反恐合作:進程、障礙及前景[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3):28- 41;楊文靜.后拉丹時代美巴關系走向探析[J].現代國際關系,2011(6):58-62.
[17]趙景芳.打造能源支點,維護中國能源安全[G]//胡思遠.中國大海洋戰略論.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69-70.
[18]中巴舉行第二輪海上合作對話[EB/OL].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 674879/wjbxw_674885/t1337847.shtml,2016-02-03.
[19]葉海林.印度南亞政策及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影響[J].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6(2):15.
[20]時宏遠,王歷榮.冷戰后印孟關系的變化[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2):114-117.
[21]中國中鐵簽約孟加拉國31億美元基建項目[N].人民日報,2016-08-09(03).
[22]拉賈·莫漢.莫迪的世界:擴大印度的勢力范圍[M].朱翠萍,楊怡爽,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11.
責任編輯 趙繼棠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8.033
D822.2
A
1004-0544(2017)08-0176-06
天津市教委社會科學重大項目(2014ZD26);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TJZZ15-004)。
劉明(1985-),女,遼寧撫順人,法學博士,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