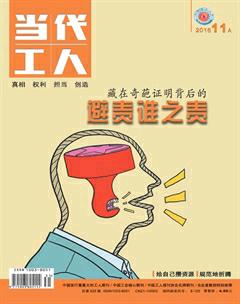聚會(huì)生病根
李憶鋒
畢業(yè)后時(shí)隔30余年的小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源于一位在美國定居的同學(xué)的回國探親之行。這位同學(xué)旅居海外10余年,在異國他鄉(xiāng)特別思念祖國,特別想念小學(xué)同學(xué)和老師。回國之前,她和國內(nèi)同學(xué)通話,主張來個(gè)小學(xué)同學(xué)大聚會(huì),這樣在她回國之時(shí),可以見見更多的同學(xué)。
人就是這么一回事,對距離遠(yuǎn)的人和事懷有更深的感情。那些依舊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同學(xué),隔三差五能碰上,母校的大門也是天天經(jīng)過,就沒什么懷念感覺。這位同學(xué),一是因?yàn)檫h(yuǎn)隔千山萬水,有著特別的思念,再是年紀(jì)大了好懷舊,自然渴望見同學(xué)。
為實(shí)現(xiàn)這位海漂同學(xué)的心愿,班里的活躍人士開始聯(lián)系全班同學(xué)。找啊找啊,通過張三找李四,通過李四找王五,以此類推,總算找到了2/3的同學(xué)。只剩下十來位打小就和同學(xué)老死不相往來的那種同學(xué),實(shí)在不好找。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在人社局工作的同學(xué),通過查找保險(xiǎn)人姓名,按照保險(xiǎn)底賬上留下的電話號去聯(lián)系同學(xué)。要說這種做法有些不妥,牽扯到暴露個(gè)人隱私,但是同學(xué)見面的熱情實(shí)在太高漲了,過激的做法可以理解。聯(lián)系班主任老師也費(fèi)周折,但還是挖地三尺把八十來歲的老師找到了。
這天下午,蔡勇的手機(jī)響了,是一個(gè)陌生號,他沒遲疑立刻接通。蔡勇在機(jī)關(guān)工作,基層人員多,有陌生電話號很正常。
聽對方說是自己的小學(xué)同學(xué),蔡勇很意外。自己小學(xué)畢業(yè)后在外地念高中、上大學(xué),和小學(xué)同學(xué)幾乎沒有聯(lián)系,怎么會(huì)有小學(xué)同學(xué)來電話。
電話是被稱作“社會(huì)活動(dòng)家”的女同學(xué)打來的,使用女生慣用的套路(也挺招人煩的做法),讓蔡勇猜自己是誰?聽語聲的親和度,知道對方應(yīng)該是和自己熟絡(luò)的人,但是確實(shí)猜不出來是誰。你想啊,當(dāng)年是十來歲的小姑娘,如今是50歲的老大媽,說不好聽的話,性別都發(fā)生變化了,那嗓音能一樣嗎?聽不出來是正章。覺得蔡勇真的聽不出來,女同學(xué)只好主動(dòng)報(bào)上自己的名字,蔡勇才恍然。聽女生說了小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的安排,蔡勇熱情地答應(yīng),自己一定參加。
小學(xué)同學(xué)現(xiàn)在能是什么樣了?見面聚會(huì)能聊些什么話題?自己在同學(xué)心目中是什么樣子?聚會(huì)后還會(huì)有什么事情發(fā)生?蔡勇聯(lián)想起伏,竟然還失眠了。
聚會(huì)日期到了,蔡勇興沖沖去了飯店。
大包房里分開三十幾年同學(xué)們見面了。彼此互相打量,猜測面前這個(gè)小老太太是當(dāng)年的哪個(gè)黃毛丫頭,面前這個(gè)禿頂?shù)陌氪罄项^是在校時(shí)的哪個(gè)淘氣小子……同學(xué)們圍在老師周圍,匯報(bào)自己的工作生活,漸漸說起了小時(shí)候印象深刻的事,大事小事一起說,什么時(shí)間加入少先隊(duì),那時(shí)叫“紅小兵”;小事說到鉛筆橡皮“三八線”,又漸漸地說起了小時(shí)候的糗事,起外號什么的,比如溜須老師的“跟屁蟲”,愛打報(bào)告的“小叛徒”,也有“鼻涕蟲”“小刺頭兒”……外號起得很客觀,帶著對一個(gè)人外貌、性格的鑒定。
蔡勇一直以為,寡言少語的自己在同學(xué)心目中的印象應(yīng)該是很好的,但是沒想到,同學(xué)們還是給他小學(xué)時(shí)代的行為做了貶義的定義,那個(gè)稱呼就是“欠兒登”,說蔡勇把同學(xué)的秘密事告訴給老師,這個(gè)欠兒登不僅僅有[得][口]瑟的意思,還有告密、告狀的嫌疑。
這個(gè)定義不準(zhǔn)確吧,自己雖然身為班干部,但是很正派,不會(huì)把同學(xué)的秘密報(bào)告給老師。蔡勇好奇地問,哪件事我告密了?就是那件事,男生偷葡萄的事。那時(shí)張梅家住一樓,窗前有個(gè)小院子,張梅她媽種了葡萄,葡萄熟了的時(shí)候,幾個(gè)男生就去摘,被張梅媽給攆跑了。你把這件事告訴給老師,老師把我們狠狠地批評一頓,還通報(bào)給家長,結(jié)果我們都挨老爸的屁板子了。同學(xué)繪聲繪色的講述讓蔡勇發(fā)愣:我怎么不記得這件事。蔡勇解釋,可是沒人相信他的話,都說有那么一回事,蔡勇只好閉嘴告饒。
聚會(huì)在接近午夜時(shí)分結(jié)束,大多數(shù)同學(xué)情意纏綿,相約以后每個(gè)月聚會(huì)一次,有同學(xué)張羅去歌廳唱歌。受“欠兒登”貶義外號影響,蔡勇情緒低沉,他直接回家了。
蔡勇跟妻子說“欠兒登”的事,妻子說,別小心眼,無所謂。
小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后不久,很快電話又來了,還是同學(xué)聚會(huì),這回是初中同學(xué)。蔡勇如約而至。一是盛情難卻,再是他也想看看初中同學(xué)的樣子,讓蔡勇萬萬沒想到的是,初中同學(xué)里也有小學(xué)同學(xué),兩下一摻合,不知怎么搞得,蔡勇“欠兒登”的外號又被初中同學(xué)叫開了。
蔡勇急切地向同學(xué)們解釋,我真不是那樣人,我不會(huì)告狀,真的沒有那么一回事。初中同學(xué)似乎沒把蔡勇的解釋當(dāng)回事,輕描淡寫地說,就是欠兒登又怎么了,這是班干部對班級工作負(fù)責(zé)任,是要求進(jìn)步的好學(xué)生,那些不要求進(jìn)步的學(xué)生從來不向老師告狀。這是什么邏輯?蔡勇接受不了,繼續(xù)解釋,同學(xué)們繼續(xù)反駁。百口難辯,越描越黑,蔡勇不吱聲了,再一次帶著郁悶的心情離開初中同學(xué)聚會(huì)。
在初中同學(xué)聚會(huì)不久,蔡勇又提心吊膽地參加了一次高中同學(xué)聚會(huì)。謝天謝地,高中同學(xué)聚會(huì)沒人提及“欠兒登”這個(gè)話茬兒,蔡勇算是全身而退。
小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后,一些同學(xué)意猶未盡,提出建立微信群。建吧,群名也是滿滿柔情的名字,叫“親親同學(xué)群”。蔡勇工作忙,沒空出來聊天,一直潛水。有一天他看見有同學(xué)說:一些同學(xué)很不仗義,只在搶紅包時(shí)冒泡,平時(shí)潛水,這樣不好。蔡勇感覺這話是說自己呢,就開始“冒泡”。可是這個(gè)泡沒“冒”好,他又惹禍了,有同學(xué)想起了外號的事,直呼他“欠兒登”。
蔡勇很無奈。他覺得,自己這個(gè)很雄性的名字和很男人的高大身材和很正派的人品,很難和“欠兒登”這樣卑劣的稱號聯(lián)系在一起。他百思不解,開始回憶小學(xué)生活。作為插班生,他是后來轉(zhuǎn)學(xué)到這個(gè)班的。班里大部分同學(xué)都是工人村的孩子,蔡勇和后來的幾個(gè)外來同學(xué)不住工人村,很少和那一片的同學(xué)來往,甚至他都不記得張梅家的小院子種過葡萄樹,所以他覺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把男生偷葡萄的事向老師“告密”。
蔡勇不是為一個(gè)外號耿耿于懷。男子漢大丈夫,不值得為一個(gè)外號斤斤計(jì)較,問題是他覺得這個(gè)外號有損人格,他絕對不是那樣陰險(xiǎn)之人。越想越不高興,蔡勇一按刪除鍵,退出了微信群。
在這之后,蔡勇又參加了幾次同學(xué)聚會(huì),漸漸覺得,同學(xué)聚會(huì)也就是那么回事,見面之前蠻激動(dòng)的,見面之后也沒啥收獲。聚會(huì)次數(shù)多了,反倒讓人頭疼。不去不好,別人說你清高;去了也別扭,比你職務(wù)高的同學(xué)看不起你一個(gè)小職員,當(dāng)了大老板的同學(xué)懶得理你的清貧,在底層做體力勞動(dòng)的同學(xué)又不敢接近你一個(gè)政府公務(wù)員。蔡勇屬于“中層干部”,比上不足,上有當(dāng)廳長的高官,比下有余,下有在勞務(wù)市場做力工的下崗工人。不管怎樣,他都覺得沒勁!
蔡勇參加同學(xué)聚會(huì)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心境總算安穩(wěn)一些。他還發(fā)現(xiàn),親親同學(xué)群也漸漸蕭條,有時(shí)一連好幾天群里都沒一個(gè)人出來說句話。蔡勇覺得這樣也好,比起自己被誣陷成“欠兒登”,耳根清凈利大于弊。蔡勇還祈禱,最好不要再接到同學(xué)聚會(huì)的電話……
這天傍晚,手機(jī)響了,蔡勇一看是陌生電話號,想了想他接了。對方是一個(gè)對他非常熟悉的人,開口叫他“蔡處”,接著問他,最近有空沒,同學(xué)聚會(huì)能來不?
同學(xué)聚會(huì)?蔡勇心里一緊:什么同學(xué)聚會(huì)?小學(xué)初中高中?
都不是。對方回答。
那是大學(xué)、研究生?
也不是。
那是什么同學(xué)?蔡勇一時(shí)蒙住,想不起來自己還有什么樣同學(xué)。
黨校同學(xué)。對方高聲回答。
黨校同學(xué)也聚會(huì)?蔡勇脫口而出。
是呀,現(xiàn)在不是流行同學(xué)聚會(huì)嗎。你就說吧你能來不?
我——不好說呀。蔡勇遲疑著。
別磨嘰,來吧。時(shí)間地點(diǎn)都安排完了,過后我發(fā)你短信,你來就行。
我——?
我什么我?對方帶著自來熟的命令口吻:大家都到場,一個(gè)都不少,你也不能缺。不等蔡勇回答,對方撂了電話。放下電話,蔡勇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怎樣才好。
回家后蔡勇和妻子說,黨校同學(xué)還要聚會(huì),去不去哪。妻子一點(diǎn)沒打奔兒,斬釘截鐵地說:這個(gè)聚會(huì)你得去。黨校同學(xué)都有能力有出息,和他們搞好關(guān)系,將來能用得上。
萬一——
萬一什么?老婆問。
萬一有人說起我什么呢?
怕啥,誰愛說啥誰說啥,咱也沒什么見不得人的事。
蔡勇想說,萬一有人知道我在同學(xué)當(dāng)中的外號叫“欠兒登”,那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