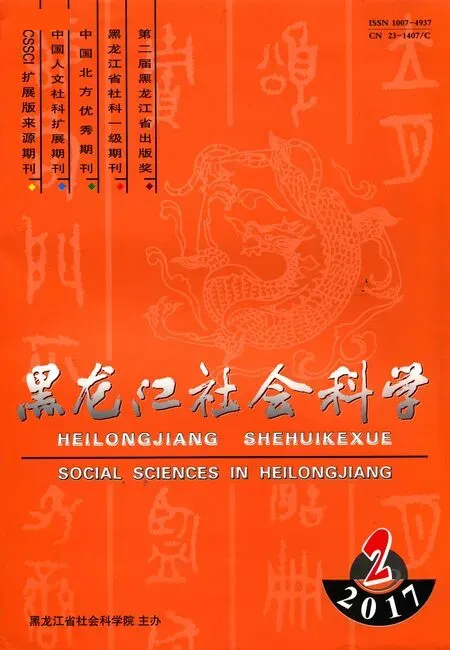走向實踐:實踐人道主義的邏輯起點與對異化概念的理解
——馬爾科維奇實踐人道主義思想理論意義述評
宋 鐵 毅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哲學教研部,哈爾濱 150080)
?
走向實踐:實踐人道主義的邏輯起點與對異化概念的理解
——馬爾科維奇實踐人道主義思想理論意義述評
宋 鐵 毅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哲學教研部,哈爾濱 150080)
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以實踐人道主義超越理論人道主義的構想,并逐步形成并開啟了哲學的革命性變革。在此基礎上,馬爾科維奇從人道主義辯證法思想出發,嘗試以實踐人道主義的思維范式重新闡釋馬克思哲學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并試圖構建一種“現代批判的社會哲學”。馬爾科維奇一方面認為馬克思哲學是徹底的歷史一元論,而另一方面又在“現實—潛能”的二元結構中理解人的本質,毋寧說,馬爾科維奇在理論邏輯上從人即一種二元結構走向了一種徹底的歷史一元論。盡管,相對于人類的現實歷史進程而言,這種邏輯上的考察似乎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但是,從中卻不難窺視實踐人道主義對理論人道主義進行超越的關鍵節點所在,以及馬爾科維奇辯證法思想對于理解馬克思實踐人道主義思維范式的理論意義。
馬爾科維奇;實踐;人道主義;辯證法
從對于馬克思哲學的實踐人道主義闡釋出發,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試圖以一種新的哲學范式來超越傳統哲學。在此意義上,這部手稿并不是馬克思青年時期不成熟的成果,而是一部奠基或開端之作——實踐人道主義范式成了他此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1]。然而,由于歷史原因,這部手稿及其所奠定的實踐人道主義范式被長期地埋沒,直到它重見天日才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重視。對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的關注與挖掘,成了使馬克思的整體理論向實踐哲學或實踐人道主義轉向的歷史契機。在諸多學者中,作為南斯拉夫實踐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馬爾科維奇,尤其重視對于馬克思的實踐人道主義范式的闡釋,他將馬克思的辯證法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辯證法,并以此為方法論基礎,嘗試建構一種“現代批判的社會哲學”。
一、馬爾科維奇對于實踐人道主義的理解:批判的或辯證的人類學
馬爾科維奇認為,辯證法“包含著一種明確闡述了的方法論,一種無保留的方法,一種世界觀,一種活動方式和‘為我們’的世界”,而在哲學的語境中,辯證法意味著一種理論和方法以及作為“元水準”的方法論[2]7。但是,一種合理的方法論與自發或無意識的方法運用之間卻存在差距,即能否獲得清醒認識與方法論預設了理論整體的自覺兩者之間存在差距。在馬爾科維奇看來,馬克思的辯證法業已獲得了這種自覺,就其在諸多批判方法的類型學地位來說,乃是一種人類學假定,而這種人類學假定與其他批判方法的根本區別在于它的核心范疇,即人在歷史中的自我實現。因此,馬爾科維奇從實踐人道主義范式出發,將馬克思的整體理論指認為一種批判的人類學或辯證的人類學。
首先,在關于人道主義的理解方面,馬爾科維奇提出了人道主義理論的評價標準。他認為,只有從人的觀點出發研究現實,才能被認為是人道主義的,其他傾向則不然,“因為它們使人服從一種理想,這種理想或者是一種人類心靈的異化產物,或者采取了一種人類行為的實體化規則的形式,或者可能只是人類解放和自我實現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已經被那些拋棄了普遍的人類觀點的批評家變成了一個基本目標”[2]26。其他傾向則不然,比如現今大行其道的理性主義,“在這種思維模式的支配下,可測量性、可計算性、可證實或證偽性成了衡量一切存在合法性的尺度”[3]。如果回想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人道主義以及理論人道主義與實踐人道主義之間本質區別的論斷,*馬克思認為,理論人道主義是以對神的揚棄為旨歸,而實踐人道主義則是以對私有制的揚棄為目的。參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頁。就不難發現,他們對于人道主義理解的契合點,即人道主義在其本質上乃是以人的本質及其對象化世界之間的關系為其理論核心問題的。進而,理論人道主義與實踐人道主義的本質區別則在于前者是以給定的人類本質來拒斥人類自身的異化形式,而后者則是將人類本質理解為生成的歷史過程,從而不斷對人本質的異化形式進行揚棄,使其對象化世界復歸于自身(從具體總體的人的立場出發,不斷揚棄特定歷史階段的異化形式,就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而言,乃是揚棄私有制,從而在實現人的政治解放的基礎上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在此意義上,理論人道主義因無法擺脫自身理論出發點的局限——人類的給定的本質本身即是人之異化的現實形式之一——而始終不能超越給定的本質與現實的人之間的異化關系的困境,因此,馬爾科維奇認為,實踐人道主義才是一種徹底的歷史一元論或一種徹底的人道主義。
其次,為了闡明實踐人道主義對于人的本質的理解,或實踐人道主義何以成為一種批判的或辯證的人類學,馬爾科維奇引入了三個重要范疇,即基本的人的能力、真正的人的需要和實踐。馬爾科維奇認為,以上三個范疇來自于人的自我實現這個概念的預設,其中,基本的人的能力是“人性之主要的決定性因素,并以潛在的先天傾向的形式存在于每一個正常人之中”,只不過這些能力由于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的限制“被閉塞、禁錮和阻撓著”[2]28,因此也就為人之存在的未來的可能性即人的能力的歷史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間。需要概念在人之存在的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起到了聯通的作用,即是說,作為一種能動的關系,需要為人的對象世界的“內在化”和人的本質的“外在化”的過程提供了基礎,“需要是人對世界的一種能動關系,即一種雙重的關系……就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一種物理—心理的、客體—主體的關系”[2]29。但是,馬爾科維奇認為,必須要在真正的人的需要與虛假的、人為的需要之間做出區分,“真正的人的需要是那些其滿足導致了重新認識和發展人之基本能力的需要。虛假的、人為的需要則是那些與這些能力的發展完全無關的需要,因而這種需要直接或間接地阻礙和窒息了人的基本能力的發展”[2]30。在此意義上,虛假的、人為的需要即為異化了的需要。至此,馬爾科維奇立足于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為其設定了一個由實際結構和潛在結構所構成的二元形式,即“現實—潛能”。但是,馬爾科維奇并不滿足于停留在對人之存在自身矛盾的理論“描述”上,換言之,他不過是從現實的二元結構即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最終走向了一種徹底的歷史一元論。在馬爾科維奇看來,實踐是人類自我實現的過程,亦即人之歷史的實質,因此,實踐概念在這樣的結構轉換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在實踐活動中“創造了最佳的可能性,因此這種活動就是目的本身……一方面,它根本不同于描述的、價值中立的勞動概念;另一方面,實踐也是和否定的、異化勞動的概念完全對立的”[2]30。因此,實踐是發展人的基本能力、滿足真正的人的需要,并最終實現人之自我實現的歷史過程,亦即人與其對象世界、人之現實性與可能性、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中介,“實踐包括特殊的個體能力的客觀性,因此,它的本質之一就是自我確證;與此同時,實踐也滿足了其他人的真正的需要”[2]31。
綜上所述,在馬爾科維奇看來,一種徹底的人道主義必然要從現實的人的二元結構即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在人與其對象世界的辯證關系中,以實踐為中介理論的人的真實歷史的呈現,即人之自我實現的過程,在此意義上,實踐的人道主義也必然會是一種批判的或辯證的人類學。
二、馬爾科維奇對于異化的理解:人之自我實現的局限
從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馬爾科維奇提出了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盡管奧伊澤爾曼曾批判馬爾科維奇“以最一般的抽象形式把異化概念解釋為個人的可能性和有限而不充分地實現這種可能性之間的矛盾”[4],并沒有擺脫所謂的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局限,但是,這恰恰證明了馬爾科維奇對于異化理解的獨特性。在馬爾科維奇看來,“個人的實際存在和潛在本質之間的這種差異,即實有和應有之間的差異,就是異化”[2]18。換言之,異化是對于人之本質的實現,即人之自我實現的限制。進而馬爾科維奇將黑格爾與馬克思辯證法中的“否定”理解為對人之自我實現的限制的超越,并將馬克思的理論理解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與抽象的否定不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總是指向如商品、異化勞動、階級、國家等人類歷史中的現實的異化形式,并試圖超越這些歷史的特定限制而實現人類未來的最佳可能性。因此,“馬克思的關鍵概念總是要么指涉那些已經被廢除或可能被廢除的結構,要么指涉那些尚未被創造或可能被創造的結構”[5]。
可以斷言,馬爾科維奇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與他對馬克思實踐人道主義的理論結構的揭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實踐人道主義的邏輯起點乃是現實的人的內在矛盾,而不是一種虛假的總體性或給定的先在的同一性。困擾近代思想家們的問題,在實踐人道主義的理論框架下以相反的形式被呈現出來,并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與說明。即是說,近代思想家們從抽象的、虛假或給定的普遍性出發,最終陷入了難以彌合的二元論困境;相反,實踐人道主義卻從人之存在的二元論結構中走向了一種徹底的歷史一元論。在此意義上,馬爾科維奇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真正地捍衛了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合法性。
眾所周知,對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拒斥與批評,源自于對其的誤讀,換言之,源自于將馬克思異化理論重新置于傳統哲學的結構中,并將其作為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的延續而加以拒斥。在傳統哲學的框架下,“非異化”與“異化”之間的關系,被宗教神學解釋為以原罪為中介的上帝與人的關系,而在自然主義者那里,則被指認為以客觀規律為中介的自然與人的關系,一言以蔽之,“非異化”與“異化”的關系被理解為給定的總體性或本質與現實的人的境遇之間的關系。但是,馬克思異化理論與此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即是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于異化的揚棄并不是要使現實的人的境遇與給定的總體性或本質達成一致,并不是要使人的境遇“復歸”于那個業已被給定和發現的“舊世界”,而是要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去發現“新世界”或人之存在未來的可能性。因此,馬爾科維奇將異化理解為對人之自我實現的局限,理解為以超越為中介的人之現實性與可能性(現實—潛能)的關系,顯然與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內涵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馬爾科維奇以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為邏輯起點,以對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獨特理解為基礎,以實踐人道主義為范式,對馬克思理論進行了重新地闡釋,并將其發揮為一種批判或辯證的人類學或直面人之現實境遇的社會批判理論。這樣的發揮將實踐哲學、人道主義與辯證法統一在一起,對重新理解和闡釋馬克思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三、馬爾科維奇思想的理論意義:走向實踐
可以說,馬爾科維奇之所以能夠以實踐人道主義范式將實踐哲學、人道主義與辯證法統一起來,并以其對馬克思理論進行整體上的重新闡釋,乃是在于他理論結構中的核心范疇——實踐。毋寧說,馬爾科維奇通過對馬克思理論的實證主義理解方式的整體批判,最終捍衛了馬克思理論作為一種實踐哲學的合法性。
首先,馬爾科維奇理論的邏輯起點,即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是馬克思實踐基礎的重要理論形態。直立行走以解放上肢,即人類實踐活動的最初表現形式,使人類獲得了自身的規定性。然而,這一規定性卻以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兩種不同的形式具體展現出來,“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個方面是社會關系”[6]。即是說,人類需要同時面對人與自然即人與其對象世界的關系,以及人與社會即個體的特殊性與類的普遍性或現實性與可能性之間的關系。在此意義上,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既是人類現實歷史的理論形態的邏輯起點,同時又是對人之存在的真實的人類學指認。
其次,馬爾科維奇理論的整體建構,即人之存在的二元論結構與徹底的歷史一元論之間的統一,在其本質上,乃是人之現實的實踐活動的展開過程和歷史結果。古代哲學乃至理論人道主義,由于自身理論的局限性,都未能正確地揭示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的實質,因而也就無法真正理解人之存在的二元論結構與歷史的一元論之間的內在關系。古代哲學和理論人道主義割裂了主觀性與客觀性,“或簡單地把兩者并列起來(二元論),或者在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間進行理論推導和還原(一元論),因而他們根本沒有解決問題,而是把問題原封不動地承續下來,或者干脆取消了問題”[7]。一言以蔽之,他們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自身的現實性與可能性的關系,理解為抽象的本體關系或認識關系,而非一種實踐關系。因此,在對于人之存在的現實的理論指認與歷史的理論指認之間設立了難以逾越的鴻溝,最終均導向了實質上的二元論。事實上,馬爾科維奇理論所揭示出的恰是這種被古代哲學和理論人道主義所忽視的實踐關系,亦即馬克思哲學的理論特質。從實踐人道主義的立場發出,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及其統一與歷史展開立基于實踐之上。一方面,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是實踐活動的歷史結果與前提,即歷史的“先驗”與“后驗”的統一;另一方面,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的統一與歷史展開的過程亦是人類實踐的過程和人之歷史的現實進程。因此,實踐人道主義正是人的現實活動和人之歷史進程的理論形式。
最后,馬爾科維奇理論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即對人之自我實現的局限性的超越,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及異化理論合法性的有力說明與論證。由于人之存在的內在矛盾——盡管不同的理論形式對其本質的理解不盡相同——任何一種人道主義理論都無法回避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但是,無論是自然主義的理解方式,還是宗教神學的理解方式,都難以使其對異化概念的理解自圓其說,并最終走向理論困境,即便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也曾因其對傳統哲學的解釋方式而飽受爭議。但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傳統哲學的異化理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換言之,傳統哲學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總是從一個給定的和抽象的本體出發,試圖以還原——返魅或原罪的自我救贖——的方式,揭示“非異化”與“異化”之間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則將異化與異化的揚棄視為一個統一的過程,視為現實的歷史進程和人的本質不斷生成即人之自我實現的過程。眾所周知,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考察,揭示了在私有制條件下,人與其對象世界的分裂與對立,然而,這種“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8],即是說,實踐活動是揚棄異化、統一人之存在內在矛盾的唯一途徑。因此,由于馬克思理論整體上的實踐哲學特質,其異化理論中所使用的“復歸”概念與傳統哲學意義上的“還原”相去甚遠。在此意義上,馬爾科維奇對于異化概念的理解方式正是對于馬克思異化理論基本觀點的證明與發揮。馬爾科維奇將異化理解為對人之自我實現的限制,而將異化的揚棄理解為對限制的否定與超越,換言之,異化及其揚棄的奧秘正在于人類的現實歷史進程亦即人之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而所謂的“復歸”也并非指向某種抽象的本體,而是指向人類歷史的真實核心,即人之實踐活動自身。因此,一種徹底的實踐哲學,即實踐人道主義,也必然將其實踐特質貫徹在它的本體論層面,展現為一種實踐本體論。
綜上所述,馬爾科維奇以實踐人道主義范式對于馬克思理論的重新理解,不僅揭示了馬克思理論整體上的實踐哲學特質,揭示了馬克思理論對于實踐哲學、人道主義與辯證法三者的統一,同時也為在實證主義理解方式之外尋求馬克思理論的發展與出路,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與方向。毫無疑問,這種展現了馬克思理論實踐本質和時代精神光輝的理解方式,同樣也會在現實中發揮其作為“現代批判的社會哲學”的實際意義。
[1] 宋鐵毅.作為實踐人道主義開端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王宗禮,馬俊峰,主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5-24.
[2] 馬爾科維奇,彼得洛維奇.實踐——南斯拉夫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文集[M].鄭一明,曲躍厚,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
[3] 李曉敏.危機與救贖——科拉科夫斯基現代性批判理論的重要維度[J].學術交流,2015,(7):30.
[4] 奧伊澤爾曼.關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考——與M.馬爾科維奇院士商榷[J].潘培新,摘譯.哲學譯叢,1990,(3).
[5] 馬爾科維奇.從富裕到實踐——哲學與社會批判[M].曲躍厚,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2:58.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7] 丁立群.發展:在哲學人類學的視野內[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73.
[8]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責任編輯:張圓圓]
2016-12-0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大學生信仰危機的哲學反思及對策研究”(14CSH015)
宋鐵毅(1983—),男,黑龍江哈爾濱人,副教授,哲學博士,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哲學研究。
B1
A
1007-4937(2017)02-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