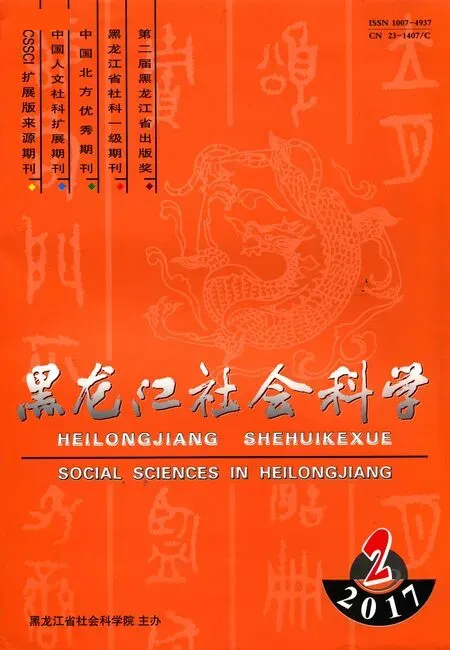音、語、點三符變譯變通觀
楊 曉 靜
(哈爾濱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 哈爾濱 150080)
?
·語言與文化·
音、語、點三符變譯變通觀
楊 曉 靜
(哈爾濱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 哈爾濱 150080)
按照符號學觀點,歌曲是音樂符號、語言符號、標點符號合三為一的藝術表現形式。歌曲變譯指譯者對原語歌曲三符系統的形式及內容進行適應譯語文化需求或特殊現實需求的改造性或變通式翻譯。“變”是歌曲變譯的靈魂和精髓,需求是歌曲變譯的原動力,三符變通是歌曲變譯的主要翻譯策略,包括音符變通、語符變通和點符變通。
符號學;歌曲變譯;三符系統;三符變通
歌曲翻譯是一種特殊的翻譯活動,變譯現象在翻譯實踐中廣泛存在,其作用日益擴大,為歌曲翻譯研究者提供了深入探索的廣闊天地。歌曲是音樂符號、語言符號、標點符號三者的有機整體[1]。準確傳達原歌三符的形式和意義是歌曲翻譯的最高標準,力求保證原歌信息內容不受損是歌曲翻譯策略的主體。但在具體翻譯實踐中,受諸多因素的限制,譯者須對原語歌曲三符的局部或整體采取變通手段,即變譯策略,以滿足多元現實需求。“變通”是歌曲變譯的靈魂,“需求”是歌曲變譯的原動力。
一、歌曲變譯的靈魂:變
(一) “變”之哲學內涵
“變”“化”是中國古典哲學當中的一對范疇,“化”表示事物漸進、自然而然發生的運動變化;“變”側重于表示事物劇烈的、驟然發生的運動變化。朱熹云:“陽化為柔,只憑地消縮去,無痕跡,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2]所謂“陽化為柔”,是由陽之剛向陰之柔的轉化,是由動到靜、逐漸實現的;從外在形態上看,沒有明顯的跡象,謂之“化”;“陰變為剛”則相反,由靜到動,突然發生,跡象顯著,謂之“變”。
《易傳·系辭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變而通之以盡利。”意思是變是化之中表現劇烈、顯著的部分,其中包含著人為的因素,即人們為了求通盡利,在認識自然之化規律的基礎上,通過人為的手段促成事物形態、性質的改變。“‘化’是漸變,‘變’是劇變;‘化’是自然,‘變’則包含人為;人為的劇變又以自然的化為基礎和前提”[3]。
(二) 歌曲變譯之“變”
“變譯論”是由學者黃忠廉首先提出的。變譯指“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思維活動和語際活動”[4]。他認為變譯有四大特征:一是突出了譯者和讀者,是對“人”字的大寫;二是對全譯的異化;三是對原作的部分否定;四是對原作價值的凸顯[5]。歌曲變譯指的是譯者對原歌三符系統的形式及內容進行適應譯語文化需求或特殊現實需求的改造性或變通式翻譯,這種翻譯形式在歌曲翻譯實踐中很普遍。相對于歌曲全譯的“化”,歌曲變譯之“變”主要體現在變動的結構、程度,以及變動是否基于原歌三符內容上。結合中國傳統哲學之“變”,可以將歌曲變譯之“變”的內涵詮釋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歌曲變譯之“變”是主動適應譯語環境的質變過程。歌曲全譯中所出現的細微、不顯著的“化”,是基于中外歌曲三符系統的客觀差異性即不對等性而產生的,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被動適應的結果。即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也是被動地順從原歌的形式和內容,盡最大可能去接近罷了。而較之歌曲全譯的“化”,歌曲變譯的“變”則是大手筆的變革,是“無中生有”“有中變無”的質變過程。或拋棄原歌三符中部分或整個符號系統的形式及內容,主動地對原歌進行“削足適履”地改頭換面;或增加新的符號形式和內容,擴大原歌的容量。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是為了主動去適應譯語環境,達到最大限度地融入與滲透。
第二,歌曲變譯之“變”允許譯者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較之于歌曲全譯過程中譯者的束手束腳、小心翼翼,唯恐“因形害意”,被他人垢之以“不忠實”,歌曲變譯給了譯者極大的自我表現空間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平臺,譯者的地位和創造性大大提高,從原歌的奴隸地位解放出來,反客為主,成為駕馭、操控原歌的主人,可以對之進行符合需要的增加、減少、修改等等。盡管譯者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間,但其翻譯行為卻不能脫離變譯最重要的一條主線——需求,包括譯歌可唱性的需求、聽眾的需求、傳播的需求,等等。因此,歌曲變譯之“變”應該是譯者有意識、有計劃、有目的、故意而為之的變通,是為達到某種現實需要而采取的翻譯策略。在這方面,要把歌曲變譯與譯者因其自身外語、音樂、文化素養不高而造成的誤譯、錯譯嚴格區分開。
第三,歌曲變譯之“變”是譯語聽眾多元化需求的產物。歌曲變譯之“變”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滿足譯語聽眾多元化的需求。可以說,“以人為本”是歌曲變譯的最大特色。譯者就如同裁縫,要針對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量體裁衣”。聽眾對于歌曲的需求可以有很多種,如演唱的需求、欣賞旋律的需求、賞析歌詞的需求、了解歌詞大致內容的需求、了解異域文化的需求等。譯者要針對聽眾的某種特定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變譯方式。特定的需要不僅決定著內容的取舍,也決定表述方式和文字體式的選擇。如果聽眾只是想了解原歌歌詞的大致內容,譯者就沒有必要將歌詞逐句譯出,否則就不僅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也沒有有針對性地滿足聽眾的特定需求。
二、歌曲變譯:三符的變通
事實上,變譯現象在歌曲翻譯實踐中是廣泛存在的,如我們平日所熟識的“歌詞大意”“歌詞翻譯”等,都屬于歌曲變譯的形式之一。而以往廣為傳唱的蘇聯歌曲,通曉俄語的人都會發現翻譯過來的歌詞中似乎總有一些地方與原文不符。其實這些翻譯現象,除了一部分確屬譯者的錯譯、謬譯,絕大多數則都是譯者根據特定的需求,如節奏需求、文化需求、聽眾需求等進行的歌曲變譯,即變通式翻譯。“變通手段的研究范圍可以說最為廣闊,因為任何可以借以實現翻譯的實質內容中所包含的意義和意向轉換的途徑,都可以納入方法論作為變通手段”[6]。
較之于歌曲全譯,歌曲變譯既要照顧三符轉換時自身的內在規律,又要受制于特定條件下特定聽眾的需求,只有通過對現實的某種適應性變通,才可能真正滿足這些需求。
(一)音符的變通
如果說在歌曲全譯范疇下,定型定調的原歌音符系統(旋律)作為全譯三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譯歌語符、點符與之協調統一的指揮棒,是限制譯者畫地為牢的枷鎖、鐐銬的話,那么在歌曲變譯范疇下,原歌的音符系統就不再是眾星捧月的太子,而成了可有可無的小人物,譯者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對其進行局部或整體性的變通。
1. 局部音符的變通
聽眾受自身年齡、職業、受教育水平、音樂素養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對外國歌曲的需求是多元化的。為滿足特定聽眾的特定需求,譯者會對原歌音符系統的形式和內容作出局部的變通。例如,如果聽眾需要適合獨唱的、單聲部的譯語歌曲,譯者就要把本來是多聲部合唱歌曲的原歌音符系統改造為單聲部,只需要轉換主聲部的音符系統,刪去主旋律以外的配合聲部;如果只需要原語歌曲的正歌部分或副歌部分,就可以只摘出正歌或副歌部分的音符進行轉換,刪去其他。
2. 整體音符的變通
在歌曲三符系統中,音符系統、語符系統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即可以脫離其余兩符系統獨立存在,因此,原歌的音符系統具有整體變通的可能性。如果聽眾只是想了解原歌歌詞的內容,或是只針對歌詞進行形式上的改造,那么翻譯的對象就只包括語符系統和點符系統,音符系統就完全沒有存在和轉換的必要,可以整體刪除;如果需要在旋律不變的基礎上,將原歌的節奏變快或變慢,如將四二拍的抒情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改造為四四拍的、快節奏的舞曲風格,那么,譯者就要在音符轉換過程中將整體音符系統的節拍重新劃定,以適合聽眾的特定需求。
(二)語符的變通
語符是歌曲三符系統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于不同語言間尤其是不同語系的語言之間客觀存在的差異,即語形、語義、語用三方面的差異,所以較之音符的變通,語符的變通要復雜得多。
1. 局部語符的變通
局部語符的變通指的是歌詞文本中以音、詞、語、句、段為翻譯單位發生的變譯。其變通的對象不是整個歌詞文本,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同的需求仍然是語符變通的直接動力,這種需求大致分為兩種。
一是對歌曲可唱性的需求,即歌曲演唱的需求。以俄語歌曲的漢譯為例,俄漢兩種語言在語言形式上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俄語屬字母文字,每一個單詞至少一個音節,一般為兩個音節以上,漢語一個字一個音節,通常情況下,表達相同內容俄語的音節數量要比漢語多。而歌曲的可唱性要求譯歌詞和曲節奏上的結合要與原歌詞、曲節奏上的結合相一致,即譯語歌詞的字數應與原語歌詞的音節數相等。歌曲翻譯家薛范先生明確提出:“原文歌詞有一個語言音節,翻譯歌詞也應有一個漢字;原則上,原詞一個語言音節占一個音符,翻譯詞也應在一個音符下安一個漢字;原詞如果一個語言音節占多個音符(拖腔),翻譯詞也一字多音,‘亦步亦趨’。”[7]因此,為了填補空缺的音節,譯者需要盡可能在保證原語歌詞內容不變的前提下增加歌詞字數,這仍然屬于全譯的范疇。但是如果由于韻腳的限制或是空缺音節過多,譯者則不得不局部地對原語歌詞的內容進行以詞、語、句為基本單位地增加、減少或改換。這種脫離原語歌詞意義、“另辟蹊徑”的變通方法,就已經不再屬于語符全譯范疇,而是屬于歌曲語符變譯范疇了。
另一種需求是對原語歌詞部分內容攝取的需求。俄語歌曲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即主歌部分的歌詞通常都在三段以上,甚至五六段的歌詞也并不少見。如我們非常熟悉的《三套車》,其主歌部分就有六段歌詞。這種歌詞特色自然與俄羅斯民族的敘事風格及演唱傳統有關,但如若傳譯到中國就會與漢族以“簡”為美的審美習慣發生沖突。為避免演唱時因主歌部分旋律重復次數過多給國內聽眾帶來的審美疲勞,譯者有時候要減少歌詞主歌部分的段數,只從原歌詞中摘選出若干段進行翻譯。如20世紀50年代高山先生在翻譯《三套車》時,就故意刪減了歌詞的第三段、第五段和第六段,只保留了原歌的一、二、四段,歌詞的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不能不說是譯者為了滿足國內聽眾的審美期待,或傳播的需求而作的變通處理。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高山先生對原歌詞的“再創造”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更深層的根源:“譯者在‘左傾’思想泛濫的年代,把文藝作品當作打擊敵人,宣傳群眾的武器,對《三套車》的歌詞進行了穿鑿附會的‘再創造’,得出他的譯文。”[8]可見,無論是為了適應聽眾的審美習慣,還是為了突出強烈的階級斗爭意識,譯者都采取了不同于全譯的翻譯策略,只攝取了原語歌詞中的部分內容,對原歌的語符作出了符合某種現實需要的變通處理。
2. 整體語符的變通
相對于局部語符的變通,整體語符的變通通常以整個歌詞文本為變通對象。整體語符的變通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整體語符形式的變通,二是整體語符內容的變通,三是整體語符形式及內容的變通。
歌詞是詩化的文學語言形態,具備詩美的語言特質和詩化的文學語言美,既有外在的形式特征,又有內在的內容體現。其外在形式特征體現在:句末同韻相協,節奏頓數相對,遣詞造句注重排偶、對仗,從而造成韻律和諧、節奏鮮明的詩化美的藝術語言效果[9]。歌詞語符外在的詩化形式對于其內容的表現和整體風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形式意義的轉換也是歌曲全譯的要求之一。但是將歌詞譯為詩化的語言,其復雜性必然要比譯為更接近口語的散文體大得多,如果現實的需求只是了解歌詞具體內容的話,譯者為提高翻譯效率,縮短翻譯時間就會放棄原語歌詞詩化的外在形式,改用更為平實的散文體來表述歌詞內容,也是采用變通整體語符形式的方法。
我們注意到,在一些歌曲中,形式較之內容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甚至整首歌曲的風格就取決于形式的風格。例如字母歌、拆字歌、回文歌、繞口令歌,等等。例如,美國音樂劇《音樂之聲》中的插曲“哆來咪”,就是把自然音階中的每個唱名與一個發音相同或相近的英語單詞通過諧音的方式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整首歌詞的內容脫離了英語的發音根本無法理解,如果勉強地直譯為漢語,聽眾完全無法領會到原歌詞形式構造的巧妙之處。因此,要想傳達這種特殊的形式意義,譯者只能摒棄原語歌詞的內容,仿效原歌詞所采用的諧音方法,用漢語重新填詞。
在某些條件下,出于時間或篇幅有限的要求,不能將原語歌詞的內容完整地譯出,只能大致地翻譯其內容,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歌詞大意”。這時,不僅原歌詞詩化的語言形式無法保留,就連歌詞內容也要根據需求作整體地壓縮。譯者首先將歌詞的大致內容進行概括、濃縮,然后再用自己的語言對其進行表述,這種變通方法是對原語歌詞的形式和內容所做的較大程度地改造。如果說這種變通方法算得上大手筆的話,那么還有一種變通方式就堪稱是“偷天換日”了。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外歌翻唱”,即只保留原語歌曲的音符系統(旋律),其語符系統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統統棄之不顧,用漢語重新填詞、“另起爐灶”。聽起來,曲還是原來的曲,但曲中發生的人和事卻早已“物是人非”了。
(三)點符的變通
點符作為一種不能完全獨立使用的符號,與語符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與語符不同的是,點符所蘊含的意義或信息并不指向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缺乏明確的語義功能,而是通過“考慮語義、邏輯、語法、語調、語用等因素,使用約定的書寫符號、間隔安排及其他技術手段把話語加以切分,標示停頓、語氣以及各語言單位的性質、作用及其相互關系,以輔助文字準確地表情達意,使話語易于閱讀和理解”[10]。但在歌曲翻譯特別是在歌曲全譯中,點符除了輔助語符的基本功能外,自身還承載著與歌曲旋律相符的節奏信息。對于單純聆聽歌曲的聽眾來說,原歌的點符是隱形的,聽眾既不能聽到逗號、分號,也無法聽到句號、問號;但聽眾卻能輕松地理解歌詞內部的邏輯關系和所述內容,一般不會對歌詞的內容產生誤解。這是因為在作曲家為歌詞譜曲的過程中,點符已經被作曲家融化在音樂中,以動機、樂節、樂句、樂段、半終止、完全終止等方式和節奏給歌詞標上了無形的點符。
導致歌曲點符變譯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語符在轉換過程中由于兩種語言在語法結構、邏輯關系等方面的差異性,語符形式發生了變化,如原語中的詞或短語可以轉換為譯語的小句,小句可以轉換為復句。隨著語符形式的更換,作為語符輔助工具的點符也不得不通過增加、減少、改換的方式來適應語符的變化。二是當語符脫離音符發生整體變譯時,點符就喪失了自身承載的、與音符相呼應的節奏標注功能,只保留其輔助語符表意的基本功能。
結 論
本文通過對“變”內涵的闡釋與分析,得出“變”是歌曲變譯的靈魂和精髓的結論。歌曲變譯是譯者對原語歌曲三符系統的形式及內容進行適應譯語文化需求或特殊現實需求的改造性或變通式翻譯,需求是歌曲變譯的原動力,變通是歌曲變譯的主要翻譯策略,主要包括對原歌音符、語符、點符整體或局部的變通。但無論歌曲三符如何變化,譯歌仍要保留原歌三符的部分形式或內容,才不至于失去與原歌的血緣聯系,完全變成另一首全新的歌曲。因此,歌曲變譯與全譯并不是相互沖突、無法共存的對立體,而是按不同比例配比的結合體。
[1] 楊曉靜.音、語、點三符全譯轉換說[J].學習與探索, 2011,(4).
[2] 黃黎星. 朱熹論《周易》“乾道變化”之精義[J].孔子研究, 2010,(1).
[3] 錢遜. 和與變[J].社會科學研究, 1998,(2).
[4] 黃忠廉,等. 翻譯方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12.
[5] 黃忠廉. 變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1:78.
[6] 劉宓慶. 新編當代翻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5:184.
[7] 薛范. 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111.
[8] 余一中. “姑娘”是怎樣變成“老馬”的?[N].中華讀書報, 2009-03-11.
[9] 余篤剛. 聲樂藝術美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2005:11.
[10] 林慧芳. 標點符號學習與應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10.
[責任編輯:修 磊]
2016-12-11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歌曲漢譯之全譯方法體系研究”(13B020);黑龍江省哲學社科研究規劃青年項目“19世紀俄蘇歌曲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音樂文化發展影響的研究”(13C041)
楊曉靜(1981— ),女,河北邯鄲人,副教授,文學博士,從事語言學研究。
H159
A
1007-4937(2017)02-01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