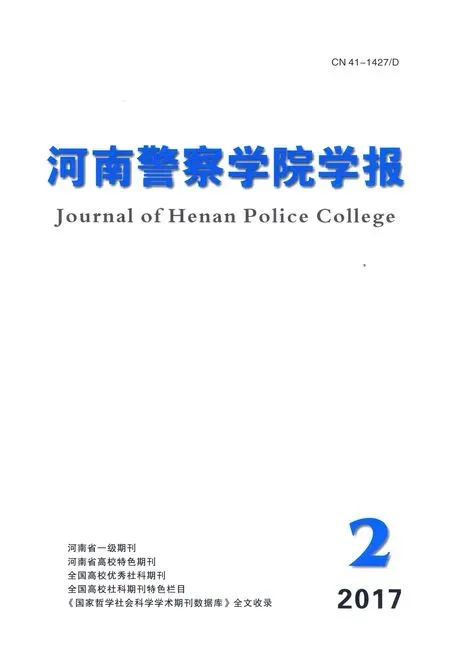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主體性考察
——以C直轄市司法人員實證訪談為基礎
樊華中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主體性考察
——以C直轄市司法人員實證訪談為基礎
樊華中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社會工作中,主體對主體性認識程度、實現程度決定了工作積極性與工作成效。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機制中雖存在多元主體設計,但掩蓋不了單一主體推動制度落實的現實。原辦案單位的法官、檢察官是刑事指導性案例的報送、推薦主體,但其在整個指導性案例工作機制中因付出多回報少而工作積極性不足。又因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中標準確定被行政化管控而喪失。相較而言,在生成機制的主體性考察方面,與正面宣傳相反的坊間信息更有可信度,進而也暴露出被遴選出的指導性案例從長遠來看,其生命力與指導性值得擔憂。
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主體;主體積極性;案件質量;案件數量
一、問題提出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何謂本文的主體性。在社會工作中,主體永遠是第一位的,主體對客體的運用、改造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規律。主體本身的價值取向、動力源泉、在開展工作時對各種利益的衡平,將直接決定最終的工作成果、成效。人只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時才會熱情、真切、踏實地完成工作,如果自己的成果被他人決定,那就意味著主體性的喪失。主體對自身主體性的認識程度、實現程度決定了主體參與工作的積極性以及主體如何開展工作,進而也決定了工作本身的成效。
二、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主體分析
人與事始終是考察社會工作的兩條主線。在中國公權事務中,人作為主體性因素,對于事的決定性意義更是重大,人興則事旺。刑事指導性案例作為國家司法權力篩選的結果,參與其中的主體成分有哪些,參與的積極性如何,提供了多少案例源,何種案例、哪些案例具有標本意義、指導性意義,誰擁有最后的決定權等,則是分析中國指導性案例的關鍵指標。
從《高檢規定》第十條、《高法規定》第五條的內容來看,兩高對于指導性案例申報、推薦予以了較高的開放性,更多的主體可以參與到中國特色指導性案例建設中。根據規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專家咨詢委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可以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案例指導工作委員會工作機構推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律師,以及其他關心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的社會各界人士” 可以向做出生效裁判的原審人民法院推薦。兩高規定充分體現了生成主體的民主性、多元性取向[1],對于指導性案例的申報主體未做任何限制,只要是本國國民均可以推薦,意味著案例當事人也可以向法院推薦申報。
任何工作的難易程度、可實現程度與工作回報都是成正比的。無激勵、無實質認可的工作既調動不了兩院系統內的工作人員,也調動不了尋常百姓。對這種看似寬泛的多元主體理論研究中也不無批評,而且,基于法官具有撰寫指導性案例的特殊平臺、通過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后大幅提升的能力以及為法官的職業尊榮感驅使等因素,“法官才更有動力參與到指導性案例工作之中”[2]。只有法官、檢察官才是多元申報、推薦主體中的真正主體。在實證研究階段,筆者對生成主體核心——法官、檢察官的深談訪問中,聽到不少不同于正式制度但又客觀得讓人無法質疑的聲音,*因為這些看似不符合正面宣傳的話語只有在閑談時才會表露,出于尊重談話者,本文以下不會一一表述每個談話者的姓名、單位。如“我們法官申報、推薦都很困難,讓體制外人推薦條件苛刻的指導性案例,他們閑的沒事做了么?”,如“檢察院內部的工作機制,我們有時都覺得程序過于繁瑣,要填寫很多文書,外行人哪里會填寫那么多文書?”,如“我們收到的推薦案例中,全是系統內的人撰寫,他們更懂案件的來龍去脈”,再如“有些案件的前因后果、重大背景只有我們的人才會深刻領會”等等。實務訪談也印證了只有法官、檢察官才是真正的指導性案例的參與者。
從風險承擔上,指導性案例也不會由法院、檢察院體制之外的人參與。試舉簡單一例,在常規的指導性案例篩選工作中,只有法官、檢察官才會對自己推薦的案例進行反復、認真的研習、修飾,最后以符合法院、檢察院官方話語結構的文體表達出來。這一過程要經歷細心、細致的上下級法院、檢察院之間的溝通、匯報,如有不慎,本如十月懷胎一樣精心呵護、小心推薦的案例便會因推薦程序、遴選程序中的一些因素而難產或流產。這一風險,是任何法院、檢察院體制內的推薦主體都不愿意承擔的,更何況法院、檢察院體制外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專家咨詢委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因此,看似開放性的多元主體推薦制,掩蓋不了單一主體推動制度落實的現實。
三、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主體積極性分析
讓指導性案例生成的主體呈現出多樣性,在制度層面上減少了法官的申報壓力,但掩蓋不了單一主體——法官、檢察官推動制度落實的現實。從推薦工作后的實際承擔者方面考慮,根據《高檢規定》,檢察機關指導性案例雖然由多元主體參與推薦,但最終落實工作的仍然是“辦理案件”的檢察院。根據《高法規定》,法院指導性案例的最終落實工作也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審人民法院”完成。換言之,不論是由哪一個推薦主體推薦的案例,最終落實具體申報案例工作的人員,均是原辦案的檢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員。
(一)基于辦案量考查生成主體的積極性
法官、檢察官均是血肉飽滿、有情有義的人,既非啟蒙時代思想家所言的正義女神,也不是輸送正義的傳送器。現代法社會學對司法工作的研究已經豐富到將法官、檢察官視為斤斤計較的經濟人、理性人。法院、檢察院等體制內的人既關注自己的榮譽感,也關注生存感。實證訪談中,“生活不好的法官不可能無憂無慮、秉持中正地判案”“對自己親人都不能照顧的法官、檢察官不是好法官、檢察官”“被記功、推模范、宣講事跡的法官、檢察官都是落下殘疾的法官、檢察官,有的連命都豁出去了”等一些言論表現了法官、檢察官對于官方正面宣傳中的偶像的真實評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身的價值取向。客觀而言,這既不是貶損、也不是對核心價值觀的違背,而是對事實的交代,也是對歷史的真切認識。流傳清史的包公、海瑞等從家庭、朋友圈、社交的角度獲得的積極評價要遠遠低于公正斷案獲得的積極評價。真實的歷史就是如此。工作任務挑重擔,只能家庭壓力減負擔;家庭壓力挑重擔,工作任務只能減重擔。就正常人的生理結構而言,其一生承擔的工作量是有限的,超過負荷拼命工作要么是瘋子,要么是在撒謊。
良好的人際關系不僅可以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還能為人才的成長營造良好的氛圍。大學階段是自我意識形成的重要階段,人際交往是認識自我的重要途徑,但大學生在這個階段最突出的問題是有強烈的需求卻缺乏實現需求的能力。
從宏觀數據來推算,改革開放三十余年,法院受理案件數由1978年的61萬件增加到目前的1200多萬件,增長約20倍。與此同時,法官人數從1978年的6萬余人增加到目前的21萬余人,增長約3倍。顯然,辦案人數增長與案件量增長明顯不成比例。*更多法院編制數與案件數變遷情況,參見劉忠:《規模與內部治理——中國法院編制變遷三十年(1978—2008)》,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5期,第47-64頁。限于可公開、可查閱的數據,2011年出版的《中國法律年鑒》中統計,2010年我國法官人數為19.3萬,當年處理案件總數為1099.9萬件,人均年辦案數僅為57件。但事隔多年后,2014年啟動、2015、2016年內繼續發酵的法院、檢察院員額制改革引發的入額問題,卻引發了不少法官、檢察官離職現象。據統計,C直轄市下的若干法院法官辦案年均量在300件以上,一些簡易案件庭法官,年審結量在數千件以上。
中國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法官之忙,蓋在于“一是訴訟驟增而帶來的“案件增加型負擔”,二是由于法院擔負其他非司法職能而形成的‘功能增加型負擔’”[3]同樣觀之,中國檢察官忙,一是檢察院法律監督性不斷擴張,擴編的部門占據了大量的辦案編制;二是許多人身為“檢察官”卻終身不辦案,無辦案經驗卻能指導辦案。從2015年一些試點省市的檢察改革中入額的檢察官來看,讓“入額檢察官多辦案、辦大案”可能僅僅是一口號而已。入額的人員大多是有職務的老資格檢察員。檢察官助理辦案仍然與改革前助理檢察員獨立辦案情況一樣。據實證訪談C市YB區、YZ區兩大主城區的法院、檢察官工作人員,“年輕人辦案是主力”“老同志有經驗”“年輕人反應快、動手能力強”等語錄需要深刻咀嚼。年輕人作為開展工作的主力,再讓其在繁重的辦案之余投入繁復、細致的需要上下溝通的工作中,其積極性可想而知。
(二)基于榮譽回報等視角的生成主體積極性考察
如前所述,不論是由哪一個推薦主體推薦的案例,最終落實具體申報案例工作的都是原辦案的檢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員。這一規定有兩種意味:一是如果原辦案法院、檢察院在司法業務上具有較強競爭力,那干得好,等于干得多;二是如果原辦案法院、檢察院在司法業務上不具有較強競爭力,那干得多,不一定干得好。這是一個兩難命題。實證訪談中,到了一定年齡、職務的法、檢人員才會吐露真情:“何必那么累!”因此,原辦案的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人員積極性如何,應當細細考究。
在具體的激勵或獎勵工作機制方面,報送和推薦指導性案例也并無較大的榮譽激勵。基本上,全國各地的指導性案例申報均依行政化力量讓下級院定期報送[4]。《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參考性案例工作的意見(試行)》第十八條規定,“各級法院應將案例的報道和推薦納入崗位目標考核。經確認和通報為參閱案例的,評優評先時,優先予以考慮”。其他一些省市的激勵方式也大多如此。據此,我們實證訪談了法院、檢察院的相關同志,下面一些訪談實錄,大體也能反饋主體的積極性,如“案例如果有幸最終被最高人民法院選入,自己雖然有一定的回報,但遠不如推薦人獲得的回報大。如果體制外的人推薦,這種回報落差可能更大”,如“最大榮譽莫過于年終評優的時候多了一條,但最終還不一定能被評為優秀”,再如“院里的工作太多了,誰會記得這一文字工作。而且,相比于院內其他工作,這種工作成功率太低,付出卻太多”。既然如此,那相較于基層檢察院、法院的檢察官、法官,其他社會各界人士撰寫指導性案例的積極性如何?“雖然各個社會主體的推薦意愿非常高,但實踐中,參與編寫案例、推薦案例的情況極為罕見,甚至可以說,這一社會參與推薦指導性案例的機制完全淪為虛置裝置。”[5]在實證調研中,據接觸到的C直轄市負責指導性案例上報的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透露,至今尚未收到一例案例是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律師等社會各界人士推薦的。
(三)四級法院、檢察院之間業務均衡性的考量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80%的案件在基層,80%的司法人員在基層。基層法院、檢察院與上級法院、檢察院之間的業務量屬于明顯的倒三角關系。實證訪談中,基層院與中級院、高級院之間相互各有表揚(表揚系場面話,先揚后抑,也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但最后落腳點卻是對彼此各有微詞。基層法院、檢察院的同志認為“我們每天辦案件很忙,沒有時間去整案例”“編寫案例、推薦案例工作聽著挺好,實際工作中誰會看?還有,與上面人員溝通太難,說不清”“每溝通一次,就是給自己找活、增加任務一次,他們不辦案件,有的是時間,為什么不去寫”“就知道讓我們下級院的寫,我們寫好之后,他們一個字不改”。省級院的同志認為“這些案子我們不清楚,他們辦理的當然由他們具體寫作更合適”“我們的工作量很大,要對口溝通下面那么多單位,打電話、發文件,還要再與上面溝通,哪里有時間去忙案例撰寫”“我們非常忙,哪里像他們想的那樣輕松”……基層院與高級院之間各有各的忙,在基層院的觀察中,高級院就是打電話、發文件,向下面攤派任務,自己不動手;高級院的人員那么多、部門那么多,就沒有實際干活的人。而在高級院的觀察中,基層院就會審點案子,寫個東西都不會;就會在審點案子之外去應酬,不去鉆研一下業務能力提升。
客觀而言,基層院審案直接與案件當事人打交道。案件辦理中,與外部人打交道比與內部人打交道,可能更辛苦。在各種報道中,被當事人襲擊的基本均是基層院法官、檢察官;因工作勞累而病倒在崗位上的也是基層院法院、檢察官居多。高級院雖然不參與或很少參與案件審理,但仍然承擔一定的工作量。這些工作大多屬于上下溝通的、轉達性、指導性工作。應當明確,業務量與工作量雖然不直接成正比關系,但很明顯成立正相關關系。下級院既有工作量也有業務量。高級院只有工作量,而且高級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在工作方式上確實可以假借基層院更熟悉辦案業務而將工作直接轉交下級。如果以業務量作為衡量標準,顯然基層院更加繁忙;如里以工作量為標準,二者之間還真難以說清,因為審判工作與溝通工作間不具有客觀的可等價性。但總體而言,二者之間繁忙程度是向基層院傾斜的。*這一點從每年的公務員招考中可以看出,為什么報考法院、檢察院的考生中,有更多的考生愿意選擇級別較高的法院、檢察院作為應聘單位。除了級別高、待遇好、環境好之外,工作相對輕松也是不爭事實。
四、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主體對案件質量數量的博弈
自2010年兩高發布 《高檢規定》《高法規定》時至2016年,最高檢發布了七批共計27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了十二批共計60個指導性案例,其總量并不多,年均發布量也不多,但這87個指導性案例成功入選背后落選的數量有多少,值得我們發掘。
指導性案例在實際工作中實行層層推薦、層層選拔方式。基層檢察院、法院是目前87個指導性案例的重要來源,甚至可以說是唯一來源。根據當前法院區劃與行政區劃重疊或者說一樣的狀況,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共有直轄市、省、自治區等省級行政區劃單位32個(若加上2個特別行政區,共計34個),地級市286個、地區14個,自治州30個、盟3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共計33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2853個(其中市轄區872個、縣級市368個、縣1442個、自治縣117個、旗49個、自治旗3個、特區1個、林區1個)。據此,大概有3171個不同層級法院,3171個不同層級檢察院(若加上林區、鐵路運輸等特設法院、檢察院數量可能更多)。每個基層法院、檢察院,根據內部工作要求,要推薦上一年度辦結案件中的兩至三個認為符合條件的案例,作為備選層層上報。粗略統計,每年共有6324—9531個案件進入檢察機關指導性案例備選庫,也有6324—9531個案件進入法院指導性案例備選庫。據此,從6324—9531個案例中,法院、檢察院每次各選出4—5個案件,基本上可以認為呈現出了“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景象。在這一現象中,基層檢察院、法院如何對待每一次選拔活動?又是誰參與并決定這些案件的質量評價?
(一)基層院主體的質量為主或數量為主取向
在一些基層辦案單位的申報過程中,基本上有兩種思維:一是質量抵數量;二是數量換質量。質量抵數量,是指以自認為案件本身質量較高,具有“社會廣泛關注的、典型性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等特征,認為本院所推薦的案例具有大概率上榜度,因此,只報一個。數量換質量,是指自認為每個案件都具有較高質量,但又不是特別高,上榜的可能性存在,但大概率不能保證,那只能多報送一點,“報那么多,總會中一個吧”。在質量與數量的選擇中,案例本身的指導性、真實價值多有喪失。尤其是在數量為主的思維中,一些實務工作者認為“報送、推薦就是完成任務而已,反正上級院有自己意見”。這一思維反映了基層院對上級院工作方式的某種態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加強案例指導工作的實施意見》第二十九條規定,“改進省法院各審判業務部門的案例考核制度,年度崗位目標管理考核設定統一的基本任務分,不以報送數量作為考核標準,報送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法院案例選》《中國審判案例要覽》采用的,按照相關考核規定加分,該加分不設上限,各中、基層法院考核案例工作也應體現相同導向”。以質量作為各級辦案單位報送指導性案例的導向成為一種潮流。但質量決定權歸屬于誰?基層院法官、檢察官可能會因質量決定權受制于人而影響自身的工作積極性。
(二)質量決定權在誰——主體性的喪失
由于整個案件實行的是層層遴選制度、層層把關工作機制,這樣的工作方式中存在兩大傾向:一是省市級擠壓下級效應,比如省市級檢察院、法院如果親自辦理過一些案件,會點名讓下級檢察院、法院報送特定案例,如果下級檢察院、法院本欲推薦或上報此案件,倒也相安無事;如果下級檢察院、法院本不愿意推薦此案例,就會在層級院之間產生認識爭議。遇到這種情況,下級法院往往只能硬著頭皮,完成上級指令。實務者認為“畢竟上級院才是真正的決定者,報了其他的上去,吃力不討好”“上級院點名,肯定意味著這個案例要推薦到最高院了,即便最后中不了最高院,完成省級任務也很重要”。再如省市級檢察院、法院如果親自辦理過一些案件,省級院要上報最高院特定案例,不過下級院又上報了很多案例,質量也不錯,比較符合指導性案例的若干條件,但是,最高院預留給各省級院的總數量有限,省市級院為了本級院的一些工作,可能犧牲掉下級院中具有較好指導性意義的案例。二是省級與下級信息不對稱機制,使得真正符合指導性案例條件的案件被淹沒在海量案件中。在省級檢察院、法院收集到的一些報送案件中,有些是下級院精心準備的,確實也比較符合“社會廣泛關注的、典型性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但在“標題、關鍵詞、基本案情、訴訟過程、要旨、法理分析、相關法律規定等”文字表達上差強人意,換言之,形式意義與實質意義因上下級院之間信息不對稱而產生沖突,上級院更愿意優先選取形式意義上的完備者。畢竟實質意義上的指導性,難以明確。
據此,由于這種數量質量間沖突與選擇、質量決定權完全由上級院說了算的狀況,即使后續選出了指導性案例,其本身的固有價值也因層層遴選中的主體選擇權、決定權分散而被掩蓋。換言之,質量不再是關鍵,完成工作的形式價值是第一位的。
五、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中標準確定對主體性的影響
俗語有云“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申報或推薦指導性案例者必須有對案件之所以能被申報的深刻認識,只有意識到自己的案例具有特殊性、價值性,有相較于其他案件的優勢才會付諸行動。申請人憑何認定自己的案例具有上述特性,換言之,案例成為“金剛鉆”的原因何在必須有其標準。根據“兩高”的《高檢規定》《高法規定》,檢察機關“指導性案例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案件處理結果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二)案件辦理具有良好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三)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政策掌握等方面對辦理類似案件具有指導意義”。法院的指導性案例為“裁判已經發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條件的案例:(一)社會廣泛關注的;(二)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三)具有典型性的;(四)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五)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二者相較,檢察指導性案例標準抽象、但邏輯設計上存在瑕疵;法院指導性案例的標準更具層次性,也更具有抽象性。
在現代網絡化、信息化社會,最有指導價值的案例應當是一段時間內社會關注度較高、爭議較大、全民參與討論的案例。這些案件判決的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等才是指導性適用的焦點。以近幾年信息化社會中關注度較高的幾個案例而言,“許霆盜竊案”“梁麗機場撿金案”“杭州駕車七十碼”“三鹿奶粉案”等等均屬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社會廣泛關注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的、具有典型性的、疑難復雜或者新類型的、其他具有指導作用的案例”。但從最高檢發布的27個案例、最高法發布的9個刑事案例來看,這些重大影響力案件無一上榜。難怪批評意見認為:“指導性案例遴選人不是‘正向’利用自然淘汰選結果,而是小心翼翼地避開已公開案例,獨辟蹊徑,另尋‘遺珠’。這種工作思路既沒有效率,也難以保證指導效果。”[6]從司法改革的方向來看,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揭示了一直以來中國刑事司法工作遵循的行政化管控現實,“也意味著中國的指導性案例在生成過程上也遵循了行政化管控。使其在生成過程堅持的是一種組織化邏輯……指導效力的約束機制都流露著極強的行政權運作邏輯的色彩”[7]。也使得“兩高”在選擇指導性案例時,都過于注重從體現當下政治意義的角度選擇指導性案例[8]。
在已經發布的指導性刑事案例中,從實務部門的反饋中,可以得知利用率并不高。綜上認為,其原因關鍵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誰做實做好基礎工作,做實做好基礎工作能獲得多少激勵;二是誰定的指導性案例標準、是誰判定案例成為指導性案例。這兩大關鍵問題在現實表現中均不盡如人意。將基礎性工作在實質意義上推由基層院承擔,但基層院沒有獲得實質的激勵,基層院各個工作主體缺乏足夠動力。而后續內部程序中的封閉性、壟斷性讓起點上多元性設想、貼近直接辦案者的設想,無法具體落實。因“我定的標準如何適用由我來判”,在標準意義上,上級院行政權力管控又否定了指導性案件內在生成的動力。正因如此,在如此生成機制上遴選出的指導性案例,從長遠來看,其生命力與指導性值得擔憂。
[1]張先明.用好用活指導性案例 努力實現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負責人就案例指導制度答記者問[N].人民法院報.2011-12-21.
[2]王杰兵,王瑩.案例指導制度的建立對法官角色定位的影響[EB/OL]. http://jsjy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3/id/1222247.shtml. 2016-6-1.
[3]姜峰.法院“案多人少”與國家治道變革——轉型時期中國的政治與司法憂思[J]. 政法論壇,2015(2):25-37.[4]孫光寧. 案例指導的激勵方式:從推薦到適用[J]. 東方法學. 2016(3):27.
[5]段陸平. 指導性案例社會推薦模式初論[J]. 社會科學研究. 2012(5):107.
[6]湯文平. 論指導性案例之文本剪輯——尤以指導案例1號為例[J]. 法制與社會發展. 2013(2):47-56.
[7]鄭智航. 中國指導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邏輯——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為分析對象[J].當代法學. 2015(4):125.
[8]楊雄. 刑事案例指導制度之發展與完善[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2012(1):29-35.
(責任編輯:付傳軍)
An Investigation of Subjectivity on the Formation of Criminal Guiding Ca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Judicial Officers in C Municipality
FAN Hua-zh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How a man realizes his subjectivity determines his work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social work. Although there exists the multiple subject design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riminal guiding cases, it cannot cover up the fact that only a single subject has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chanism. The judge and prosecutor of the original case handling unit are the men who actually submit or recommend the criminal guiding cases. Ye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pay a lot but get little back, which leads to the whole guiding case work mechanism working in low effectiveness. They will get further loss of their subjectivity for the standard of criminal guidance is determined by their uppe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Comparatively speaking, with regard to research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man in the guiding case generative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anecdotal information,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positive publicity, is much more credible. So the vitality and its true value of guiding case is worthy of worrying about in the long run.
criminal guiding cases; main generative body; enthusiasm of the body; cases quality; cases number
2016-12-17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青年項目“刑事指導性案例生成機制研究——以重慶市指導性案例生成實踐為樣本”(2015QNFX30)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樊華中(1984— ),男,江蘇泗陽人,西南政法大學2014級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D926
A
1008-2433(2017)02-00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