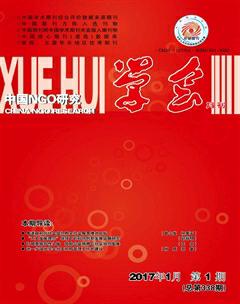粵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wù)模式比較
曾令發(fā)+楊愛平


[摘 要]上世紀(jì)70年代的結(jié)社革命使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wù)的意愿不斷增強(qiáng),而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則為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治理提供廣闊的空間。作為發(fā)達(dá)地區(qū)的香港已經(jīng)形成較為成熟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wù)的模式,并成為廣東省學(xué)習(xí)的對象。本文通過比較廣東省與香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的流程、機(jī)制、資金以及相關(guān)制度,發(fā)現(xiàn)廣東省已經(jīng)初步建立起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wù)的模式,但是政府購買社會服務(wù)的制度還缺乏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對社會服務(wù)的質(zhì)量評估與監(jiān)察不夠,社會組織還缺乏獨(dú)立性,因此對于廣東省來說,完善政府購買社會服務(wù)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關(guān)鍵詞]社會組織 政府購買 社會服務(wù)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一場有組織的志愿運(yùn)動和創(chuàng)建各種私人的、非營利的及非政府的組織的運(yùn)動正成為席卷全球的最引人注目的運(yùn)動。從北美、歐亞的發(fā)達(dá)國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蘇聯(lián)集團(tuán)的發(fā)展中,社會民眾正在創(chuàng)建各種團(tuán)體、基金會和類似組織去提供人道服務(wù),促進(jìn)基層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防止環(huán)境退化,保障公民權(quán)利,以及成百上千先前無人關(guān)注的或由國家承擔(dān)的種種目標(biāo)[1]。在我國,由于市場經(jīng)濟(jì)的推進(jìn)和政府職能的轉(zhuǎn)變,社會組織也開始參與到公共服務(wù)之中來。2003 年以來,上海、北京、廣東、江蘇、浙江等地方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wù)的探索不斷增多,形式多樣,購買的領(lǐng)域涉及教育、公共衛(wèi)生、扶貧、養(yǎng)老、殘疾人服務(wù)等傳統(tǒng)服務(wù),還包括社會工作、社區(qū)發(fā)展、社區(qū)矯正、環(huán)境保護(hù)等諸多新型社會需求 [2]。為了貫徹落實(shí)《珠三角地區(qū)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08—2020年)》,2008年8月,“借鑒香港經(jīng)驗(yàn),推進(jìn)社會管理綜合改革試點(diǎn)” 列入廣東的重點(diǎn)改革項(xiàng)目,由廣州、深圳、珠海市政府明確牽頭負(fù)責(zé)推進(jìn),移植香港經(jīng)濟(jì)管理、社會管理和城市管理方面的成熟經(jīng)驗(yàn),政府向社會組織轉(zhuǎn)移有關(guān)職能正式登上議事日程。
香港由于長期受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因此采取 “小政府、大社會”的傳統(tǒng)自由市場經(jīng)濟(jì)的管理模式,一方面香港政府將其角色定位為中心主軸,同時也賦予社會組織自治性的施政策略。政府主要是制定政策以及監(jiān)管,而社會福利則是通過“官助民辦”的方式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guān)系。廣東省社會組織的發(fā)展相對較慢,在2008年后,隨著政府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一批社會組織逐步成長起來,并開始從政府中承接一些社會管理和服務(wù)職能。那么經(jīng)過這幾年的摸索,廣東省和香港政府在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wù)模式上存在著哪些不同?這對于我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有哪些啟示?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政府購買社會服務(wù)的流程
香港社會組織承擔(dān)政府職能主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開始,但有規(guī)劃地承擔(dān)政府職能是從上世紀(jì)60年代開始的。1965年,香港政府制定了第一部社會福利白皮書——《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與目標(biāo)》,社會組織開始有規(guī)劃地參與到社會服務(wù)的供給之中。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香港政府與社會組織在社會福利的供給中分工明確,操作規(guī)范,政府負(fù)責(zé)制定社會福利政策。1973年,香港政府又出臺《香港福利未來發(fā)展計(jì)劃》,1977年制定了《群策群力協(xié)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書》、1979年出臺《進(jìn)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1991年出臺《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而具體操作是由香港社會福利署在根據(jù)社會組織提出的需求和建議以及香港社會福利發(fā)展的具體要求向立法會提出申請,立法會根據(jù)社會福利署的申請,在吸納香港社會服務(wù)聯(lián)會和社會工作人員協(xié)會和總工會的政策建議向社會福利署撥款。社會組織向社會福利署提出服務(wù)申請并獲得政府資助,同時接受社會福利署的監(jiān)督,社會組織還可以從公益基金會中獲取資金資助。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wù)時以專業(yè)的社工為主,輔以義工,同時社會工作人員協(xié)會和總工會一方面要求社會組織成員在提供社會服務(wù)過程中遵守職業(yè)操守;另一方面也起到權(quán)益保護(hù)的作用。香港社會福利服務(wù)的提供是圍繞著立法會、社會福利署、社會組織、公益基金會、社會服務(wù)聯(lián)會、社會工作者和服務(wù)使用者展開,具體見圖1。
根據(jù)2012年頒布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暫行辦法》,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有著嚴(yán)格的程序。第一,財(cái)政部門負(fù)責(zé)建立健全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制度,制訂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目錄,監(jiān)督、指導(dǎo)各類購買主體依法開展購買服務(wù)工作,牽頭做好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的資金管理、監(jiān)督檢查和績效評價等工作。第二,機(jī)構(gòu)編制部門負(fù)責(zé)制訂政府轉(zhuǎn)移職能目錄,明確政府職能轉(zhuǎn)移事項(xiàng)。第三,發(fā)展改革部門負(fù)責(zé)會同有關(guān)部門編制和實(shí)施政府投資計(jì)劃,推動政府投資項(xiàng)目列入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計(jì)劃。第四,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核實(shí)作為服務(wù)供應(yīng)方的社會組織的資質(zhì)及相關(guān)條件,參與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績效評價。第五,監(jiān)察部門負(fù)責(zé)對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工作進(jìn)行監(jiān)督,參與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績效評價。第六,審計(jì)部門負(fù)責(zé)對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資金的使用情況進(jìn)行審計(jì)監(jiān)督,參與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績效評價。第七,購買主體負(fù)責(zé)購買服務(wù)的具體組織實(shí)施,對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wù)進(jìn)行跟蹤監(jiān)督,在項(xiàng)目完成后組織考核評估和驗(yàn)收。
三、政府購買社會服務(wù)的機(jī)制
香港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在社會福利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社會服務(wù)的方式進(jìn)行。廣東在2008年后也在珠三角等城市開始推行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推動社會福利。
(一)撥款機(jī)制
在2001年以前,香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wù)的模式主要有四種,即修訂標(biāo)準(zhǔn)成本模式、模擬成本資助模式、單位資助模式和整筆撥款資助模式。前兩種模式占80%。每個津助服務(wù)都有一套認(rèn)可人手編制,列明職位、職級、入職條件、薪酬,職級、入職條件、薪酬與公務(wù)員相同(沒有公務(wù)員的附帶福利),基本體現(xiàn)了同工同酬[4],這兩種模式就是實(shí)行實(shí)報(bào)實(shí)銷的方式資助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wù)。2001年開始,香港政府開始推行整筆撥款的方式購買社會服務(wù),即不再就其具體從業(yè)人員情況進(jìn)行區(qū)別對待,而是根據(jù)其服務(wù)的內(nèi)容確定資助金額,并且以一次性撥款的方式向社會組織發(fā)放,社會組織根據(jù)《津貼與服務(wù)協(xié)議》來自由支配資金。在一個資助周期內(nèi)(一般是5年),受資助的社會組織可以根據(jù)本機(jī)構(gòu)內(nèi)部的需要調(diào)配整筆撥款所提供的資金,只要能夠確保這些重新調(diào)配符合政府規(guī)定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