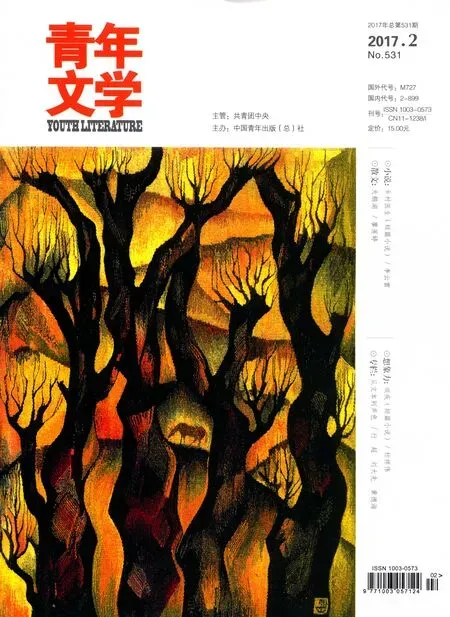是到裝抽水馬桶的時候了
⊙ 文 / 林曉哲
是到裝抽水馬桶的時候了
⊙ 文 / 林曉哲
林曉哲:一九八〇年出生,浙江樂清人,在《青年文學》《上海文學》《文學界》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有作品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曾獲《上海文學》新人獎。
一開始,我以為他是一個不易接近的男人。在我第一次來到辦公室時,他甚至沒有抬頭看我一眼。
他的眼睛緊盯著電腦,不知道是在思考,還是僅僅在發愣。他的眼睛很大,眼袋很深,眼珠是小而灰的,這使它們看起來并不有神而有些渾濁。在我坐到他對面時,他仍然緊盯著電腦,微微皺了皺眉,點上一根煙,從人中兩側呼出兩道濃重的弧形煙柱,吸入兩個鼻孔。兩個鼻孔幾乎沒有漏出一丁點煙霧,只有從嘴巴抽出過濾嘴時才有少許滲出來。他顯得十分干瘦,像窗臺上枯萎的君子蘭一樣干瘦。他把煙灰彈在君子蘭的花盆里。他說出的第一句話不是對我的歡迎,而是詢問我的睡眠狀況。我說我的睡眠不差。然后他說在這樣一個科室里做事,經常失眠的人會更好一些。他的語氣里有一點挖苦或自嘲的意味。他又問我晚上通常會有什么安排。我敷衍了一句看書之類的話。他說這很好,他之前的搭檔就是因為有太多的夜生活才被他趕走的。他在說到“趕”字時加重了語氣,拉長了語調,隨即瞟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需要從我這里得到什么反饋。我木訥地點了點頭。他又問我到這樣一個科室做事有沒有心理準備。我不知道一個寫寫材料的地方需要什么心理準備。我又木訥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忽然把大半根香煙掐滅在花盆里,向我伸出手,在我伸出手時在我的手掌上重重地擊了一下,鄭重其事地宣布我們的合作開始了。好像我們此刻身處舞臺或新聞發布會一樣。
他在這個地方的機關有著不小的名聲。他的名聲來自于“材料”——這是機關各類公文的通稱。我翻閱過他幾年來各種體式的材料。他的材料與通常的公文模式不同。他的材料里極少套話和官話,有時甚至會流露出一份情感。這份情感出現在不同的領導、專家、黨員、農民和企業家身上。他好像可以隨心所欲地成為他們中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人群,為他們中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人群代言。從這一點上,說他的材料抵達了道家的境界也不為過。事實上,我也多少知道他有那么一點道家的做派。他原先就在我剛剛離開的鄉鎮。在我來到那個鄉鎮時,他恰好調離,騰出來的宿舍就成了我的宿舍。在那個宿舍里,他撕毀了許多張毛邊紙和宣紙。他把它們揉搓成一團,丟棄在陽臺上。這使我得以見到他各種體式的書法。如果有落款,落款必定是“池道人”——他單名一個“池”字。在被丟棄的毛邊紙和宣紙中間,我還發現過一封情書。這封情書也是被撕毀的,我用了一個夜晚的時間才大致拼接成功。我當時很驚奇自己會對一個陌生男人懷有一份如此綿長的耐心。現在我明白了。與其說那是一封情書,倒不如說是一次通牒。他告訴她如果無法理解他目前的狀態,無法接受他不會離開鄉鎮的事實,他將不會挽留她,不會挽留他們的感情。這封情書(或者說通牒)沒有帶上一絲情感,連稱呼也是用了全稱——夏未雪。
在這樣一個科室里,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寫材料,不停地寫各種體式的材料。我們辦公室的門總是關著的,有時甚至需要倒鎖。在門外的走廊上,越來越多的時候聚集著上訪的人群。那一張張義憤填膺或者楚楚可憐的臉,有時會錯誤地占領我們的辦公室。它們時常讓我心神不寧,而他從未理會過它們。通常,他都是斜睨一眼,徑直走出了辦公室,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可以去什么地方。有一次,我也沖破了那些臉龐的封鎖,我也跟著他走出了辦公室。他回頭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一下子忘記了自己該去什么地方。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才得知他去了什么地方。那是在廁所里,我聽到了一陣熟悉的咳嗽聲,接著聞到一股煙味。撒完尿后我就沒有打算離開廁所。我打開水龍頭,站在洗手臺前一次次搓手,幾乎搓破了一層皮。足足十分鐘后,他才銜著一根煙走出來。
我不失時機地詭笑了一聲說:“你是不是便秘了?”
他怔了一下說:“便秘有助耳根清靜。”
只有一次,他沒有走出辦公室。那一次,我非常意外地聽到了一句中年女人的問候:“您好!”中年女人穿著一件干凈的碎花格子的確良襯衫。眼神里流露出一種不會讓人產生不安的淡淡的憂愁。很難說清楚是中年女人的問候還是裝扮還是眼神觸動了他。他一下子斷定中年女人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她可以成為他某個材料的主角。或者說,他可以為她代言。事實也是如此,現在,已經有許多人知道女村支書劉大娟的先進事跡了。但是,在那個時刻,女村支書還只是一個尋求村干部補助的上訪人。在女村支書身后的門口,站著一群前來為她做證的農村婦女。他一反常態地請女村支書坐下來,叫我泡了一杯茶。他向女村支書詢問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遠遠超出了村干部補助的范疇。大門敞開著,站在門口的農村婦女安靜地簇擁在門口,認真地傾聽著女村支書漫長的也是苦難的敘述。她的敘述貫穿四十余年。
她說她曾經是一個營長的女兒,她的雙親在那個特殊年代撒手人寰,她作為知識青年來到小山村時還是一個初中生,此后她再也沒有離開過小山村。她嫁給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農民早早離世,她徒手養大了三個子女,她的子女靠著外出打工過上了拮據的生活。現在,她也許只有最后一兩年時光了。她得了癌癥,癌細胞已經擴散……女村支書在訴說個人的苦難時是平靜的,娓娓道來的,只有說到為村里付出十八年時光時才激動了起來,好像所有的苦難都是為這一刻鋪墊的。她說她原本不想麻煩組織,但是她實在難以忍受鄉鎮無休止地拖延了——那樣會拖到她死的。女村支書以明顯的顫音發出“死”字,使死亡的凄厲瞬間呈現在眼前。女村支書一眨不眨地望著他,眼神里的憂愁和淡然都不見了,只留下哀求。她身后的門口,那群農村婦女泣不成聲。
我在這里只是截取了女村支書敘述中最精要的部分。事實上女村支書的敘述枝繁葉茂,甚至觸及每一片樹葉的葉脈。我的記錄長達數十頁。這完全是拜他所賜。一開始,他就提醒我要原汁原味詳加記錄。他在女村支書的敘述中像一個調查記者一樣穿針引線,引導女村支書一步步陷入歷史的深處和細部。他答應女村支書會盡快辦理補助事宜。當看出她心存疑慮時,他無所顧忌地承諾了五天的期限:“五天之內,我就會把好消息帶給你。”——他的信口開河嚇了我一跳。他完全不計后果。他忘記了他的職責和村干部補助是完全搭不上邊的。我原本以為是女村支書的敘述感染了他。但是在送別女村支書之后,他迫不及待做的第一件事情,卻是在墻上的地圖尋找那座小山村。他終于找到它的位置。
他指著一圈棕褐色,亢奮地對我說:“你看,確實非常偏遠!”

⊙ 陳 雨·博爾赫斯
他接過我十數頁的記錄認真地看了起來。他很快羅列出一個寫作提綱。我用一個不眠之夜完成了這份后來帶來極大反響的材料的初稿。第二天一早,他改變了思路。他告訴我在落筆之前,應該多看看墻上的地圖,進入地圖上某個實在的場景,想象自己正在和那里的人交談。“只有土生土長的聲音才是一份材料可信的證言。”他的語氣里仍然帶著點挖苦或自嘲的意味,使我難以判斷是否應該聽從他的教導。我付出了第二個不眠之夜。第三天一早,他開始自己修改。他用原子筆在我的材料上進行密密麻麻的修改。我陪他度過了第三個不眠之夜。第四天一早,他把材料送給領導。他在領導的辦公室待了很長時間,之后把領導改動幾個字的材料遞給我,讓我在電腦上做最后的修改。
之后,他撥了一個電話給女村支書。他告訴女村支書她的事情已經辦妥。他抿了一口茶,點上一根煙,目光瞥向窗外。他一下子陷入了萬籟俱寂的狀態。即使我很快輸出定稿,也不好意思去打擾他。我拾掇起那一摞厚厚的廢稿,準備扔到垃圾桶。他突然轉過頭,制止我說:“不要扔,對照著看看,想想下回怎么寫好。”接著,他取走我手中的定稿,沒有再瞄上一眼,而是背對文字的一面卷起來,離開了辦公室。
這份材料之所以帶來很大的反響,是因為得到了一位省級重要領導的批示。省級重要領導的職級,即使對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而言也太大了。這里,姑且用“首長”一詞來指代省級重要領導——她寫下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批示。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在誦讀完首長的批示后笑逐顏開。他陶醉的神色很容易讓人以為他為之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但是他接下去的顫音卻未能連帶出激動的淚水。事實上我們的這個領導還是落下了淚水。我們很快收到首長的第二次批示。首長決定親自到小山村探望這位罹患絕癥的女村支書。我們單位的領導就是在誦讀首長第二次批示的時候,落下了激動的淚水。
相比之下,他比我們的領導冷靜得多了。在回到辦公室后,他無聲無息地坐了下來,眼睛緊盯著電腦,點上一根煙。他問我是否清楚接下去該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們在大獲成功之后,還應該做什么。難道我們現在該回家睡覺去嗎?我想。
他把一臺筆記本電腦裝入一個碩大的公文包,說道:“是到走出辦公室的時候了。”
我們動身前往那座陌生的小山村。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去往辦公室之外的地方。在路上,我和他談起我們曾經共同工作和生活過的鄉鎮和共同的宿舍。他對此毫無興趣。他說他在離開鄉鎮后就沒有再和那里的人聯系過。他提醒我抓緊時間整理訪談女村支書的思路。他瞥向車窗外,漫不經心地說:“我們很可能要為她寫一本書。”這句話讓我直冒冷汗。我想我的前任可能不是被他趕走,而是主動請辭,據說此人后來去了檔案局,從此不再過問江湖上的事。我們的小車駛入一段螺旋式上升的盤山公路,穿越了一段相對平緩的山坡,接著又展開了一段螺旋式上升的盤山公路。一個小時后,我們終于看到了在路邊翹首以待的女村支書。但是離終點還有一段距離。我們把車停靠在路邊,跟隨女村支書進入一條泥濘的山路。
女村支書一直錯愕地打量著我們,絮叨著那個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人來干什么。他寬慰女村支書說是她的事跡而不是上訪驚動了首長,她將成為首長到任后第一個探望的村支部書記。他寬慰她說首長的到訪就像電視上看到的場景一樣,所有流程都會事先設計,她不必擔心什么。他寬慰她說我們會為她安排一切,包括對白。他挽著村支書走著,語氣平緩,語調柔和,讓人倍感親切。接著,他話鋒一轉說:“鄭書記,首長非常感動,她很期待知道您更多的事情。我們也很期待。”
女村支書狐疑不定地注視著他,語無倫次地說:“謝謝你幫助我解決了補助的問題。”女村支書反復重說這句話,如果不加以阻止,她也許會一直重復下去。
他不容置疑地說:“不要這么說,是我們應該感謝你才對。”
但是,我們在抵達女村支書的石頭屋后就發現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這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女村支書漫長的敘述里隱瞞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她是一個基督徒。我們抬頭看到了大門上正中的鮮紅十字架。我們忽然明白了,上訪當日站在門口的一群婦女之所以十指交叉,不是出于緊張,而是正在祈禱。我們在十字架下面面相覷。女村支書尷尬地解釋說十字架是她已故的丈夫漆上去的,他在病危之際皈依了耶穌。女村支書沒有再違心地說下去,而是敦請我們到里屋坐坐。女村支書朝廚房疾步走去,接著端出一個開水瓶和兩個茶杯。我隨即步入女村支書的房子。我想這不是我應該也不是我可以解決的問題。我瞥了他一眼。他站在原地一動不動。
內外光線強烈的對比使我只能看見他的剪影。他面對黑暗的思考很快有了眉目。他沒有接過女村支書遞過來的茶杯,而是問女村支書家里有沒有紅紙。女村支書在家里馬虎地翻了一下就沖出了房子,她開始挨家挨戶地詢問和尋找,最終一無所獲。接著他給小山村所在鄉鎮的主要領導撥了一個電話。他提醒沒有必要讓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為此擔心。“木已成舟!”他強調道。他掛斷電話,囑咐我明天一早就去買幾張紅紙。他的包容——我實在找不出其他更適合的詞語——使女村支書大為感動。她坦言家里還有一些與耶穌有關的物品,她會盡快轉移。他終于緩步步入房子。但是我們接下去與女村支書的交談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女村支書幾乎沒有說出一句有切實內容的話來。是那個該死的十字架把女村支書連接記憶的線路給切斷了。我們敗興而歸。在返回的路上,我們接到了單位領導的電話。
單位領導得知我們的行蹤后表揚了我們,隨后對我們說:“首長將在四天后到訪。”
他說:“看來,今晚就要把對聯貼上去。”
我們繼續返城,在一家書畫店購買了紙筆。即使如此形色匆忙,他居然也沒有忘記開具發票。我們攜帶著紙筆和發票,馬不停蹄地趕回女村支書的家。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女村支書家正間一盞昏黃的白熾燈亮了起來。飯桌上的剩菜被騰挪到廚房。他將紅紙平鋪在飯桌上。他寫下一副十分俗氣的聯句和橫批。他在運筆時皺了好幾次眉,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他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耐心,甚至產生了一絲厭惡。他徑自走出正間。我納悶的是,他為什么不去買一副寫好的對聯。
不知道是蓄謀已久,還是屋檐下一只黝黑煤球爐的提醒,他斜乜了一眼就大踏步回到了正間。是的,他啟動了一道復雜的工序。他要將對聯迅速做舊。他讓女村支書煮了一水壺茶葉水。他默默地守在煤球爐邊上等待茶水沸騰,接著將沸騰的茶水倒入一個臉盆。茶水冷卻之后,他雙手端起臉盆,滿滿地灌上一口茶葉水,在嘴巴里攪拌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噴灑在對聯上。如此反復數次。但是效果不佳,他好像又失去了耐心,索性將整副對聯浸入茶葉水捋了一遍,接著平鋪到院子里。他隨便撿拾了幾塊石子壓在對聯的上面。
漫長的等待讓我越發覺得無聊。我想他已經忘記我的存在。我心里對他說:“如果沒什么事的話,我先回家啦。”但是我嘴里還是說:“馮主任真是有辦法!”
他朝我看了一眼。我想他的臉上大概又浮現出了挖苦或自嘲的神情。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了幾聲狗吠。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沿著狗吠聲疾步走出了院子。我也跟著他走出了院子。他回頭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接著在一片小竹林里停住腳步。他徑自拉開褲鏈尿了一泡。我也尿了一泡。小竹林里隨即發出清脆的嘀嘀嗒嗒的聲響。他的神經終于松弛了下來。他對我說有很多年沒有機會露天撒尿了。他告訴我他童年時常常和小伙伴們一起比賽撒尿,看誰撒得更遠一些。他曾經是一個撒尿高手。他告訴我直到高二他才第一次坐上抽水馬桶,那是在他城里的叔叔家里,他沒有翻下馬桶圈就坐上了抽水馬桶,雙腿沾上了留在馬桶唇上的小便。
“那時我根本不知道馬桶蓋里還有個馬桶圈。”他說,“我連沖水按鈕也找不到,舀了好幾勺水才沖干凈。”
我賠笑著,我從來沒關心過一個抽水馬桶會有如此復雜的構造。我慶幸我們能以這樣特殊的方式稍稍拉近距離。
他把沒有洗過的手搭在我肩上,說:“這樣的經歷,你們城里人沒法想象吧?”
對聯終于晾干了。顏色果然從锃亮的鮮紅變成陳舊的橙紅。十字架被橫批完整地遮掩住了。看起來一切非常完美。但是他還沒有離開的打算。他和女村支書又家長里短地聊了很長時間。他確實是一個不需要睡眠的人。就像一只鼯鼠,或者是狼,在夜晚捕獲的食物甚至超過白日。
第二天一早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就趕來了。單位領導再次表揚了我們。那時我們僅僅在車上靠了兩三個小時,之后就站在女村支書原來迎接我們的地方迎接他。單位領導帶來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包括我們單位的同事,以及小山村所在鄉鎮的干部。單位領導走到凹凸不平的山路時皺了皺眉。他向在場的人詢問了這幾天的天氣狀況。他振振有詞地問道:“你們有沒有信心,兩天之內把這條路修好?”
馬上得到肯定的答復。兩三個鄉鎮干部匆匆離開了現場。
單位領導一邊走著,一邊向在場的人詢問一些細節。他這時才發現,他和單位領導存在著關注點的偏差。他太專注于挖掘女村支書的故事了。他竟然疏忽了向女村支書交代單位領導幾年來的得意之作。這些得意之作中有幾項和農村是息息相關的,但是女村支書一無所知。單位領導突然流露不快的神色。單位領導瞥了他一眼——或許僅僅是因為他恰好處在最容易被瞥到的位置。他為此懊悔不已。他和我交換了一個眼色,暗示他無法原諒自己的疏忽。我則用眼神安慰他,那個最矮最胖的鄉鎮干部已經忙著解釋了。單位領導又恢復了和顏悅色。
這時龐大的隊伍走到了女村支書的家門口。單位領導看到那副對聯贊不絕口。他說:“這個好,農村嘛,就是要貼貼對聯,那股子味道就出來了。”
最矮最胖的鄉鎮干部轉過頭,對另一個戴眼鏡的瘦子吩咐道:“記著,家家戶戶都要貼上對聯。”
最矮最胖的鄉鎮干部說完搭住了他的肩膀。他們在一個隱蔽的時間里,彼此會心一笑。
單位領導走后,幾個鄉鎮干部留下來。我不知道他為什么也要留了下來。我們很忙。我們需要馬上準備女村支書會見首長的臺詞。但是他踅進一條山路走了上去。我感到他想甩開我而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他很快到了一個山頭。
他說:“我們原來的鄉鎮,就在對面那座山峰的后面。”
他試圖掩飾內心的激動,但不是很成功,我還是從他的語調里感受到微妙的變化。我們的對面不只是一座山峰。我們的對面是一座座連綿起伏的山峰。
我問:“是哪一座?”
他沒有回答我。他像是在尋找著什么。我擔心他要走到對面的山峰。他果然從山頭翻了下去,很快消失在叢林中。這一次我沒有跟著他下去。過了好一陣子他才回來。
他說:“我們回去吧。”
我問:“你是不是在找什么?”
他避開我的目光,說:“沒什么。”
次日下午,我們又來到小山村。我們震驚的是,一夜之間,那條泥濘的山路已經變成水泥路。修路工人橫七豎八地躺在草叢間。我們艱難地從他們身體的空隙跨過去。他說:“如果現在落場雨,無數臺烘干機一起勞作的場面一定十分壯觀。”他又帶上了挖苦或自嘲的語氣。
我們已經準備好女村支書會見首長的臺詞。他在女村支書家里待了一會兒就出去了。他叫我留了下來。我需要以首長的身份,充當女村支書的陪練。我和女村支書對了幾次臺詞后就沒有興致了。我納悶的是,這僻遠的山間究竟勾起了他什么回憶?
我問女村支書:“獨自一個人在山里頭走會不會有危險?”
女村支書說:“很容易迷路,去年里邊就困住了一隊人馬。”
我說:“他一定是一個人跑到山里頭去了。”
我沒有撥打他的手機。我對女村支書說他的手機沒有信號。他已經離開兩個多小時了。我向女村支書建議一起把他找回來。接著我跟隨女村支書踏上了昨天走過的山路。我告訴女村支書他極有可能是往對面的山峰去的。女村支書不由得緊張起來。女村支書說那一帶已經早就不能走人了。她加快了步伐。我不得不為謊言和好奇付出代價。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跟著她,腳步越發遲重。不久之后,山路果然消失了。我們的右側就是懸崖峭壁。
我們找到他的時候發現他正躺在一塊巖石上抽煙。那塊巖石的旁邊,有一個干涸的小池。他沒有注意到我們。及至我叫喚著他的名字,他才若無其事地瞟了我們一眼。他從巖石上跳了下來。他的眼神回避著我們。他主動對我們解釋他就是來尋找這一方小池的。他說他幾年前意外發現了它。他常常攀登至此,但是自從離開鄉鎮后,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他說他沒有想到它已經干涸了,如果他知道它已經干涸,他就不會上來了。
他在離開之前又回頭瞥了一眼那一方干涸的小池。返回的路上他一言不發。直到走出山路時,他才問起女村支書準備得怎么樣了。沒有等到回答,他就指責我說:“首長馬上就要來了,你不知道留給女村支書的時間不多了嗎?”
離首長到來只有最后一天了。
我們陪同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再次來到小山村。這次的到來就像是一場預演。水泥路修整完畢了,村里道路打掃得一干二凈,家家戶戶都貼上了對聯。一棵榕樹下的宣傳欄也更新了,一律換上單位領導的得意之作。單位領導頻頻點頭,向在場所有的人強調它們蘊含的理念。單位領導說:“你們的理解還不能說很到位。”
我和他跟在單位領導的隊伍的最后頭。我感到他比以往更加的沉默。我感到他時常抬頭望向那一段山路,那一座看不見的山峰,或者那一個干涸的小池。我感到他有一段重要的回憶落在那里。他急切地想把它撿回來。但是單位領導一直檢查到傍晚還沒有離開。單位領導一直在敦促大家考慮周全。直到進入小山村唯一的一座二層樓房子,單位領導還在嘮叨著什么。小山村所在鄉鎮的干部在這座房子里安排了晚餐。單位領導像品茶一樣呷了一口酒,告誡大家今晚只能小飲。但是場面還是失控了。場面是在一次次成功的試探中失控的,是在從女村支書為主角一步步轉變成單位領導為主角中失控的。那時候已經沒有人關心女村支書了,沒有人關心女村支書的眼淚為什么嘩嘩地落下來,沒有人關心女村支書的雙手和雙腳為什么猛烈地顫抖。所以當女村支書突然做出下跪的舉動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反應過來。女村支書再次聲明,她曾經是一個營長的女兒,幾十年來一直默默地守在小山村里。接著,女村支書說她現在什么心愿都沒有了,就希望她那不爭氣的小兒子不再四處漂泊。最后,女村支書亮出了她的底牌,她懇請單位領導為她的小兒子安排一份工作,哪怕是多么不起眼的一個小崗位。
小山村所在鄉鎮的干部終于清醒過來,他們團團圍住女村支書,安慰女村支書。單位領導就是這樣成功脫身的。單位領導臨行前還撂下一句話:“對鄭書記的要求,你們一定要妥善考慮。”這頓失控的晚餐就此結束。單位領導在走出二層樓房子時也聽到了幾聲狗吠。
單位領導提了提褲子,輕聲問道:“衛生間在哪里?”
沒有人回答。這時單位領導看見一個人正挺著腰桿站在院子的前面。單位領導會意地笑了一聲,朝那個挺著腰桿的人走去。
當單位領導一臉輕松地回來的時候,他,這個在酒桌上完全失蹤的人卻醒目地出現了。他貼近單位領導的身體,小心翼翼地說道:“首長是女人,要是她明天內急的話……”他沒有說完就停住了。單位領導愣了一下,一語未發。接著,他以一種不無焦慮又異常慎重的口吻說道:“我們是不是應該裝一只抽水馬桶?”
那個一直處在單位領導最近位置的最矮最胖的鄉鎮干部說:“現在恐怕來不及了吧?”
單位領導大聲喝道:“來不及也要來得及!首長要是內急,誰擔得起這個責任?”
一個小時后,施工工人趕到現場。他們將抽水馬桶安裝在二層樓房子的一間邊間里。他們遇到了一個技術難題,就是沒有排污管道可以連接。因此抽水馬桶只能直接排放到二層樓房子后門的陰溝里。我們單位最大的領導直到抽水馬桶安裝完畢才放心離開。他在離開之前又表揚了他。單位領導顯然不知道他對抽水馬桶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
首長終于來了。但是首長僅僅在小山村停留了一個小時。首長真是太忙了,當天就要飛往另一個地方參加一個重要會議。首長雙手緊握女村支書的畫面,被許多攝像機和照相機永久地記錄下來。那是后來我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的。事實上,在現場,我連首長的背影都沒有見到。為了能見首長一面,我守在二層樓房子的院子里。我多么期待首長能來用一回抽水馬桶。可是首長沒有來。首長短暫的停留使她沒有時間醞釀出一泡完整的尿來。于是我忐忑地決定,替代首長享用一下小山村唯一的抽水馬桶。當我興致勃勃地朝抽水馬桶走去的時候,他卻出現了。他帶來了一個記者模樣的女人。他們的表情十分淡漠,也可能是拘謹。他把記者模樣的女人帶入二層樓房子的邊間。我就這樣被這個女人捷足先登了。
她回到院子的時候,對我而不是對他莞爾一笑說:“馬桶是全新的?你們該不會是特意裝上去的吧?”
我馬上承認了。我看到他置身事外地低著頭。
她說:“不過,現在確實也是到該裝抽水馬桶的時候啦。”
我問:“你嗅覺這么敏銳,不會是記者吧?”
她“嗯”了一聲,爽朗地說:“省報記者夏未雪,你呢?”
我問:“你叫夏未雪?”
她說:“是啊,名字有點怪吧?”
他掏出一根煙,接著又掏出另一根遞給她。她徑自點上一根女士煙。他們就這樣離開了我的視線。即使首長離開之后他們也沒有再出現。所有人都陸續離開了。
小山村在一陣喧鬧之后又恢復了寧靜。我不知道為什么我會留下來。我不知道為什么我會相信他們還在這里。我不知道為什么我會涌起一股悲傷的情緒。我獨自走上那條通往山頭的小路。或許我聽到了他們的耳語聲。或許我只是聽到了風吹樹葉的聲音。我看到灰暗的天空出現一輪色彩極淺的圓月。我想我不應該在此刻呼喊他們的名字。
我走出山路,用了一回抽水馬桶,然后朝女村支書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