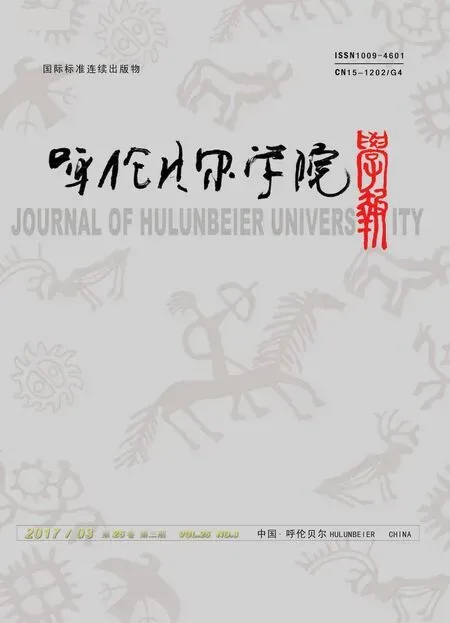《沙揚娜拉》的藝術符號學解讀
彭 柔
(吉林師范大學長春校區 吉林 長春 130000)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沉默是今晚的康橋。一想到徐志摩,就想到他的經典之作《再別康橋》。我們徜徉在詩人創造的康橋的美麗意境中,感受他的癡情與眷戀,苦澀與沉重,詩中充滿著對戀人的眷戀和失戀的痛苦,而《沙揚娜拉》是一首可以與《再別康橋》相媲美的現代小詩。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蜜甜的憂愁——沙揚娜拉!”[1]這首詩寫的語句清新,意境優美,很多學者在解讀這首小詩時,依據這首詩的標題《沙揚娜拉》(沙揚娜拉為日語,中文意思為再見),副標題“贈日本女郎”,以及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把這首詩理解為描寫的是詩人與日本友人離別時的場景,表現的是日本女性展露出來的嬌羞,含情脈脈的神態。從詩的寫作背景入手,采用一般性的普通的語言符號來解讀這首詩,顯然與這首詩的藝術形式、與詩人想表達的真正的情感相距甚遠。然而只有從詩的本身入手,用藝術符號學的方法解讀文學作品,才能真正的理解詩歌本身,理解作者想要抒發的感情。
一、藝術符號解讀的正確性
一般性的語言符號是對客觀事物的描繪,是對現實景物的再現,是對作家情感的敘述,具有通訊、傳遞等功能。一般性語言符號的作用就是傳遞信息,指代事物,并沒有摻雜敘述者多余的情感,它有別于藝術符號。藝術符號實質上是藝術家創造出來的藝術品。為什么用藝術符號來指代藝術品,是因為藝術符號承載了藝術家在藝術品中投射的感情,它實質上是一種情感的“表現性形式”,是作家內在情感的外部顯現,是對主觀現實的客觀顯現。藝術是什么?克萊夫貝爾認為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蘇珊朗格認為藝術是一種“表現性形式”。我們不能以一般性的語言符號來看待意味,審視情感,而是應該從它的藝術符號角度入手,從詩歌本身入手,才能了解詩歌的真正意義。
詩歌相對于一幅畫,一件雕塑,一場舞蹈來說都是不同的,它是通過語言的使用來傳達藝術家或者作者內心的真實情感,而這些語言并不是普通的語言,而是一種藝術符號,這種藝術符號具有著一定的造型功能,不能把詩歌這種藝術看作是對一件事情的論述,對風景的再現。對于《沙揚娜拉》這首詩來說,題目中的“再見”不是作者要闡述與某一個人說再見的這一事實,而是作者想要通過這樣一個符號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很多人因為這首詩的副標題是“贈給日本女郎”,就認為作者描繪的是一位婀娜多姿的日本女郎,她擁有著像水蓮花一樣嬌羞的面容。這樣的解讀就是忽略了詩歌的表現性形式,以及它的造型功能,只是單單從它的一般性語言符號來解讀,把意境優美的詩歌完完全全地解讀成了敘事詩。在蘇珊·朗格看來,真正偉大的藝術是反對再現形式的,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作家內心的真實情感,而不僅僅是對人物或者是對景物的客觀的、單純的描寫,更不是對于外部世界的再現。由此我們再看《沙揚娜拉》這首詩的時候,應該從作品的純形式來審美、欣賞,而不應該從文學作品所再現的內容去理解作品。
二、沙揚娜拉中的意象
我們不能從一般性語言符號與敘述角度來解讀《沙揚娜拉》這首清新明麗的詩,應該從詩中來尋找它所具有的意味與蘊含的感情。“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詩中的意象符號寫的溫婉動人,“那一低頭的溫柔”,為什么這“溫柔”是低頭的溫柔,而不是投入懷抱的溫柔,因為“低頭”是作者創造出來的獨特意象,低頭是因為不能正視,為什么不能正視自己的內心,和心中的情感呢?不敢還是舍不得,在詩人徐志摩的心里,兩者都有吧。這表現了作者對往昔的懷念,心中無法忘記曾經擁有的感情,對往昔有著無限的眷戀,不敢正視那曾有過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蓮花在水中亭亭玉立,一陣涼風吹過,有著無限的嬌羞。這陣風不僅吹過池中的水蓮,也吹過詩人的心中,一陣陣涼風,象征著作者此時內心的悲涼之感,情感上受到的創傷如同風的的微涼,悲傷之情油然而生。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蜜甜的憂愁——沙揚娜拉!”文中重復了三次“一聲珍重”,重復的手法在于強調,詩人在強調什么呢?是那真正的一聲聲珍重么?并不是,而是在這“一聲珍重”中表明了徐志摩心中充滿了不舍之情,一聲珍重并不能夠表達他內心的不舍,詩人反復用了三次,更說明了徐志摩心中充滿著無限眷戀,萬分不舍。這一聲珍重也象征了詩人要表達的“一生珍重”,可見這是對詩人多么重要的一份感情,需要詩人苦苦追尋一生,用他的一生只為說一聲珍重。這是徐志摩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情,一份尋而不得的悲涼之情,也是只能放在心底珍重的遺憾之情。而“蜜甜的憂愁”,也是詩人創造的獨特意象,表達了即使這份感情是遺憾的,是得不到的,但是在他心里也是甜蜜的,值得回味的,更能說明詩人表達了他喜憂參半的心境。結尾處的“沙揚娜拉”,并不是與友人告別時說的再見,而是作者以此為意象,對過去的種種往事,心中的縷縷情絲做一個告別,也象征著他內心追求的美好情感的破滅。這些曾經美好的往昔與作者說再見,作者也要與心中的美好的愛與過往說再見,更表現出了作者對失去的美和愛的眷戀之情。
三、意象的原型
“一低頭的溫柔”、“水蓮花”、“嬌羞”,“蜜甜的憂愁”……為什么詩人徐志摩在這首詩中選取了這些柔美卻又悲傷,并且帶有女性色彩的意象,來表達內心的感情呢?我們只能從中國古代的原型意象中一探究竟。
水蓮花:蓮花這一形象在中國早期的藝術中已經出現,不僅在出土的陶器上具有模擬女陰的性質,并且在中東的埃及、東方的印度等國家,女性陰部都以蓮花或荷包來象征,并且在梵文“蓮蓬”與“子宮”是同一個詞。[2]作為常見的女性意象的荷花,在中國的文學《詩經》和《楚辭》中也有體現,在《詩經》的《山有扶蘇》中有“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陳風·澤坡》中猶有“彼澤之陂,有蒲與荷”《簡兮》中有“山有榛,兮有苓”。《詩經》中的這三首都描寫了少女與愛情有關的故事。徐志摩這些甜蜜又悲傷的情緒原來是源于一位女子,蓮花不僅是女性的象征,并且在佛教中,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清新淡雅,是佛門的圣物,是佛家完美無瑕、圣潔的象征。徐志摩用蓮花來象征這位女子,這位女子就是徐志摩心中的純潔的初戀林徽因吧。徐志摩選取蓮花這個意象,并不是刻意的去通過蓮花與女性嬌羞的相似性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而是他內心潛意識的真實寫照,他內心中的林徽因是一個純潔如蓮花般的少女,他與她的這段感情也是純潔不摻雜任何其他的東西,這是徐志摩無意識的來表達他心中的真實感情。
涼風:這里的涼風并不是詩人描繪的風景,而是詩人創造出的意象符號。如果說這里的風是現實的風景,那是有悖于常理的,這首詩寫于1924年5月29日徐志摩陪泰戈爾訪問日本之后,而日本這個島國全年溫暖,即使是冬天也沒有嚴酷的寒冷,如果這首詩真的是寫實以及是再現現實的產物,顯然這里寫的“涼風”太不符合當時的場景了。所以“風”是詩人有意選擇的一個意象。“風”意象在愛情中經常用于寫女子見到思念中愛人后的喜悅之情,以及愛情婚姻遭到破壞或者是經歷波折。這一點多見于《詩經》中。如《正風·風雨》中“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北風·谷風》中“習習谷風,以因以雨”等等。[3]徐志摩與林徽因的感情歷經波折,卻終究是一場空,用風來形容這一段感情,和自己的心境,涼風吹過詩人的心頭,一切都結束了。
藝術品就是“情感生活”在空間、時間或詩中的投影,因此、藝術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或是能夠將內在情感系統地呈現出來以供我們識認的形式。[4]詩是作者表達情感的一種形式,其中的意象符號也承載了作者的感情,如果非要把這種情感的形式看作是具體的事物,那在理解作品的時候,可能就會看不到作者到底表達了怎樣的情感。藝術就是這樣,它的情感形式是與作品直接溶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以它為媒介物傳達出來的,情感本身就是融入在藝術作品中的。如果我們把情感與形式割裂開來看,只看到作品呈現給讀者的表面的形式,只欣賞作品中描繪的客觀事物或者是景色,而看不到這種形式作為一種藝術符號承載了作者內心的真正的感情,往往在理解作品時會與作者當時的情感有所偏差,只有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文學作品體會到作家的情感,我們才能具有真正的審美體驗,把握文學作品中的意味。
四、結語
藝術品本質上就是一種表現情感的形式,并且它也是可以感知的一種形式,它們所有的表現正是人類情感的本質。徐志摩寫的這首《沙揚娜拉》,正是表現他內心對于失去美好的一種本質性情感。藝術的本質都是內在生活的外部顯現,都是主觀現實的客觀顯現,是主觀生活的對象化,文學作品也是如此。正是因為他和林徽因相愛過最后卻沒有在一起,這樣的生活經歷,使徐志摩對林徽因一直念念不忘,但是他理智上知道林徽因不可能與自己在一起,應該和這段回憶、這種感情做告別,所以這首詩是他內心情感的本能體現。如果我們只從副標題看,就認定這首詩是寫給一位日本女子的話,那就割裂了藝術創作的真正原則。蘇珊·朗格認為創造一種訴諸知覺的表現性形式,是藝術的原則。文學和藝術一樣,都不是純粹的再現客觀事實,它呈現給我們是一種形式,蘊含著作者感情的一種外在形式,在欣賞和解讀文學作品時,應該如同蘇珊·朗格所說的:我所要作的就是透過層層表皮,最終揭示出這樣一個哲學問題;“表現某個人對于某些‘內在的’或‘主觀的’過程的概念”究竟意味著什么?[5]如果我們只從表面去欣賞文學作品,就不能體會到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當時的內心情感,也就不能體會到其中的“意味”所在。所以我們不能從作者的經歷以及副標題等等內容,就來定義作者的寫作意圖。不僅僅是《沙揚娜拉》,在這之后所創作的《再別康橋》,《再會吧,康橋》等作品中,徐志摩都表達了內心的感情,也體現了全人類追求美的普遍感情。
[1]徐志摩.志摩的詩[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9
[2]郭榮梅.試析蓮花文學意象的起源與發生[J].開封大學學報,2007(12).
[3]榮小措.試論古代詩歌中風意象[D].西安:西北大學,2002(05).
[4][5]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滕守堯,朱疆源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