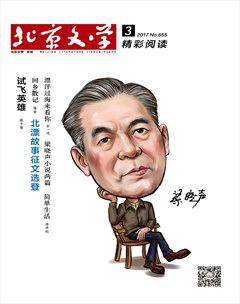爐火正旺
郝春霞
“從門口到窗戶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七步。”這是我在2001年內的第三次搬家的落腳處,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我需要越搬越偏離中心地帶,往城鄉接合部的繁雜區域靠攏。難以想象的是,新租的平房大小情形卻完全迎合了《二六七號牢房》開篇名言,單調、無聊、乏味、促狹,唯一不同的是我還享有自由的腳步。現實的雜亂無序,更加劇了內心的無依和迷茫。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馬路對面花園式小區,樓勢磅礴拔地而起,綠樹蔭翳,花團錦簇,曲徑通幽的石子小徑,行走著三三兩兩閑庭信步的人們,醒目的、艷紅的、張揚的寬大橫幅,熱烈歡迎著新入住的業主們。視覺和感受上巨大的反差,沖擊著我往日的價值觀和認知,羨慕,嫉妒,外加如牙齒癢癢般的那點滴的恨,一股腦地俯沖而來。歸屬的無依,自我的否定,讓卑微、沮喪的情愫,傾瀉而下,北京原來是天堂,亦是地獄!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被這種情緒激烈對抗著。
不大的院落內,住著六七戶人家,干著各色營生,從凌晨到午夜,喧囂、叫嚷一刻也不會停止。我那20平米的出租屋內,放置著兩張膠合板對接而成的雙人床,再加上房東大媽舍予的一件方形柜子,有幾塊木板釘在一起,成為我在北京蝸居里唯一的家具;一臺奢華的14英寸電視機坐落其上,供空閑時全家消遣娛樂。不過我卻幾乎沒有時間消磨在它身上,倒經常用它來哄孩子,因為經常搬家的緣故,三歲的兒子和同齡的孩子建立不起來穩固的友誼,在一個地方,剛剛和小伙伴熟絡起來,因各種緣由,不得不重新找房搬家,熟悉到陌生,不停地循環往復,孩子也變得融入不進新的群體當中,顯得孤單且落落寡歡。少兒頻道的各種動畫節目,成為孩子穩固而開心的保姆和玩伴。
凌晨4點我硬撐著起身下床,要把愛人凌晨兩點出夜市烤魚回來的攤子收拾停當。冬日里這個點,天空中還是繁星閃爍,滿載的一輛腳蹬三輪車靜默地立在墻根,各色調料玻璃罐里面裝滿孜然、辣醬、甜面醬、蒜蓉醬、鹽巴,林林總總,不勝繁多。逐一擰開,重新灌裝填滿。把已烤好、雇主沒有蘸動的烤魚,擼到一個盤子里,留在晚上加熱后,讓孩子也品嘗下烤魚的美味,解解饞。細算下來,光成本就得有1塊,我可是舍不得吃,真的。一個月要120塊的房租,外加水電費的費用就要150元,孩子的幼托費就差不多一月300塊,外加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一天一睜眼,就要欠別人幾十塊,不節省著用能行嗎?想著盡快還上背井離鄉時借用的兩萬多外債,光靠我倆那可憐的800多元薪水是不夠的。蜂窩煤爐里還殘留著余溫,點點星火還不時地閃著若隱若現的光,把未燃盡的蜂窩煤用鐵鉗夾出來擱置在水管的一旁,把爐內四周的灰燼倒干凈。我吃力地把爐子從三輪車上搬到院子的自來水管下,刺骨的涼水,浸泡其中的雙手凍得麻木不覺,就著爐子旁夾出余炭的殘溫,仔細沖刷干凈,油刷、醬刷、筷子、鏟子……分門別類一一歸置妥當,天已大亮了。只要時間趕趟,早餐一般都不在外面的攤位上買,怎么也沒有自己做的節省,我的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刃上,因偌大的北京城,舉目無親,在我深陷困境時,沒有人會無端地借錢幫我渡過難關,不得不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送孩子入托后,胡亂地吞幾口飯菜,急著趕到單位上班,早8點到晚6點,10小時的班制,沒有本地戶口,簽的是臨時工,一年一聘,表現不好,就有可能隨時卷鋪蓋走人。在自己和外人看來,能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落下一只腳,已是上蒼的眷顧了,要格外珍惜。6點下班我直奔幼兒園,估計孩子又是最后一個孤零零在那兒翹首期盼我的到來了。孩子每次都是略帶祈求的語調:“媽媽早點來接我。”我每每狠狠地點頭答應,卻又一次次食言,沒有辦法,為了生存,我也是分身乏術。接上孩子,就直接扎進附近的菜市場,這是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場景了,每天這個點,我都準時到這里挑選晚上出夜市的各種烤魚,主顧之間也已相當熟絡,沒有過多交涉,就稱好裝袋。回家打開電視機,調到動漫頻道,孩子立刻被畫面所吸引,我抓緊利用這個間隙,把買來的魚清洗處理干凈,按不同部位、不同種類串串,整齊地碼放在一個白色的保溫泡沫箱里。萬事俱備,只等愛人準時下班回來,推車走人去攤點站街烤賣。
北京深夜的街頭,北風凜冽著一陣陣呼嘯而過,在零下十幾度的低溫侵襲下,唯一一個取暖的火爐,被推走擺攤了,出租屋冷得像冰窖一樣,孩子凍得哭哭啼啼,連長點兒的美夢都不能合攏,時斷時醒。外加又擔心愛人一個人照顧不周攤位生意,我索性帶著包裹好的孩子,一起出攤來了。強勁的北風颼颼地越過臉頰,生硬且刺骨,時間久了,那雙不算厚的棉鞋,也漸漸吃不住這寒風一個勁地猛吹,腳開始麻木酸脹地痛,唯有不停地挪動著腳步,不停地替孩子揉搓著有些僵硬的雙手,拔掉火爐上擋風插板,吹旺了爐火,一家人靠近那火苗騰騰跳動的火爐,抵御著北京街頭的嚴寒。沒多少人在這么晚了,還出來閑逛,生意冷清得很。不知誰喊了一句:“城管來了!”稀里嘩啦,周圍的攤子都慌亂地往車里裝著家什,愛人也麻利地把地上裝烤魚的箱子和用具,一股腦地扔進三輪車里,可這火爐和上面燒得滾熱的鐵板呢,圍堵的城管近在咫尺,來不及多想,我伸手抱起來也往車里掄過去,刺啦一聲,手心里的一層皮被剮了下來,疼痛得臉幾近扭曲變形。孩子也驚恐地目睹著大人們為了生計的瘋狂舉動,茫然不知所措。去醫院處理后回家已是午夜1點了,說及此事,一家人極其沮喪頹廢,一言不發,神情落寞到極點,想想也是,今晚一共沒賣出去幾份,還有一個無賴沒收上錢來,車、魚、爐,一切用來營生的用具,都給沒收了,連本加利,足足有幾百塊。想著那一爐膛燃燒正旺,本可以給人以溫暖的煤火,卻不曾想呼呼卷吐著的淡藍色的火舌,急急要吞噬掉世間的一切。站在北京繁華的街頭,卻時時感受到從繁華背后吹過來悲涼的風,因為北京,它從不憐憫任何人的眼淚。考慮到退縮回鄉,卻又憶起臨行前的初心,真是應了別人那句:“回不去的農村,融不進的城市。”既然北京不憐憫任何人的眼淚,那我就要不顧一切地微笑一次,置之絕地而后生,逼迫自己任性而自我地活一次,蛻變一次。不要到垂垂暮年,憶起舊年,只有年輕時的力氣和飯量可以向后人述說。既然貪戀爐火的溫暖,就不要拒絕它的灼傷,就像你鐘情于玫瑰的馨香,就不要憎恨它銳利的針刺。
接下來的日子,我利用空余的時間,自修了會計專業,考取了有著技術含量的專業消毒鍋本,藝多不壓身,拿著與之相適應的不薄的薪水,不再是單調乏味的重復低成本的工作。愛人也經過幾年的打拼,如今,已擁有了自己的醫療設備公司,日子溫暖踏實。當年的我們趁著爐火正旺,擦干眼淚,引著另一“生命爐膛”里的炭火,如今在窗明幾凈的樓房里,外面天寒地凍而室內依舊溫暖如春,悠然喝茶品茗,而不用去擔心城管,來沒收你違章設攤且用來立命的家什。也不見捉襟見肘的窘迫日子,催得人四處游蕩而不顧一切地去討生活。也終于能和你并肩站在帝都的街頭,有著賞花、賞月、賞“秋香”的閑暇與愜意。
如今城市倡導節能減排,很少再能見到煤炭爐火了,在鄉下偶爾遇見,也常是倍感溫暖親切。因那一膛的爐火,讓人在北京這個物欲橫流、人聲鼎沸的大都市,時時都會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責任編輯 張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