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寫小說,是為自己制造愁煩
張愛玲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先生對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們大家點頭領會。她繼續(xù)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我將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于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嗎?寫作不過是發(fā)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fā)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基本問題是:養(yǎng)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
一般來說,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jīng)驗,一點獨到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想過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也就就此湮沒了。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于老年人的脫發(fā)有極其精微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禿頭,現(xiàn)在不禿了。老太爺則相反,從前不禿,現(xiàn)在常有禿的。外國老太太不禿而老太爺禿。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著太緊的發(fā)髻,將頭發(fā)痛苦地往后拉著,所以易禿。男子以前沒有戴帽子的習慣,現(xiàn)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子于頭發(fā)的健康有礙,所以禿頭的漸漸多了。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禿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后,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于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yè)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她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地撿了回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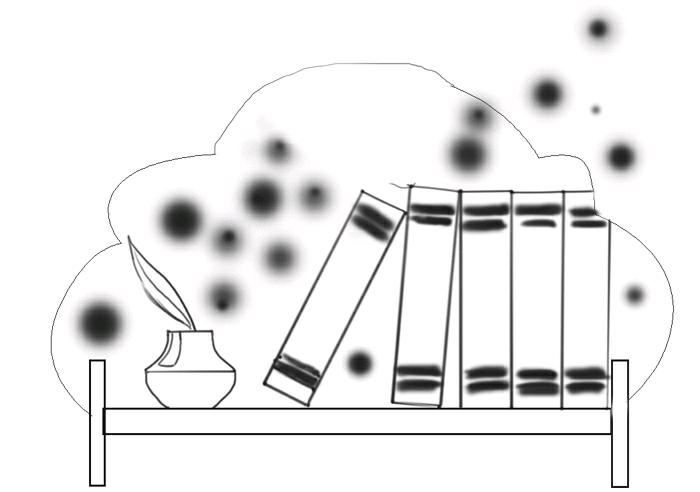
寫小說,是為自己制造愁煩。我寫小說,每一篇總是寫到某一個地方便覺得不能寫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寫的《年輕的時候》,剛剛吃力地越過了阻礙,正可以順流而下,放手寫去,故事已經(jīng)完了。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人生恐怕就是這樣的吧?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麻煩剛剛完了,人也完了。
寫這篇東西的動機本是發(fā)牢騷,中間還是兢兢業(yè)業(yè)地說了些玩話。一般文人何以甘心情愿守在“文字獄”里面呢?我想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文字的韻味。譬如說,我們家里有一只舊式的朱漆皮箱,在箱蓋里面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幾行字,印成方塊形:
高州鐘同濟 鋪在粵東省城城隍廟左便舊倉巷開張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發(fā)客貴客光顧請認招牌為記主固不誤 光緒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撐著箱子蓋看了兩遍,因為喜歡的緣故,把它抄了下來。還有麻油店的橫額大匾“自造小磨麻油衛(wèi)生麻醬白花生醬提尖錫糖批發(fā)”。雖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們也像是隔了一層,略有點神秘。
然而我最喜歡的還是申曲里的幾句套語:五更三
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zhí)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照例這是當朝宰相或是兵部尚書所唱,接著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種種問題。若是夫人所唱,便接著“老身”的自敘。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具有同一種的宇宙觀——多么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文官執(zhí)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思之令人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