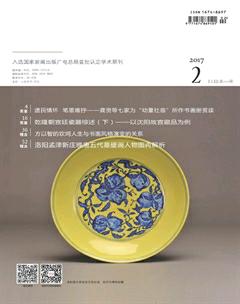試析西周復合體玉柄形器的組合方式
張儉


【摘 要】通過梳理西周時期復合體玉柄形器的資料,著重對其器柄、組合附飾、穿孔蚌托、玉柱四個組成部分的組合方式進行了分析,認為復合體玉柄形器的器柄是插嵌入組合附飾之中,而組合附飾是粘連于漆木牌上的整體,穿孔蚌托是緊貼于組合附飾末端,最下方是玉柱插入穿孔蚌托之中。
【關鍵詞】西周時期 復合體玉柄形器 組合方式
柄形器是商周玉器中較為常見的一種玉器制品。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玉柄形器絕大多數出自規格較高的大中型墓葬。最早見于二里頭文化的墓葬中,經歷了商代早中期的初步發展時期,商代晚期、西周早中期的大發展繁榮時期,后逐漸衰落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1]。因其名稱和用途目前還未弄清楚,故以其形狀略似器柄,暫稱之為柄形器[2]。
一般來說,可根據有無組合附飾,將玉柄形器劃分為單體和復合體(也有稱“組合型”[3])兩大類。顧名思義,單體玉柄形器即出土時沒有附飾,僅為一件器柄;復合體玉柄形器不僅包含有器柄,而且器柄末端還有一組玉飾、石飾、綠松石片、蚌片按照一定規律分層、分列地鑲嵌在一起的附飾組合。組合附飾是一個整體形象,其出土時玉、石、蚌、綠松石片均呈較易散亂的單個個體,但排列整齊。部分復合體柄形器的附飾下方還發現有漆痕[4],因此推測它們可能是粘連或鑲嵌在一種易腐朽的有機質載體上,如絲帛、布、革,或是竹木片、漆木牌等。此外,據保存較為完整的玉柄形器資料[5]來看,器柄、組合附飾的底部還有一件穿孔方形蚌托,蚌托中插入一件玉柱或蚌柱。由于器柄末端部分或出榫、或薄刃,似為方便插入或嵌入某物之中,而復合體玉柄形器出土現狀大都是器柄與附飾組合緊密連接在一起,因此有理由推測器柄下端是插入或嵌入附飾組合,然后組合附飾底部連接一件穿孔的方形蚌托,蚌托下插入一件玉柱或蚌柱,這樣便構成了一件完整的復合體玉柄形器(見圖1)。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知,復合體玉柄形器最早出現于商代后期,僅在小屯西北地[6]發現4件,其中1件出自墓葬M41,3件出自小屯宮殿區以婦好為代表王室墓附近的祭祀坑內,這說明玉柄形器具體執行的宗教祭祀功能受到晚商上層階級的特殊關注[7]。西周時期,復合體玉柄形器主要集中分布在陜西、河南、山西等地的大中型墓葬中。西周早中期是復合體玉柄形器最盛行的時期,數量多,形制豐富,且普遍隨葬于大中型墓,說明上層階級對其非常重視和偏愛。西周晚期,復合體玉柄形器數量逐漸減少,形制由多樣變單一。至春秋初期,幾乎完全消失。
從復合體玉柄形器出土現狀來看,大部分情況是:自上而下,依次連接為器柄、組合附飾、蚌托、玉柱。器柄末端呈薄刃、出短榫,或斜平,或抹角,似為插入或嵌入組合附飾部分。
有的學者認為,器柄是裝入鞘袋的,而組合附飾是鞘袋上的裝飾物[8]。依據有二:一是鎬京發現的一件單體玉柄形器長花M15:25出土時即插入魚皮鞘中[9];二是器柄和組合附飾并非緊密連接,而是有一段間隙,而且組合附飾兩側寬于器柄。這一觀點值得商榷。首先,魚皮鞘屬孤例,也許可以不排除單體玉柄形器有插入鞘袋的慣例可能,但不能將之拿來證明復合體玉柄形器也是如此,畢竟復合體柄形器的組成部分還包括組合附飾、蚌托、玉柱等。從洛陽北窯墓地所出的完整復合體玉柄形器來看,蚌托下插入玉柱,蚌托和玉柱緊密連接在組合附飾的末端,那么,這樣一個整體如何插入鞘袋?其次,由長安張家坡M44:7(見圖2,原報告標注為戈,實際上7號戈應該與之旁邊的組合附飾形成一個復合體玉柄形器,否則該組組合附飾無處安放,而且該墓是保存完好連填土一起整體提取出來復原的)[10]可知,組合附飾和柄是可以完全脫離、拆卸分開的,有理由相信這二者是可活動裝卸的。如果按照該學者的說法,組合附飾是鞘袋上的裝飾物,那么為何埋葬時有的裝入鞘袋(復合體玉柄形器的器柄和附飾組合連接在一起),而這件卻沒有裝入鞘袋,難道是鞘袋脫離?再次,該學者認為附飾組合與器柄之間有空隙,因此二者不是插嵌關系。但如果附飾是鞘或袋上的裝飾品的話,為何所有的附飾組合都是出現在緊接著柄尾端的位置,難道鞘或袋子的深度正好是在附飾以上?那所謂的鞘袋上裝飾組合附飾有何意義?這樣顯然和兩者分開沒有區別。此外,他假設組合附飾是兩面各一層或兩層對稱地裝飾于鞘袋上,但是根據考古發現,兩層或四層附飾并不對稱,它們僅僅在同一層、同一平面上中軸左右對稱,而非作者所認為的第一層與第二層一模一樣,第一、二層與第三、四層對稱。所以,如果第一層、第二層比較精致的玉飾鑲嵌在正面,第三層、第四層比較粗糙的石飾、蚌片鑲嵌在背面,何來對稱之說?似乎沒有這個必要。因此,我認為,組合附飾并非是鞘袋上的裝飾。
我認為,組合附飾應是鑲嵌在漆木牌上的裝飾物,器柄是末端榫頭插嵌木質漆牌中并加以粘連牢固。
由出土現狀來看,組合附飾中同形制的玉飾或石飾或綠松石片都是一層一層緊密重疊的,可見二者并非分開粘連在不同的平面上,而是一起粘連附著成一個整體,然后才鑲嵌在一個漆木牌上。根據洛陽北窯墓地出土的復合體玉柄形器的器身及其周圍發現有漆痕殘跡來看,組合附飾應該是附著在牌狀的漆木器上。而組合附飾的末端較為齊平,與之相接的蚌托面同樣非常平整。那么,再來看看厚度的比較:蚌托側立的厚度,即蚌托的寬是1.4厘米;組合附飾的厚度,即四層附飾+漆木牌的厚度,四層附飾大致的厚度累加起來是0.95厘米[11];反推之,漆木牌的厚度可能會在0.45厘米左右,器柄末端的薄刃厚度是0.2~0.9厘米,不超過組合附飾的厚度,再加上未知的漆木牌厚度,理論上可以完成插嵌。
因此,通過以上三者大致可推算出器柄末端、組合附飾末端與蚌托之間的厚度并不相沖突,能夠完成器柄插嵌入組合附飾以及組合附飾末端與蚌托對接。最后是玉棒插入蚌托穿孔中,超出穿孔的部分依然插嵌入帶漆木牌的組合附飾整體中。
從出土位置來看,西周時期復合體玉柄形器較多的是集中于墓主人胸、頭骨、腹、腰胯部,少數出土于葬具即棺蓋上、槨蓋上及棺槨之間,此外還有極少數出土于墓壁或被墓主攥握在手中。可見,復合體玉柄形器作為隨身攜帶的配飾的可能性較大。其中,貼于墓壁放置的3件復合體依然保持四部分結構完整,足以證明復合體玉柄形器的四部分結構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張劍據此認為是玉柄形器出外時佩戴于腰間,居家時懸掛于墻壁之上[12]。曹楠簡單根據出土位置判斷即得出結論,認為它用于多種禮儀活動,是可以捧在手上、佩戴在胸前、懸掛于腰間的[13]。我認為,根據其出土位置來推斷柄形器的用途和性質,實在是不妥。張長壽即認為根據柄形器出土的這些位置并不能表示柄形器自身的功能,而只是顯示墓主人的地位和財富[14]。此外,劉釗在考察安陽后崗殷墓的柄形器用途時,從柄形器上的銘文王的稱謂,甲骨文“示”“主”字與柄形飾的象形方面的綜合考證,認為“石主”是柄形飾的用途之一[15]。同樣從古文字著手并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推斷,李小燕、井中偉從古文字“瓚”的結構與晚商小臣單體柄形器自名的瓚字進行比較,同時結合洛陽北窯M155:17復合體玉柄形器下端有一件形似觚的漆痕,遂判斷玉柄形器是玉瓚,是祼祭用玉之一[16]。此外,關于玉柄形器的用途還有琴撥、命圭、發簪、玉璋、玉節等說法,但是從復合體玉柄形器的完整組合結構來反觀,部分說法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從墓葬中隨葬的頻率來看,大多數墓葬僅隨葬1~2件復合體玉柄形器,隨葬較多的有寶雞茹家莊M1甲、乙室共出17件[17],扶風強家村81M1出土5件[18]。而且,如果一座墓葬中出復合體玉柄形器的話,就必然會出單體玉柄形器,反之則不然。可見,復合體玉柄形器在西周時期仍然較為珍稀,多隨葬于等級較高的墓葬,隨葬于身份顯貴的諸侯、奴隸主貴族等墓主人身上。
注釋:
[1]張劍.商周柄形玉器(玉圭)考[A].三代文明研究(一)[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401.
[2]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J].考古,1983(5).
[3]石榮傳.再議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J].四川文物,2010(3).
[4]洛陽北窯西周墓地的復合體玉柄形器器身和周圍發現有漆痕.
[5]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洛陽北窯西周墓的M174:40、M216:3、M216:4、M216:5、M216:6、M215:35、M215:48、M155:17、M173:9、M250:1這10件復合體玉柄形器均保存完整,由一件器柄、一組附飾、一件蚌托、一件玉柱或蚌柱,這四部分組成,彼此緊密連接。而且,器身四周有木跡和漆片痕跡.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小屯[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04.
[7]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2(3).
[8]魏繼印.玉柄形器功能新識[J].考古與文物,2013(1).
[9]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J].文物,1986(1).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11]根據報告中對玉附飾的描述計算得出,即厚體玉飾厚度0.5+薄片玉飾厚度0.25+兩層石飾0.1+0.1=0.95厘米.
[12]張劍.商周柄形玉器(玉圭)考[J].三代文明研究(一)[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13]曹楠.三代時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J].考古學報,2008(2).
[14]張長壽.西周的玉柄形器——1983~86年灃西發掘資料之九[J].考古,1994(6).
[15]劉釗.安陽后崗殷墓所出“柄形飾”用途考[J].考古,1995(7).
[16]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J].考古與文物,2012(3).
[17]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弓魚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8]周原扶風文管所.陜西扶風強家一號西周墓[J].文博,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