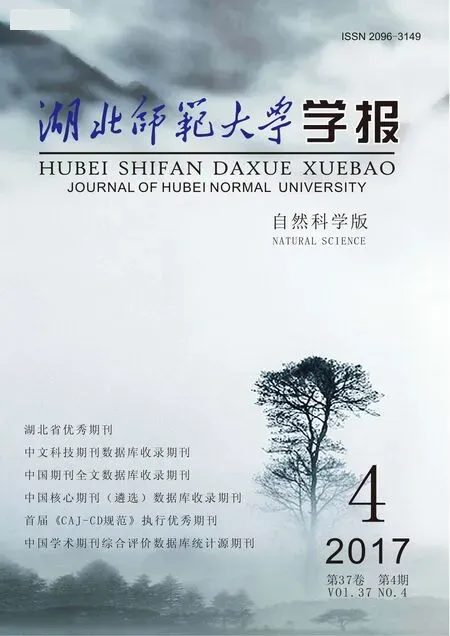淺析“互聯網+”背景下圖書館的發展與變革
劉桂琴
(湖北師范大學,湖北 黃石 435002)
淺析“互聯網+”背景下圖書館的發展與變革
劉桂琴
(湖北師范大學,湖北 黃石 435002)
“互聯網+”背景下圖書館所處的技術環境和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詳細闡述了“互聯網+”的內涵和特征,并以“互聯網+”背景下圖書館用戶需求及服務模式的變化為導向,分析了“互聯網+”驅動下圖書館發展模式的變化。
互聯網+;圖書館;大數據;發展模式
1 “互聯網+”
1.1 相關概念
“互聯網+”的概念,首次由易觀董事長于揚先生于2012年底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移動博覽會上提出。當時,這個概念一提出,“互聯網+”一下子就成為了網絡熱搜詞匯。隨后,各級政府和相關行業都對“互聯網+”的特點、發展及行業規范等展開了積極的研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第一次將“互聯網+”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這標志著以物聯網、通信網絡、云計算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為標志并以新硬件應用、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互聯網+”時代正式來臨[1]。
通俗的說,“互聯網+”就是“互聯網”加上“各個行業”,但這并不等于將互聯網與各個傳統行業簡單的疊加在一起,而是利用日益發達的通信技術和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讓互聯網與各個行業間能夠在技術、管理等層面深度融合,構成一種全新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態。
“互聯網+”充分發揮了互聯網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集成和優化作用,將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的發展成果深度融合于各經濟行業之中,通過創新來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逐漸形成更為廣泛的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新經濟發展形態。
1.2 特征
隨著“互聯網+”思維的逐漸清晰呈現,其運營模式的多領域應用,“互聯網+”背景下的行業形態逐漸呈現出六個特征[2]。
1) 跨界融合。所謂“+”就是跨界、開放、變革,就是重塑融合。跨界融合之后,更能實現群體智能,創新的基礎更堅實,從研發到產業化的路徑也更垂直了。從另一層面來講,融合本身也指參與者身份的融合,例如客戶消費行為轉化為投資,消費者變為參與伙伴。
2) 創新驅動。一直以來,我國以資源驅動為代價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與科學發展觀的實質相悖。唯有以創新驅動發展,走能源節約型的科學發展道路,才是一條長效不衰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創新正是互聯網的特質,用互聯網思維來實現自我變革,更能發揮創新的力量。
3) 重塑結構。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打破了全球范圍內原有的經濟格局、文化格局、社會格局和地緣格局,經濟體之間各種行業規則,如話語權、主動權等都不斷在發生變化。另外,“互聯網+”背景下的現實社會治理和虛擬社會治理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4) 尊重人性。人性是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科技進步、文明發展、文化繁榮最根本的力量。互聯網之所以力量強大、發展迅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對人性最大限度的尊重,敬畏人的體驗,重視人的創造性發揮。例如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分享經濟,卷入式營銷等都是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發展起來的。
5) 生態開放。健康的生態本身就是開放的,而“互聯網+”中生態開放是其非常重要的特征。推進“互聯網+”,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把過去制約創新和發展的環節化解掉,由市場驅動科技創新,并把過去“孤島式的創新”連接起來,讓努力創業者有機會實現其價值并得到相應的回報。
6) 連接一切。連接一切是“互聯網+”的目標和優勢。通過將功能和價值不同的各個行業有層次的連接起來,發揮“1+1>2”的整體功效。
2 “互聯網+”環境對圖書館的影響
“互聯網+”運營模式的多領域應用,社會必將呈現出多種發展趨勢。單從技術發展趨勢來看,將從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社會向數字技術(Data Technology,DT)社會快速轉變,進而將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新硬件應用、數據挖掘等方面展現出從未有過的智慧管理水平和新技術應用[3]。各行各業,無論是新興行業還是傳統行業,都將借“互聯網+”的東風,主動實現與互聯網的對接,爭取實現產能、效益、管理和服務的轉型與升級。
圖書館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的知識存儲與傳遞機構,一直緊跟時代步伐,努力適應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并在文獻保存、知識服務甚至數據挖掘等方面表現出獨有的優勢。在“互聯網+”時代,由于用戶需求的更加個性化和差異化以及資源趨于數據化和異構化特征,使得圖書館資源、服務及管理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互聯網+”大環境對圖書館的存在形態、服務模式和管理形式等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推動著圖書館的發展與變革。這種發展與變革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從文獻資源建設向數據資源建設方向變革。數據是圖書館發展的原始動力,“互聯網+”技術驅動下的大數據價值的深層次、多視角挖掘和數據密集型科研環境的形成,使得圖書館逐漸看到了通過數據挖掘和應用所產生的服務效益,越來越多的圖書館認識到了數據分析和和保存的重要性。
2) 管理模式從階梯式向扁平式變革。隨著移動通信設備的普及,“互聯網+”背景下移動互聯網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面信息交互模式成為一種普遍存在。新環境下,圖書館的內部業務既要強調個人、部室和資源之間的協作,更要強調圖書館員與用戶和資源甚至決策責任人(館長)之間的交互,傳統管理體系中的中間職務—部室主任的功能進一步被弱化,圖書館在內部管理體制上由階梯式逐漸向扁平化方向發展。
3) 從“現代功能型”圖書館轉型為“智慧型圖書館”。“互聯網+”環境下圖書館的服務逐漸從線下走向互聯網化,隨著差異化用戶需求、異構化結構數據和多元化資源類型的出現以及資源、圖書館員、用戶三者之間發揮協同支撐作用,最終圖書館的服務性質將變為對用戶的智慧管理和為用戶提供智慧服務,實現向“智慧圖書館”轉型。
面對“互聯網+”化的社會大環境,社會由IT需求向DT需求轉型發展的過程中,圖書館唯有以更加開放的思維主動去迎接和適應時代的變化,通過研究“互聯網+”下圖書館存在的新問題、新情況,推進圖書館管理、服務等各個層面的改革和創新,全面提升其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形成新型的管理和服務模式,如此才能適應環境變化,從而實現圖書館事業、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更長遠發展。
3 圖書館的應對措施
自“互聯網+”理念提出以來,圖書館界對其展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聯網+圖書館”形態下的圖書館服務的轉型與發展、服務平臺構建、數據素養教育、圖書館發展定位等方面。僅2015年,國內圖書館界就組織召開了三次以“互聯網+”為主題的研討會。隨后,許多圖書館開始嘗試將“互聯網+”思維應用到圖書館的業務與實踐工作中,依托“互聯網+”技術和理念,開展智慧服務、移動APP服務和基于大數據的知識服務等系列新型服務[4]。如上海圖書館于2015年開展了主題為“‘互聯網+’圖書館,傳遞閱讀的力量”的活動。通過活動利用“互聯網+”理念對上海圖書館資源進行了深度挖掘和有效整合,從而提升館藏資源價值。再如浙江省圖書館通過開展“互聯網+終身教育”、“互聯網+知識服務”等系列服務,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向用戶提供一體化在線交互式服務,提升圖書館的資源共建共享能力和資源管理能力[5]。筆者認為當前圖書館領域對于“互聯網+”研究與實踐的重心應該是“互聯網+”所帶來的管理與服務問題,要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1) 做好圖書館“互聯網+”的頂層設計,將大數據的廣泛應用作為推進“智慧圖書館”工作的重要思路[6]。圖書館的“互聯網+”頂層設計工作必須立足于政府出臺的“互聯網+”發展戰略。圖書館要努力推動各級圖書館協會、學會及聯盟、政府文化機構等出臺圖書館“互聯網+”健康發展的戰略規劃、指導意見及協作方案,把加快推進大數據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納入整體圖書館工作布局,協調并統籌各方面資源,穩步推進“智慧圖書館”的推廣與應用工作。
2) 做好圖書館“互聯網+”基礎支撐平臺建設工作。從目前來看,許多圖書館的“互聯網+”基礎支撐平臺建設尚不完善,尚不能支撐“互聯網+”在圖書館的正常運行和長遠發展。國家正在積極營造有利于“互聯網+”發展的大環境,基礎支撐平臺建設工程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就算依托國家戰略規劃中的“互聯網+”發展計劃,圖書館仍需要結合自身特色才能夠做好許多工作。
3) 制定與“互聯網+”相關的圖書館政策法規、行業管理制度和交互協議。國家已經制定“互聯網+”政策、標準和協議,圖書館界也應該結合行業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標準、規范和服務協議。通過對國家層面“互聯網+”相關政策的研究,促成各級政府、行業及領域相關政策法規、管理規章制度及交互協議的出臺,以保證即將實施的“互聯網+”相關服務適應圖書館的需求并能正常實行。
4) 解決好圖書館“互聯網+”平臺的知識產權及網絡安全問題。圖書館“互聯網+”投入應用后,如果沒有預先制定好相關規范,安全問題和知識產權問題會紛沓而至。面對這樣的新挑戰,必需先創建一個可靠的系統,用來主動識別并及時清除圖書館“互聯網+”大數據知識服務中的各類安全隱患與侵權隱患,對內外部所有連接環節中大數據知識服務、知識產權進行有效的監測和監護,并能通過不斷的系統修復和優化,實時、立體、全方位地保護圖書館“互聯網+”的健康、持續、穩定運行。
5) 創建“示范帶動、試點+樣本”模式,圍繞重要環節和主要矛盾,重點突破。以圖書館部分業務、或者部分圖書館作為試點、樣本,抓住涉及到的重要環節和主要矛盾,進行重點突破,并發現和研究圖書館“互聯網+”實施過程中會出現的類似問題,形成一套成熟可推廣的圖書館“互聯網+”實施方案。
4 結論
隨著“互聯網+”概念的提出,其所具備的時代特征,以及得到的廣泛應用和發展,加上“互聯網+”環境下圖書館用戶需求和數據環境的變化,都促使新時期下圖書館必須進行轉型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為了滿足新環境下的用戶需求,圖書館不得不拓展其服務內涵,改革其服務方式,重構其服務內容,以實現圖書館的信息服務與其他相關行業進行深度融合,繼續維持其社會知識信息服務中心地位。
[1]徐 雙. “互聯網+”背景下圖書館與利益相關者間跨界資源整合研究[J].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17,(3): 68~71.
[2]韓翠峰. “互聯網+”環境下的圖書館服務轉型與發展[J]. 圖書與情報: 2015,(5): 29~32.
[3]余 凌.“互聯網+”背景下的圖書館業務重組內容與方向研究[J]. 圖書與情報, 2016,(3): 79~81.
[4]向宏華.“互聯網+”思維下圖書館服務創新研究[J].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17,(4): 5~10.
[5]浙江全省公共圖書館開啟“互聯網+”新模式[EB/OL]. 2017-09-20.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728/c172318-27372044.html.
[6]張興旺, 李晨暉. 當圖書館遇上“互聯網+”[J]. 圖書與情報, 2015,(4): 63~70.
Abriefanalysisonthelibrary’sdevelopmentandchangeunderthebackgroundof“internet+”
LIU Gui-qin
(Library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library have greatly chang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ternet+”.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was illustrated. Taking the needs and service mode of library user as guid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he change of library’s development mode was analyzed.
internet+; library; big data; development mode
G231
A
2096-3149(2017)04- 0028-04
10.3969/j.issn.2096-3149.2017.04.007
2017—03—11
劉桂琴(1984— ),女,碩士,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