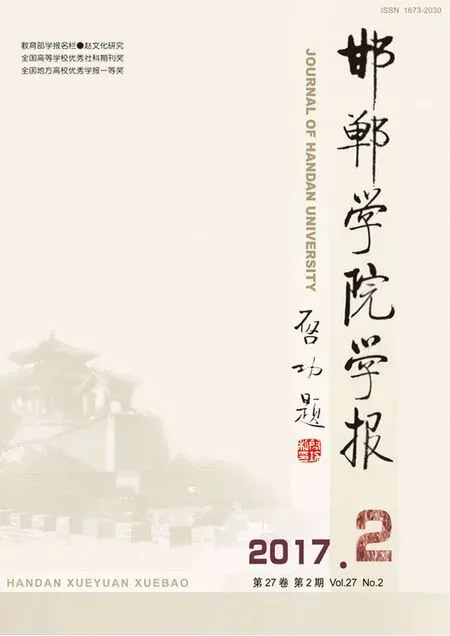荀子人性論研究綜述
王澤春
(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141)
荀子人性論研究綜述
王澤春
(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141)
朱閬仙之后,大部分學者看到了《性惡》篇與《荀子》其他篇在人性論問題上的表述不一致,由此又牽涉到《性惡》的作者問題。就上述問題,到目前為止,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一,《性惡》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學,不能代表荀子的人性論;二,《性惡》為荀子自著,跟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三,《性惡》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與其他篇章思想不盡一致。從方法來說,主要有兩種:一,從義理層面論證“性惡”、“性樸”等的矛盾或一致;二,從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等角度對《性惡》、《荀子》文本進行研究。
荀子;人性論;《性惡》;性惡
提到荀子,首先想到的是性惡論,性惡論已經成為荀子思想的標簽,根據就是《荀子》中有一篇《性惡》,在這一篇中多次提到“性惡”。但性惡論能否準確代表荀子的人性論,是否是荀子思想的核心,性惡論與荀子整體思想是否一致,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清末,蔡元培的朋友朱閬仙①朱閬仙,1873-1939,浙江紹興人,原名世煥,改名文煜,字心燾。朱閬仙的著作為《荀子大誼述》,現在沒有通行版本,不知是否尚存,只有蔡元培日記對其書的宗旨予以介紹。、蔡元培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認為“性惡”與荀子其他篇章對人性的看法不一致,《性惡》不是荀子的著作,屬于荀子弟子的著作。從此之后,或斷或續,海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論證。荀子的人性論與《性惡》篇的真偽有緊密聯系。到現在為止,基本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性惡》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學,不能代表荀子的人性論;第二,《性惡》為荀子自著,跟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第三,《性惡》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與其他篇章思想不盡一致。
一、《性惡》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學
朱閬仙的《荀子大誼述》是否尚存,筆者不得而知,現在只能從《蔡元培日記》的簡單介紹了解其主要思想:“閬仙治《荀子》數年矣,其初欲辨荀子非子思、孟子,及《性惡篇》非荀卿所著而已。……與蔡鶴庼論《性惡篇》非荀子所作書(七)、論《性惡》為孫氏之儒所著(八)”。之后,蔡元培在《荀卿論》中從文獻學的角度進行簡要分析,認為《性惡》篇可能是荀子弟子的作品:“豈知韓嬰《外傳》不著非孟之辭,董生《察名》,未引性惡之說。流傳別本,容有增加,韓非、李斯,固優為之。”
朱閬仙、蔡元培之后,劉念親于1923年1月16、17、18日刊登于《晨報副刊》的《荀子人性的見解》對這一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論述,他也認為“荀子人性的見解,我看不在《性惡篇》,并且我懷疑《性惡篇》不是他作的”,劉念親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述:除《性惡》外,《荀子》中論述性的一共有17條,“這十七條中,卻性惡二字從不見到連貫起來用”,“這是我疑《性惡篇》不是荀子自作的第一個證據”;“《非十二子篇》荀子向異己的學說,痛施攻擊,若是他曾斬截下了一個‘性惡’的斷案,那子思的率性說,孟子的性善說,便是與他根本上不能兩立的所在。他這篇非子思孟軻下,還肯將此并輕放過去么?……覺得即是那相對的‘性惡’說,非荀子自作的第二個證據”;“韓非、李斯曾師事荀子;漢代的賈誼曾師事李斯又曾向張蒼受學;蒼是荀子弟子,那么賈誼算是荀子的門人”,這些人都沒有提到過“性惡”二字,“如果荀子顯著的作了他的《性惡》的一篇,怎會他的弟子,門人,和稱美他的董仲舒說到人性許多地方,都有他遺傳的痕跡,偏莫直截了當沿用他一個惡字的斷案呢?這是我疑《性惡篇》非荀子自作的第三個證據”。至于《性惡》作偽的時間,“漢成帝以后,是廣出偽書時代……我疑心《荀子·性惡》也是這時代的出產品”。最終認為,荀子的人性“只是‘本始材樸’四字”。劉念親的這篇文章,論據充分、論證嚴密,之后討論《性惡》真偽文章的論述方法與結論,基本沒有超出劉念親的范圍,包括金谷治、周熾成。
金谷治認為“盡管《性惡》應該是《荀子》的代表作品,奇怪的是,《韓詩外傳》并沒有從《性惡》引用。再加上,荀子在《非十二子》并沒有批評孟子性善主張。根據這些事實,金谷推測,《性惡》也許是荀子后學的作品”。(見佐藤將之:《二十世紀日本荀子研究之回顧》)
近年來,中國大陸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的是周熾成,他的兩部專著及數篇論文從不同方面進行論證:《性惡》非荀子自著,荀子的人性論是性樸。他的這些論述的角度與結論基本與劉念親一致,只是在《〈性惡〉出自荀子后學考—從劉向的編輯與〈性惡〉的文本結構看》指出,劉向把《性惡》排在第26篇,應該“認為它出自荀子后學之手”。
顏世安在《荀子人性觀非“性惡”說辨》中指出,荀子的人性論不是長久以來認為的“性惡說”,而是“性善意識及荀子正面肯定情欲”的觀點。顏世安看到了《性惡》在人性論上與其他各篇的區別,認為《性惡》不是荀子本人的作品,而是荀子后學的作品。
筆者在《〈性惡〉非荀子所作新證》中指出“《性惡》中有四處“孟子曰”的引文,不見于《孟子》七篇,而屬于出現在司馬遷之后的《孟子外書》。由此可以說明《性惡》非荀子所作”,但對于《性惡》是誰所作,筆者沒有進行論斷,因為論證某一文本是某人所作比論證不是某人所作要困難得多;并且,就荀子人性論而言,只要論證《性惡》非荀子所作即可。
二、《性惡》為荀子自著,與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
劉念親的文章發表之后不到一個月,胡睿就在《晨報副刊》(1923年2曰6日)發表了一篇商榷文章——《“荀子人性的見解”的研究》,對劉念親的論證予以了逐條反駁。
對于劉念親的第一個疑問,胡睿認為“我國自古迄今的文人學者,幾乎沒有一個人的集子拿出來,都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的”,并且“《性惡篇》當為諸篇中最后之著作,自然在前幾篇中就不能倉促之間,使把‘性惡’兩字用出來”,所以,在其他篇章沒有出現“性惡”二字很正常,并不能因此就懷疑《性惡》為荀子著作。胡睿提出的理由是值得推敲的,其第一條理由,做了全稱判斷,是否合適是一碼事,即使其判斷準確,也不能得出其結論:雖然古人著書大多以單篇形式,但不影響其思想的一貫性與核心概念的重復出現。第二條理由,認為《性惡》是荀子晚年著作,基本是出于猜測,沒有進行論證。
對于劉念親的第二個疑問,胡睿認為《非十二子》“并不在學說根本上爭辯,要不然,墨子主張薄葬,荀子是主張厚葬的”,“沒有攻擊異己的學說,似乎也不能算一個確切的證據”。在《非十二子》中確實沒有批評墨子的薄葬,在《正論》中就對薄葬問題進行了批評,雖然在《解蔽》中對子思、孟子進行了批評,但還是沒有對人性論的批評。并且并非對其他思想家的任何思想都要在每篇都要進行批評,而人性論問題是重要問題,如果真的跟孟子針鋒相對的話,不至于在《非十二子》《解蔽》都沒有提到。
對于劉念親的第三個疑問,胡睿認為李斯、韓非等人沒有提到“性惡”二字,是因為“先師的道傳世能得著的,不是必得著的”,這句話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像劉念親所舉的例子,那么多后學、弟子都沒有提到先師的“性惡”,也是不好解釋的。對于董仲舒專門論“性”的《深察名號》《實性》沒有出現“性惡”,胡睿認為“吾國古人事事講忠厚,像‘惡’字這等不好字眼,就怕用得,所以‘惡’字的地方,他就說‘不善’”,姑且不論中國人是否忠厚,如果真像胡睿認為的那樣,《性惡》就不應該出現“惡”字,而應該全部為“不善”,這樣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不過,“惡”、“不善”的說法被林桂榛繼承、發揮。胡睿還對劉念親認為劉向《荀卿序錄》中的36字為后人增加的說法進行反駁,認為“若這一段后人能加上,何以不把《史記》也加上,故意引起人的疑竇呢?”后人在作偽的時候,很難保證沒有漏洞,不能因為有漏洞,反而證明其沒有作偽。
他由于認為《性惡》為荀子自著,所以,還是堅持“性惡論”,但并沒有合理解釋為什么從“本始材樸”到“性惡”。從上述論述來看,胡睿的反駁不能回應劉念親提出的挑戰,但由于“性惡”影響重大,之后的很多學者還是沿用“性惡說”。可以不贊同劉念親的觀點,很多人甚至沒有提到曾經有劉念親、胡睿的爭論,或許沒有看到相關材料吧。
還有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性惡》是荀子的著作,但認識到“性惡”與“性樸”的不同,所采取的的手段是從義理層面調和“性惡”與“性樸”。日本的兒玉六郎在《論荀子性樸說—從性偽之分考察》中“將《性惡》篇開頭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理解為先天性惡論和偽作說并不妥當……應當理解為‘人之本性易為惡,其善者乃是矯性’,這一思想的根本在于,荀況認為人之本性乃是素樸而毫無修飾。是以,講荀況人性論的本質理解為‘性樸說’而取代‘性惡說’,應當更為恰當。”曾振宇的《“性質美”:荀子人性論辯誣》認為“在人性論層面,荀子一再聲明人‘有性質美’,‘性傷’才有可能導致人性趨向惡”;梁濤的《〈荀子·性惡〉引“孟子曰”疏證》則認為“荀子‘反孟子’實際是反外書的《性善篇》。明乎此,圍繞《性惡》所引‘孟子曰’的種種困擾便可迎刃而解了”,《荀子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說》認為“《性惡》的主旨是性惡、心善說”;路德斌的《荀子人性論:性樸、性惡與心之偽—試論荀子人性論之邏輯架構及理路》認為“荀子的人性論并非只是一個‘性惡論’(荀學意義上的‘性惡論’,而不是傳統的、在‘以孟解荀’語境中得到的‘性惡論’),其完整架構是由三個相互關聯且缺一不可的部分組成,即性樸論、性惡論、心偽論。……‘性樸’與‘性惡’,絕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視之,相反,不論在事實上還是在荀學的理路中,二者圓融無礙,邏輯一貫,可以同時成立而并存”。這些文章基本是從思想層面進行論述的,很少有從文獻學、目錄學角度對《性惡》進行詳細論證的,無法解釋如果“性惡”與“性樸”等是統一的,為什么在其他篇章從未出現“性惡”二字;這些文章也僅僅是自圓其說,沒有對劉念親提出的挑戰予以回應,從論辯理論的角度來說,只具有論辯內核,沒有論辯外層。
林桂榛也認為《性惡》是荀子的作品,看到“性惡”與“性樸”之間存在矛盾,但他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揭開兩千年之學術謎案—〈荀子〉“性惡”校正義》認為“‘性惡’系‘性不善’之訛,始訛時間約在西漢末年漢成帝時”,綜觀林桂榛的文章,這一解釋沒有充分的文獻作根據,比如出土的西漢文獻中有《性惡》篇的內容,但其中“性惡”的地方全部為“性不善”。所以,這一看似從文獻學角度出發的解釋,也基本是靠推理,而不是證據。
孫旭鵬《荀子人性論:從“性樸”到“性惡”的內在邏輯》認為“‘性樸’與‘性惡’非但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從‘性樸’到‘性惡’存在者思維發展的內在邏輯……‘性樸’是‘偽’的基礎,‘性惡’是‘偽’的對象”。該文試圖借助“偽”來解決“性惡”與“性樸”的矛盾,但還是沒有直面問題本身,即“性惡”與“性樸”是什么關系。
三、《性惡》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性惡》是荀子的著作,但是也認識到《性惡》的“性惡”與“性樸”之間存在矛盾,并且與荀子的整體思想也是不一致的,他們并不試圖調和“性惡”與“性善”,而是認為《性惡》中提出“性惡”是出于特殊目的,不代表荀子的人性論觀點。
郭沫若《十批判書》認為荀子的人性論有很多矛盾之處,“大抵荀子這位大師和孟子一樣,頗有些霸氣。他急于想成立一家言,故每每標新立異”,“性惡說之在荀子只是一種好勝的強辭”。
謝曉東在《性危說:荀子人性論新探》中提出了“性危說”,認為從善惡的角度分析荀子的人性論不符合荀子的本意:“為了反擊孟子的性善論以及莊子的性善心惡論,荀子必須要強化自己的立場,故而需要某種關于人性的醒目而強硬的觀點”,“性惡說只不過是性危說的一種強勢表達而已”。這一說法基本出于猜測,沒有文本依據,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先秦至西漢中期文獻中沒有提到荀子的“性惡論”。
任何的學術研究,必須有正確的方法,沒有正確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到可靠的結論。現在荀子人性論的爭論,主要在于《性惡》的真偽。上述的諸多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從義理層面論證“性惡”、“性樸”等的矛盾或一致;二,從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角度對《性惡》本身進行研究。要想考證《性惡》的真偽,義理的論證很難得出可靠的結論,甚至可以說這一方法是荒誕的。所以,上述從義理層面論證《性惡》與其他篇章的人性論不矛盾,進而認為《性惡》是荀子所作,再由此論證荀子人性論,可以說陷入了循環論證。文獻真偽的考證比較可靠的方法是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的方法。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討論思想問題,才是比較可靠的方法。當然,也不是方法正確就一定能得出可靠的結論,但沒有正確的方法則基本得不出可靠的結論。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李俊丹)
B222.6
A
1673-2030(2017)02-0043-03
2016-11-01
王澤春(1988—),男,山西祁縣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