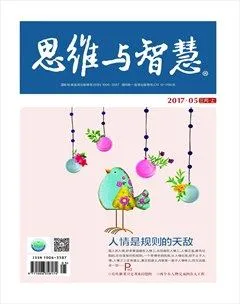珍珠是蚌的眼淚
徐偉
1981年5月,年輕的博士馬歇爾到醫院做實習醫生。一天,他聽說患者湯姆森,吃四環素,居然把胃潰瘍治好了。馬歇爾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興奮,同時,愛思考的他想:四環素是一種殺菌劑,如果四環素是胃潰瘍的克星,這是否意味著,胃潰瘍是由細菌引起的?馬歇爾覺得這是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于是,他向醫院提出要做胃潰瘍細菌培養實驗。負責微生物實驗的老教授,斜了一眼年輕的實習生,答應了。卻沒給他一點點支持,無論技術上,還是人力上。
馬歇爾毫不在意,他知道,自己這樣做,無異于挑戰權威——五十年代,美國著名的胃腸病專家Palmer博士曾研究過一千多個胃病患者的胃粘膜標本,得出結論:由于胃酸的存在,胃部是不會有細菌生長的。30多年來,這已經成為醫學界的共識。
就這樣,馬歇爾一邊給病人看病,一邊收集病人的胃粘膜標本。可是,辛辛苦苦收集了34個,做細菌培養后,卻無一例成功,他沮喪極了!恰逢復活節,馬歇爾放下實驗,回家過節。但是,不甘失敗的他隨意地又做了一個樣本。
6天長假,馬歇爾心心念念牽掛著胃潰瘍細菌培養實驗。 假期歸來,當他抽出細菌培養板時,驚喜得“啊”了一聲。原來,上面有一個菌斑——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培養幽門螺旋桿菌。他永遠忘不了那一天——1982年4月14日。
馬歇爾總結之前失敗的教訓后,又收集了100個樣本,有11個培養成功。然后,他認真整理研究成果,并把論文送到了1982年的澳大利亞消化年會,但慘遭退稿。馬歇爾是個不服輸的家伙,他孜孜不倦地繼續研究,不斷完善成果。一年后,他大膽地向著名的醫學雜志《柳葉刀》投稿。《柳葉刀》被他標新立異的觀點吸引,但謹慎地以“主編通訊”的形式發在雜志上。“幽門螺旋桿菌是胃病的病原體”這一觀點,終于被世人所知。但卻不被認可,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馬歇爾在澳大利亞年會上演講這一觀點,依然被各國醫生嘲笑。
嘲笑對于弱者是絆腳石,對強者是奠基石。馬歇爾想著如何加深研究,拿出更有力的證明。
利用逆向思維,馬歇爾想到把幽門螺旋桿菌接種到動物身上。他先是接種到豬身上,結果實驗失敗了。他沒有灰心,反而更加堅定——用自己做實驗!他首先給自己做了胃鏡,證明自己的胃是正常的。然后,培養了一些從胃潰瘍病人的胃里分離出來的細菌,義無反顧地喝了下去。很快,細菌在他身體里產生了反應,他得了胃炎,“反酸水”成為他的一項新“工作”。他的合作者莫里斯,也自愿以身“試菌”,同樣得了胃炎。好在,兩個人的胃病先后痊愈了。
應該說,馬歇爾的研究成功了,但也仍然不被認可,甚至遭到打壓。因為在當時,用止酸劑治療胃病是國際慣例,在全球范圍內,止酸劑有著30億美元的龐大市場,利益集團豈容四環素取而代之?這種控制長達十年之久,馬歇爾也由學術圈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成長為小有名氣的學者,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他給國會議員寫信,反映情況:止酸劑治療下的胃病,反復發作;而四環素能夠根治胃病。
在馬歇爾的不斷努力下,美國衛生研究院迫于壓力,舉行了聽證會,最終承認了幽門螺旋桿菌是胃病的病原體,必須使用抗生素治療。至此,馬歇爾的研究成果終于成為胃病患者的福音。
在2005年,馬歇爾與合作者因為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獲得了崇高榮譽——諾貝爾醫學獎。有人問:諾貝爾獎遲來了20年,有沒有覺得委屈?馬歇爾豁達地說:“珍珠是蚌的眼淚,珍珠會埋怨蚌曾經的折磨嗎?一切艱難險阻,只能令我們的研究成果更加熠熠生輝。”
(編輯 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