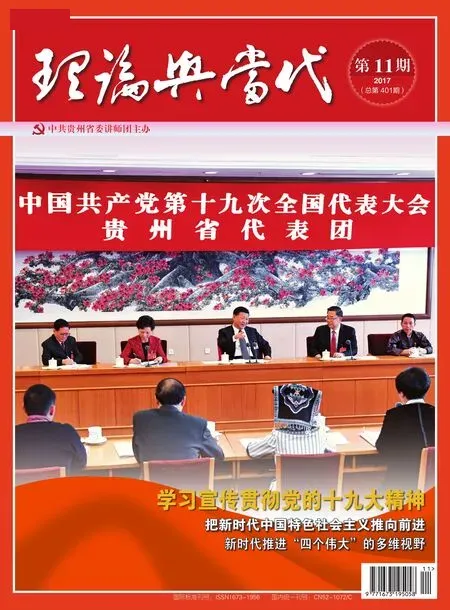葛劍雄談“學”“術”
2017-03-10 14:51:51葛劍雄
理論與當代 2017年11期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葛劍雄在“海上博雅講壇”中指出:今天討論學術至少應該分兩個層面:“學”是學問、做學問的態度,甚至人品,也包括他的思想。“術”就是怎么樣把他的“學”轉化為客觀存在的,能夠影響社會、能夠傳至后代,至少能夠記錄下來的這樣一種產品。歷史上真正對學問貢獻大的人,像司馬遷這樣,哪怕條件艱苦,他也把所有能寫的都寫下來,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下來,留給后人。我們對《尚書》有比較詳細的了解,是因為有人把比較早的文字傳承下來。我們應該感謝一位也許當時并不是一流的學者,他是誰?伏生,秦始皇時代的博士,他這個博士就是專門研究《尚書》的。秦始皇雖然燒了外面的書,但是官方的書他是不燒的,不僅可以保留,而且有人專門去研究,伏生就是研究這個的。秦朝亡了以后他把書藏在墻壁里,他怕書毀掉,就把它全部背了下來。果然,等到戰亂過后,藏在墻壁里的書找不到了。終于,在他90歲的時候等到了漢朝派來的官員,來聽他背書,他的口齒不清了,由他的女兒給他當翻譯,結果《尚書》的文本留下來了。也許在那個時代,秦始皇身邊學問比他高的人多的是,但是他們都只是自娛自樂、自我欣賞,或者在當時博得一個高名。如果沒有人去做這種具體的事情,那么這個文脈就斷了。
猜你喜歡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3期)2021-08-13 08:32:18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小哥白尼(神奇星球)(2020年7期)2021-01-18 05:07:16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娃娃樂園·綜合智能(2019年7期)2019-08-26 09:38:48
民用飛機設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汽車工程學報(2017年2期)2017-07-05 08:13:02
快樂語文(2016年15期)2016-11-07 09:46:39
中國現當代社會文化訪談錄(2016年0期)2016-09-26 08:4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