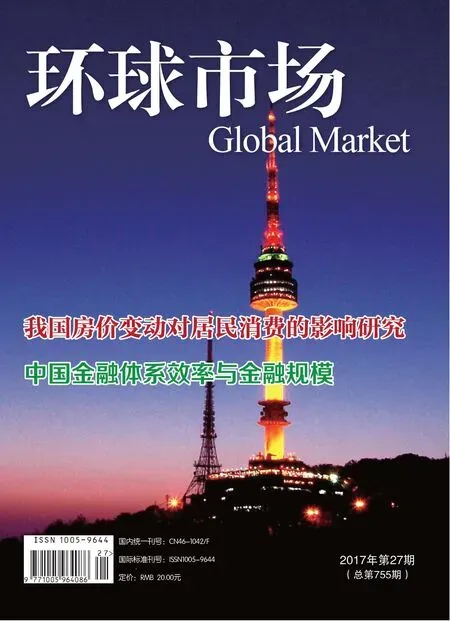小述近現代西方法治與我國的法治國家建設
李逸冰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小述近現代西方法治與我國的法治國家建設
李逸冰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一、法治的起源與近現代西方法治的演變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談到,“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雖然通篇無及“法治”二字,但這段經典論述被公認為是“法治”概念的起源。
從古希臘到近現代,對“法治”二字理解在不同國家得到了分化,其中尤以兩大法系的代表國家,英國與德國為甚。
(一)英國的法治
可以說,英國的法治起源于自然正義和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思想。17世紀,英國憲法學者提出了“rule of law”(法治)一詞。英國的法治發端于對王權的限制,在1688年光榮革命后的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亦稱議會君主制)即是議會權力壓制王權的最佳體現。君主雖然在名義上仍為英國的國家元首,仍承認其王權的世襲制,受到《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等法律的保護,但即便是王位繼承這一“家族內務”,其相關規則仍受制于議會制定的法律之下。王室的代表意義已然超過了其實質意義(發展至今日,英國王宮的部分區域都向世界各國游客開放,以補貼王室的各項開支)。17世紀以來,自由法治在英國得到不斷地鞏固和發展。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法治思想家極力主張保護和擴大公民的自由權利,隨著王權的不斷弱化,政府成為了英國法治的首要限制對象。自由法治思想家們宣稱:政府的權力只能得自人民對統治者的信任,若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人民得撤回其授權。伴隨著對不同時期統治階級的不斷制約,英國完成了對自由法治的歷史演進,自下而上的運動實現了對公民自由權利的保護,也奠定了英國法律至上、抑制專政、司法審查等的法治理念基礎。
(二)德國的法治國
19世紀,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使“Rechtsstaat”(法治國)這一概念誕生在了德國。然而與英國不同,德國的實證法學派認為,法律服從于立法者的權力意志,而非自然正義。雖然德國1919年《魏瑪憲法》中也有“國權出自人民”等積極的表述,但由于缺少自然法學傳統,法律實證主義“惡法亦法”的理念為法律的制訂者(即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者)的提供了自由發揮、恣意妄為的合法外衣。法律實證主義認為不存在正義或權利這類絕對價值。在這種理論的支撐下,法律的制訂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自行決定什么是道德和正義,達到“人法合一”的效果。這其中的近現代典型便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希特勒,在他統治德國時間,“法制普遍,極其敗壞”。法律被恣意踐踏,甚至發生了種族屠殺的這樣駭人聽聞、近現代無出其右的暴行,這與德國法治國的傳統中,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重大缺陷巨有一定關系。
二戰結束后,在總結“實質法治國”的教訓后,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將法治國連同民主、社會、共和、聯邦列為基本法的五大原則。隨著公民基本權利的重新引入,人民在基本法中被賦予了抵抗權,“當法律變成不公正時,抵抗就成為了義務”。有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和捍衛自主權利的手段,德國真正創建了法治國新模式。
二、中國的法治國家建設
(一)從法制國家到法治國家
區別論者認為,法治國中的“法治”二字與rule of law不同,法治國即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國家,僅僅具有工具意義,而法治即法律主治或法的統治(rule of law),則不僅僅指依法而治的意思,而是有目的、有價值的觀念。在如今,盡管“法治國家”的概念被繼續使用,但其中的“法治”已然是“rule of law”之義,“rule by law”常被譯作“法制”。我國“法治”一詞出現的較晚,關于“水治”與“刀制”的區別之說長期以來也是學術界論述的熱點。
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在剛剛結束的十九大中,習總書記用“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概括了5年中我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雖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仍然沿用“依法治國”這一表述,但從建設“法制國家”到建設“法治國家”,從四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論述表明,中國的依法治國已不再是單純的“rule by law”了,從某種角度上,甚至可以認為是意識形態上從“法治國”(原意)到“法治國家”的巨大轉變。
(二)建設法治政府是我國法治國家建設的關鍵一步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總體要求,由于筆者工作于行政執法部門,故試從法治政府角度談一下我國法治國家建設。
政府部門不但是國家行使行政執法權的化身,從廣義上說,又具有一定立法權(行政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同時政府的行政行為和民事行為都應當在法制框架下運行,因此,建設法治政府是建成法治國家的關鍵,政府守法是法治建設的第一要義,政府的決策與執法活動必須合法、守法。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轉變政府職能。一要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對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禁止變相設定行政許可。二要推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建立政府監管部門購買公共服務的制度體系和管理平臺,推動政府及其部門積極規范購買公共服務。完善購買公共服務的規則和監管,推動形成多元化、多樣化的公共服務新格局。三要推進政務公開。健全信息公開工作機制,做好熱點問題應對與信息公開,及時、客觀、準確發布信息。推進行政權力公開運行機制,實現行政權力運行的透明化、規范化。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規范行政決策。一是嚴格規范行政決策程序。對行政監管工作重大事項,要廣泛征求意見,充分進行協商和協調;對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重大事項,要認真組織專家論證、技術咨詢、決策評估;對同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要實行公示、聽證制度,擴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要完善內部民主決策機制,嚴格執行重大行政決策的會議集體討論決定制度。二是完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機制。通過綜合評估確定事項的風險等級,對存在高風險的,要區別情況作出不予實施的決策,或者在調整決策方案、降低風險等級后再行決策。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提高立法質量。一是實行科學的立法工作機制。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將條件成熟、公眾期待、工作急需的項目列入立法計劃。運用科學的立法方式,通過制定、修改、廢止、解釋以及清理、備案審查等多種形式,增強立法工作的協調性、及時性和系統性,及時廢止過時的、與發展不相適應的法律文。樹立科學嚴謹的立法工作作風,加強立法調查研究,加強立法評估、咨詢、論證,加強對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積極探索開展立法后評估工作,尤其要加強對群眾關注度高、對社會影響大的立法項目和地方性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評估,為立法工作提供參考。二是優化民主立法。完善政府部門主導、專家學者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立法工作機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泛凝聚社會共識。拓展公眾有序參與立法途徑,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法律文件均要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完善公眾意見反饋機制,通過適當方式及時反饋意見采納情況。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嚴格執法規范。一是改革完善行政執法模式。按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對分離的原則要求,進一步推行綜合執法、聯合執法、行刑銜接等多種形式的行政執法模式改革。進一步整合執法力量,從體制機制上解決職責交叉、重復處罰、執法標準不統一等問題。探索行政指導、行政獎勵等柔性執法方式。二是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規范化和合理化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執法行為的操作流程,依法履行調查取證、告知、聽證、集體討論決定、爭議處理等行政執法的相關規定。規范行政執法裁量權,正確掌握行政執法尺度,防止裁量權的濫用。
建設法治政府,要求加強權力監督。一是強化行政監督。綜合運用執法考評、執法監督檢查等形式,增強行政監督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自覺接受法律監督,加強執法監察、廉政監察和效能監察。重視輿論監督,對人民群眾檢舉、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應當認真調查處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繼續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二是加強行政復議與應訴。開展行政復議工作規范化建設,暢通行政復議渠道,依法受理符合法定條件的行政復議申請。全面運行使用我局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信息管理系統,規范行政復議案件的審理工作,提高行政復議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實現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統一,努力做到定紛止爭、案結事了。積極配合司法部門做好本單位相關案件的行政應訴工作,按規定提交相關證據材料并出庭應訴,自覺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裁定。
李逸冰,女,漢族,1983年出生,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2014級法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