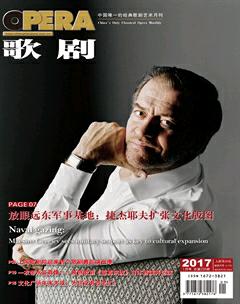《遠方的愛》首演:薩里亞霍成為大都會歷史上第二位演出作品的女性作曲家
謝朝宗
芬蘭作曲家薩里亞霍(Kaija saariaho)的歌劇《遠方的愛》(L'Amour de Loin),是21世紀最受好評的創作之一。自從2000年在薩爾茨堡音樂節首演以來,已經在法國、德國、瑞士、芬蘭、挪威、英國、加拿大等地演出,在美國也有圣達菲歌劇院(三個委約創作單位之一)和阿斯本(AsDen)的觀眾看過,而且這許多后續的演出,都是不同的制作,可見其他歌劇院認可其藝術價值愿意投資。本季大都會歌劇院終于排出此戲,算不得是石破天驚。
遲到好過不到。薩里亞霍是當代重要的作曲家,《遠方的愛》是她首部歌劇。據說她很長一段時間都拒絕歌劇院的邀約,因為她覺得找不到用音樂表現戲劇的方式,直到她看到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導演的梅思安的《阿西西的圣方濟各》,讓她了解有可能寫出沒有傳統情節的歌劇,她也通過塞拉斯,找到長居法國的黎巴嫩作家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創作出這部作品。
薩里亞霍與馬盧夫選了12世紀吟游詩人諾弗雷·魯德爾(Jaufré Rudel)的傳說編出歌劇故事。諾弗雷身為阿基坦(Aquitaine,今法國南部)的王子,過厭了錦衣玉食的日子,開始向往一個理想的、位于“遠方的愛”(他稱這個女子要“美麗,不因美而驕傲;高貴,不因貴而驕傲;圣潔,不因圣而驕傲”)。他的朝臣嘲笑他是做白日夢,但是一個旅行的朝圣者卻說,在海的另一邊,真有這樣一個女子存在,諾弗雷從此再也無法排除這個念頭。
朝圣者跨海到特里波利(Tripoli,今黎巴嫩境內),告訴克萊曼斯女伯爵(Clémence),諾弗雷作了許多詩歌頌贊她,引得女伯爵也開始想象這個遠方的詩人王子是什么樣子。朝圣者再回到宮殿,告訴諾弗雷,女伯爵已經知道了他的愛慕之心,惹得他再也受不了兩地相思,決定跨海去見克萊曼斯,但是在途中他開始后悔,等到了特里波利已經病得奄奄一息,最終死在克萊曼斯的懷里。
《遠方的愛》幾乎沒有傳統戲劇的情節可言,劇中人物都是說得多做得少,而且講的話大部分是讓情節暫停的獨白,而不是推動情節的對話。作為穿針引線的人的朝圣者,與王子和女伯爵的對話,很有點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里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對話的效果:聽起來是同一個主題,實際上是各說各的。“得不到的愛”不是前所未見的歌劇題材,但這里阻擋兩人的,不是倫理道德,不是國仇家恨,甚至不是距離,而似乎是兩人都寧愿坐在家里自怨自嘆而不愿意面對現實。
從音樂戲劇的角度來看,《遠方的愛》不能讓人屏息凝神期待接下來的情節發展,音樂的節奏、輕重、緩急都沒有很大的變化。但是薩里亞霍很能掌握整體的情調,音樂從頭到尾有一種瑩亮的感覺,仿佛水波蕩漾(這可能是她使用電子儀器的效果)。打擊樂器不是為其音量,而是為其作金石之聲。人聲雖然不走傳統的調性,但線條委婉、情致纏綿。
人聲角色除了三個獨唱人物,還有合唱團,分別是諾弗雷宮廷里的男聲與克萊曼斯方面的女聲。唱諾弗雷的是男中音埃里克·歐文(Eric Owen),他把所有的音樂都唱得悅耳動聽,但似乎并沒有深入角色內心。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受限于作品本身,因為諾弗雷雖然看來是主動的一方,但我們并不知道他真正的動機和目的,感到的只是他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對生命的不滿足。朝圣者是一個女中音的角色,他的音樂比較平鋪直敘,沒有太多可稱為詠嘆調的地方,但塔瑪拉·芒福德(Tamara Mumford)唱得很悠揚。克萊曼斯在諾弗雷死后有一大段質問命運的詠嘆調,這是全劇最情感激昂的唱段,女高音蘇珊娜·菲利普斯(Susanna Phillips)以清麗的聲音、層次豐富的詮釋,展現了音樂的力量。指揮是作曲家的芬蘭同胞蘇珊娜·馬爾基(Susanna Malkki),對這段音樂的起伏有良好的控制,充分傳達出夢幻的美。
海是歌劇里最重要的意象,演這出戲一定要解決如何表現海的問題。當年塞拉斯的首演用了真的水,大都會找來的加拿大劇場導演羅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說他不想用真水,因為“水像動物和小孩一樣,一上了舞臺就很難控制”。他把整個舞臺搭成一排不斷升高的樓梯(讓人想起譚盾的《秦始皇》十年前首演時的布景),階沿上鑲滿了2.8萬個LED燈,成為一片燈海,透過色彩、明暗的變化,表現了大海的各種樣貌,時而晴空麗日、時而波濤洶涌、時而月光照得夜色流麗、時而晚霞五彩炫爛,有時還有魚躍波浪間,效果十足。只是,在漆黑的劇場里看久了,有點眼花,但是他給這個很靜態的歌劇帶來一些堂皇富麗感,符合大都會的氣勢。比較可以討論的是舞臺中央的一個巨大的翹翹板起重機,讓諾弗雷和克萊曼斯站在上面,代表海的兩岸。其用意或許是對的,但起重機笨重的樣子,破壞了燈光塑造出的夢幻感。
薩里亞霍是有史以來第二位在大都會演出的女性作曲家,距1903年演出《森林》(Der WaM)的艾塞爾·史密斯(Ethel Smyth),已經超過100年,受到批評是難免的。但與其說是大都會有意冷落女性作曲家,真正的原因是大都會在演出當代歌劇的問題上一向就偏保守,而流傳至今的傳統歌劇劇目里沒有女作曲家的作品,大都會當然排不出來。
《遠方的愛》演出同時,傳出取消與阿根廷作曲家奧斯、瓦爾多·格利約夫(Osvaldo Golijov)的委約,是排演新作品困難的寫照。在千禧年前后很受重視的格利約夫近年來面臨創作瓶頸,無法在預定時間交出作品,不是大都會的錯。劇院經理彼得·蓋爾伯(Peter Gelb)一再強調新作品的重要,也確實想了一些方法鼓勵創作,但他任職十年至今還沒有一部能傳世的全新歌劇,是音樂界和觀眾都很焦急的問題。錢財人才大都會都不缺,結果就是不讓人滿意,難道大都會真是與當代作曲家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