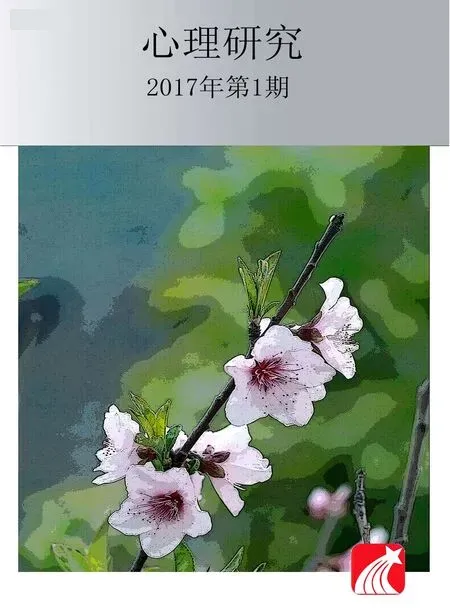物質主義作為自我建構的工具:功能主義的研究視角
鄭曉瑩 阮晨晗 彭泗清
(1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 300073;2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 100871)
物質主義作為自我建構的工具:功能主義的研究視角
鄭曉瑩1阮晨晗2彭泗清2
(1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 300073;2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 100871)
物質主義通常被視為一種相對穩定、強調物質財富重要性的個人價值觀或目標導向,對個人及社會均有負面影響。近年來,有學者指出這種定義的局限性,將物質主義重新定義為心理需求的表達工具,強調其作為構建和維持自我身份的手段和方式,從而拓寬了物質主義的表現形式和研究范疇。通過總結和對比上述兩種研究取向在物質主義的內涵、成因及影響等方面的不同,提出未來研究應致力于整合不同理論視角,更加系統全面地理解物質主義全貌。
物質主義;價值觀視角;功能主義視角;心理需求;自我
1 引言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既是經濟迅速騰飛的30年,也是中國人對物質成功的欲望不斷膨脹的30年。根據財富品質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15年中國奢侈品報告》,中國消費者在2015年買走了全球約46%的奢侈品,消費金額達1167億美元[1]。盡管有評論認為物質主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助推作用,但就個體而言,物質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又有什么樣的影響?對物質主義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述問題。
大量文獻對物質主義的概念內涵、結構測量、前因后果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探討。盡管研究者們對物質主義究竟是個人特質,還是價值觀,抑或是由外部動機驅動的目標導向等問題各執一詞,但他們都或明確或隱晦地在“物質主義是相對穩定的個體特征”這一命題上達成共識,并且傾向于認為物質主義對個人及社會均有負面影響[2-5]。為了行文比較的方便,我們把這些相對早期的、將物質主義視為個體特征的研究取向統稱為傳統研究視角。
近年來,以營銷領域著名學者Shrum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對上述傳統研究視角下的物質主義內涵提出挑戰。他們指出,傳統研究視角對物質主義的定義過于狹窄,限制了人們理解物質主義這一復雜概念的多面性[6,7]。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先驗性地假定物質主義是有害的,這不利于研究和了解物質的正面價值。事實上,有關補償性消費的文獻發現,追求物質擁有的行為并不總是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有時也能幫助個體建構積極的自我認識[8]。第二,傳統研究認為物質主義是相對穩定的個人特征,然而許多研究卻發現人們的物質主義會隨著實驗情境的變化而暫時性地增加或降低[9,10]。因此,強調物質主義的穩定性將不利于深入探討物質主義產生的根源。此外,將物質主義看作個體差異變量限制了人們對其背后動機因素的挖掘。基于上述分析,Shrum等人提出從心理需求與自我建構的角度重新界定物質主義的內涵與外延,區分由不同心理動機所引發的物質主義行為,從而拓寬了物質主義的表現形式和研究范疇。由于這一取向強調物質主義作為構建和維持自我身份的手段和方式,因此也被稱為功能主義研究視角(functional perspective)[6,7]。
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和總結物質主義的功能主義研究視角的主要理論與觀點,并將之與傳統的物質主義研究進行對比,評述這種新的研究取向的優勢與劣勢,并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2 物質主義的定義
2.1 傳統研究視角下的定義
物質主義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1]。然而,由于不同流派的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學術界對于物質主義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例如,Belk認為物質主義是一系列反映個體物質導向的性格特點的組合[2]。Richins和Dawson將物質主義定義為一種強調擁有物質和財富的重要性的價值觀[5]。Kasser,Ryan和Inglehart等人則從外部動機和內部動機的角度提出,物質主義是指強調諸如財務成功、物質享受等外部動機的導向[3,4]。
傳統的有關物質主義的研究大多采用了Richins和Dawson的定義,將物質主義看作是一種對物質財富重視程度的個人價值觀。Richins和Dawson還開發了專門的量表用以測量物質主義價值觀(materialistic value scale,MVS),提出物質主義包括 “物質—中心論”(centrality)、“物質—幸福觀”(happiness)、“物質—成功觀”(success)等三個維度。其中,“物質—中心論”是指個體是否認為物質財富在生活中占據中心位置;“物質—幸福觀”是指個體是否相信物質擁有是獲取幸福的重要途徑;“物質—成功觀”是指個體在多大程度上將擁有物質和財富作為評價自己和他人是否成功的標準[12]。該量表由于具有較好的信效度而被廣泛使用。在這種觀點下,物質主義者往往具有如下人格特征:(1)將物質追求作為生活的中心,而較少關注社會關系和生活體驗;(2)自私小氣,不愿意將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與他人分享;(3)容易對他人所擁有的物質產生嫉妒[2,5]。
2.2 功能主義視角下的定義
以Shrum等人為代表的功能主義觀點則將物質主義定義為“個體在多大程度上試圖通過獲得和使用具有理想化的象征價值的產品、服務、體驗或關系來建構和維持自我”[6]。與傳統研究視角不同,該定義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第一,強調物質追求行為背后的自我需求與心理動機,而非其人格特征或外在表現。傳統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在于區分什么樣的價值觀念或行為表現是物質主義,以及物質主義者有哪些特點(如嫉妒、小氣等)。而功能主義視角則提倡通過心理動機來辨別物質主義行為。根據動機的不同,同一行為(如奢侈消費)既可能是物質主義(如以向他人炫耀為目的),也可能是非物質主義行為(如以追求功能質量為目的);而某些看似非物質化的行為,也可能因為動機的差異而被認為是物質主義行為。例如,許多人常常熱衷于暢談自己與某些社會名流、明星人物的交好,以此來炫耀自身的社會網絡與人脈關系。在Shrum看來,這種基于炫耀動機的攀關系行為也應算作物質主義,其功能也是幫助個體建構自我形象。
第二,功能主義視角強調物質的符號價值與象征性意義及其對自我建構的作用。正如法國著名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所指出的那樣,消費已經不再是物的消費,而是符號消費,其本質是自我的建構與表達[12]。事實上,研究者曾對“工具性物質主義(instrumental materialism)”和“終極性物質主義(terminal materialism)”進行了區分:前者是指將物質消費作為實現其他生活目標的手段(注重“doing”,如購買昂貴的汽車是為了讓家人安全出行),后者是指將物質財富的擁有作為追求本身(注重“having”,如購買昂貴的汽車是為了顯示作為擁有者的地位)[13]。而在Shrum的定義里,物質主義行為是指終極性物質主義。由于工具性物質主義追求的是物質的功能實用價值,與自我建構無關,并不算是真正的物質主義行為。
第三,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功能主義視角的研究焦點從傳統的“誰是物質主義者”更多轉向“為什么會出現物質主義”以及“人們什么時候會表現出物質主義行為”。根據功能主義的觀點,物質主義是人類基本心理需求的符號意向性表達,所以每個人都有潛在的物質主義傾向和動機,但這種傾向并不會隨時表現出來。因為滿足心理需求的方式和途徑有很多種,物質主義只是其中一種。如果心理需求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滿足,那么便不太會以物質主義的方式去表達。這一結論在補償性消費文獻當中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實證支持[8]。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講,有關物質主義的研究不僅要關心 “誰”的問題(who is materialistic),更要回答“為什么”以及“什么時候”的問題(why and when)[10]。
為了更好地說明功能主義視角與傳統研究視角的區別和聯系,我們通過圖1的示意來輔助闡釋。功能主義視角的理論基礎是更廣義的人類動機系統(human motivational system)[10]。這一系統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處于最核心、最基本的是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動機(need and motive)。盡管學者們對于這些基本需求的具體內容(如能力需求、關系需求、控制需求等等)有不同見解,但他們都普遍認同的一個觀點是,這些基本需求都與自我緊密相關[14-17]。如果這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就會出現某些心理不適甚至行為異常(malfunctions)。因此,人們總是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滿足這些需求。這些需求滿足的手段和方式便構成第二層目標系統(goal system)。與需求系統相比,目標系統更加具體化、外顯化和多樣化。例如,滿足自我能力的需求既可以通過實現內部目標(如任務成就感)完成,也可以通過追求外部目標(如他人認可)實現。對不同目標的長期追求便逐漸固化為第三層面的價值觀系統(value system),表現為個體對不同目標對象賦予的權重。而這些目標追求與價值觀念最終通過各種行為方式得以表達。此外,自身以外的環境因素(如情境、他人、社會習俗等)會與上述系統發生交互影響。

圖1 動機系統示意圖
基于這一動機系統劃分,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傳統的有關物質主義的研究重點是目標和價值觀層面,以及由這兩者引發的外在行為表現等方面的內容,而較少關注更深層次的與自我有關的心理需求的作用。與此相反,功能主義視角弱化了對物質主義表現形式(目標、價值觀、行為)的關注,而強調驅動這些表現形式背后的自我需求與動機。事實上,功能主義視角所提出或提倡的部分觀點在以往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被提及或探討。然而這種討論始終沒有成為物質主義研究的主流,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隨著對物質主義表象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更深層次的需求系統的關注越來越多。因此,Shrum等人將這些零散的研究思想歸納總結為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邏輯體系,并加入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3 物質主義的成因
3.1 傳統視角下的相關研究
有關物質主義的傳統研究多關注成長環境、生活經驗、社會學習等因素如何影響個體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例如,Inglehart曾提出物質主義形成的社會化理論,認為在貧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們由于長時間的物質匱乏,從而內化了一種主觀的經濟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持續存在,并導致他們對物質的欲望較一般人更高,最終形成了物質主義價值觀[3]。這一理論得到一些實證證據的支持。一項針對英、德、意、荷、比、法等西歐六國的實證調查發現,相對于二戰結束后出生的人們,在二戰經濟匱乏時代出生的人們的物質主義傾向普遍更高[3]。類似地,Kasser,Ryan,Zax和Sameroff發現,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青少年當中占據主導地位[18]。
此外,還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教養方式也會影響個體的物質主義價值觀[18-20]。例如,采用冷漠、獨裁、控制的養育方式的父母,其孩子長大后往往重視物質和財富的成功,而輕視其他親社會性價值觀。家庭環境對子女物質主義形成的影響還表現在家庭成員的榜樣角色與社會學習過程。家庭成員的言行舉止作為兒童早期模仿和學習的主要對象,會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孩子,并最終內化為自我的價值觀與行為法則。Kasser等人研究發現,子女的價值觀結構與其母親的價值觀高度正相關。如果母親重視和追求經濟成功,其子女往往也表現出較高的物質主義傾向[18]。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物質化的教育方式(material parenting,即通過物質給予和獎勵的方式表達對子女的愛)會提高下一代的物質主義傾向[20]。
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社會習得途徑還包括同伴影響和媒體傳播。Chan和Prendergast研究表明,與同齡人的社會比較是促進個體物質主義形成的重要因素[21]。Gerbner等人提出的培養理論(cultivation theory)認為,電視媒體,尤其是電視廣告常常讓消費者錯誤地認為社會是普遍富裕的。這種觀念在個體觀看電視時不斷得到強化,并被同化到個體價值觀結構當中,最終形成較高的物質主義傾向[22]。Shrum,Burroughs和Rindfleish研究發現,個體物質主義傾向高低與其觀看電視的時間長短呈正相關,即看電視越多的人物質主義傾向越高,且觀看者投入的注意力越多,電視對物質主義的影響越大[23]。
3.2 功能主義視角下物質主義的形成機制
與傳統視角關注價值觀形成途徑不同,功能主義視角強調引發物質主義行為的心理需求。根據Shrum等人的定義,物質主義的主要功能是幫助消費者建構和維持自我(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elf)[6]。人們總是試圖保持積極正面的自我身份感知(self-identity)[14,24],而物質、產品、經驗和服務等是幫助消費者建構這些身份認知的重要手段和工具[25]。因此,人們的物質主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一定的心理需求。當某一心理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時,人們便會產生相應的身份建構或修復動機,進而促進物質主義行為的產生。
與上述觀點一致,有關補償性消費(compensatory consumption)的研究發現一些實驗條件或情境確實會暫時性地引發物質主義動機,并導致物質主義行為[26-30]。補償性消費是指通過消費行為來彌補某些心理缺失或威脅,強調消費行為作為滿足需求的一種替代性手段和工具。例如,Rucker和Galinsky發現,當被試感知到權力缺失(powerless)時,他們會更希望通過獲得具有地位象征性意義的產品來試圖重塑權力感[31]。Sivanatha和Pettit明確指出,有地位象征意義的產品能夠幫助保護和肯定被威脅的自我價值感。他們通過實驗發現,在智力測驗中得到失敗反饋的被試更愿意為能夠象征地位的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32]。類似地,Lee和Shrum發現,被他人忽視的被試會通過炫耀自己所擁有的物質試圖重新獲得他人的關注[33]。
然而,在使用上述心理動機框架來理解物質主義行為的形成機制時,需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物質主義行為并非是滿足這些心理需求的唯一方式,人們也可能通過其他非物質性的行為實現同樣的目標。例如,個體可以通過購買化妝品或進行整容手術來增加自己的外表吸引力,提高自尊感 (body self esteem);也可以通過鍛煉和節食來塑造體形,達到類似的自我提升目的。功能主義視角認為后者并不涉及消費和物質獲得,因此不屬于物質主義范疇。第二,某一行為是否屬于物質主義取決于引發該行為背后的動機,而不是行為本身。這種動機既包括社會信號動機(social-signaling motive),也包括自我信號動機(self-signaling motive)[34,35]。前者指為了在他人面前彰顯某種身份特征而表現出來的物質消費行為,如炫耀性消費;后者是指滿足自己對自我的認知建構的需求而獲取或消費特定物品的行為,如自我獎賞式的享樂消費。與傳統研究視角關注由社會信號動機引發的物質主義行為不同,功能主義視角認為基于上述兩種心理動機的消費行為均屬于物質主義行為,而以純粹的基本功能需求為目的的購買或消費行為并不屬于物質主義的范疇。例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消費者購買一輛昂貴汽車的目的是為了給家人提供安全的出行保障,那么并不認為該購買行為是物質主義的表現。
4 物質主義的影響
有關物質主義的傳統研究大多認為,物質主義是不健康的價值觀,對個體和社會均有負面影響[36]。從個體層面來講,研究發現物質主義與自尊、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之間呈負相關關系[5,37]。物質主義較高的人往往有更大可能性出現生理性和心理性疾病[38],更可能進行沖動性購買等[39]。從社會層面上來講,對物質的追求弱化了人們對人際關系、社會問題、生態環境等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問題的關注與投入,進而導致更少的親社會行為和公民責任感擔當[37,38]。
盡管許多實證研究都較為一致地支持“物質主義降低幸福感”這一觀點,但功能主義觀點指出,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的明顯局限:由于將物質主義作為個體穩定的價值觀變量,且關注的是兩者之間的長期相關,因此難以說明是物質主義導致了更低的幸福感這一因果關系。他們進一步提出,物質主義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是正向還是負向取決于引發物質主義行為的動機是什么。他們區分了三個大類的消費動機:身份建構(identity construction),享樂/內在動機(hedonic/intrinsic motive)和滿足基本需求(meet basic needs),并且指出:(1)當消費的動機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如,購買昂貴的汽車是為了保證質量安全),這種消費行為會對幸福感有積極影響。但從功能主義視角來看,這種消費不應看作是物質主義行為。(2)當消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內在的自我追求或自我享受動機(如,購買昂貴的汽車是為了向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或為了追求愉悅的消費體驗),這種消費也會對幸福感有積極影響。(3)消費的身份建構動機又可以進一步分為向他人展示身份 (others-signaling)和向自我展示身份(self-signaling)兩種。基于向他人展示身份的動機的消費行為往往對幸福感有消極影響,因為此時個體對自我的感知完全依賴他人的評價,而他人評價往往難以預測且容易改變,因此不利于積極穩定的心理建構過程。而基于向自我展示身份的動機的消費行為被認為對幸福感會有積極影響。例如,以自我補償為目的的產品選擇行為確實能夠幫助消費者建立積極的自我概念[40]。
5 對功能主義視角的評述及未來研究方向展望
與傳統的價值觀視角相比,功能主義研究視角大大拓寬了物質主義的內涵與外延,強調了物質主義行為發生的心理動機,并且根據動機的不同區分了物質主義行為對個體幸福感的可能影響,肯定了物質主義行為在特定條件下對消費者心理建構的積極作用,對于理解物質主義和促進相關的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視角,該領域尚存在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第一,物質主義的范疇界定。功能主義視角認為,根據動機不同,同一行為既可能是物質主義的表現,也可能是非物質主義的范疇。例如,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消費不應被看作物質主義行為。從概念上來講,該定義突出物質的象征意義作為物質主義的核心表現,進而將日常消費行為與物質主義行為,積極的物質主義行為與消極的物質主義行為進行了有效的區分。然而,從研究操作上來講,由于心理動機往往具有主觀性和隱匿性,因此難以捕捉和識別。這一特點進一步導致測量上的困難:一方面動機的作用過程可能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個體自身往往對此毫無察覺,因此難以通過口頭匯報表達出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會贊許性等壓力,個體常常不愿意承認或表達那些以向他人炫耀身份地位為目的的心理動機。上述難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準確辨別物質主義的能力及相關的拓展研究。因此,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細化不同動機的外在表現形式,開發相應的測量方法和工具有效捕獲引發不同物質主義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從而為引導消費者行為提供具體可行的建議和意見。
第二,傳統研究視角與功能主義視角的整合。物質主義是一個多成分、多維度的概念,單純強調其作為個體價值觀或自我建構的工具均不利于理解物質主義的全貌。傳統研究視角過于強調物質主義的穩定性與長期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理解物質主義的形成動機,及可能帶來的各種短期影響。相反,功能主義視角強調動機的可變性和動態性,重視情境性的目標追求過程及其行為表現,而忽略了物質主義作為價值觀的可能形成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群體及他人所起的社會化作用。因此,未來研究應考慮如何將這兩種研究取向有機地整合在一起。一個可能的突破方向是將物質主義觀念與物質主義行為加以區分,既承認物質主義作為價值觀念的相對穩定性,又肯定物質主義表現形式的動態多變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從情境性動機引發的短時物質主義傾向到相對穩定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過程與機制。
第三,除了價值觀成分和動機成分外,物質主義是否還應包含情感成分?事實上,現有的兩種研究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享樂成分在物質主義定義中的存在性。例如,Richins和Dawson開發的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當中就有相應題項 (如,“我非常享受在沒有實用價值的物品上花錢”)[5]。類似地,功能主義視角也將享樂作為引發物質主義的三大心理動機之一。然而,已有研究中只是將享樂作為物質主義的測度之一,而并沒有將其作為和動機、價值觀平行的概念維度。我們認為,情感享樂成分作為物質主義的重要內涵之一,理應與以價值觀念為主的認知成分和以目標追求為主的動機成分共同構成物質主義內涵。其中,認知成分強調個體對物質重要性的主觀信念,情感成分強調個體從物質消費中獲得的愉悅感,動機成分體現個體追求物質背后的心理動機。這種由認知(價值觀念)、情感(追求享樂)和動機(目標完成)三成分構成的研究視角將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理解物質主義的多層次內涵。
第四,重塑社會大眾對物質主義的認知與印象,引導居民進行合理健康消費。一直以來,“物質主義”是一個被嚴重污名化的詞匯。提到物質主義,大多數人都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鋪張、浪費、奢靡、墮落、自私、小氣等一系列負面特質。產生這種聯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傳統研究視角下對物質主義的狹義定義所致。在這種污名化的社會包袱下,物質消費往往產生強烈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方面出現各種中國式炫富、未富先奢等以“顯擺”為特征的消費行為,這些消費者以奢侈的“物質主義”生活方式為榮,博取他人的羨慕與嫉妒;另一方面則出現壓抑消費、過度節儉的以“克制”為特征的反消費行為,這些消費者厭惡甚至憎恨物質主義者。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極易導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與隔閡,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根據物質主義的功能性視角,物質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可以是中性的,其帶來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關鍵取決于其背后的心理動機。因此,如何改變和重新樹立公眾對物質主義的認識將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只有人們對物質追求行為有相對客觀的認識,才能有效地落實國家構建和諧消費社會的主張。
第五,探討新的社會發展階段下中國消費者物質主義的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正如上文所述,過去有關物質主義的傳統研究多強調消費的他人信號動機,即通過物質的擁有和消費向他人展示身份地位。因此,許多物質主義行為往往表現出趨同性和攀比性,即“你有的我也要有”。然而,時下的中國社會,整體財富增長,物質豐富,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尋求個性化的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這一點在年輕一代消費者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種背景下,物質主義的表現形式不是趨同,而是差異化,即追求自我獨特性。這種對獨特性的尋求既可能是出于他人信號動機,也可能出于自我信號動機。根據功能性視角的觀點,這種物質主義表現形式根據其動機不同可能會帶來不同的影響:如果是基于自我信號動機,則會對個人幸福感產生正面影響;如果是基于他人信號動機,則會對個人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1 財富品質研究院.2015年中國奢侈品報告,2015.
2 Belk R W.Materialism:Trait aspects of 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5,12(3):265-280.
3 Inglehart R.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4 Kasser T,Ryan R M.A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Correlates of financial success as a central life aspir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3,65(2):410-422.
5 Richins M L,Dawson S A.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2,19(3):303-316.
6 Shrum L J,Wong N,Arif F,et al.Reconceptualizing materialism as identity goal pursuits:Functions,processes,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3,66(8):1179-1185.
7 Shrum L J,Lowrey T M,Pandelaere M,et al.Materialism: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2014,30(7):1858-1881.
8 鄭曉瑩,彭泗清.補償性消費行為:概念、類型與心理機制.心理科學進展,2014,22(9):1513-1520.
9 Kasser T,Sheldon K M.Of wealth and death:Materialism,mortality salience,and consumption behavior.Psychological Science,2000,11(4):348-351.
10 Kasser T.Materialistic values and goal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16,67,489-514.
11 Burroughs J E,Rindfleisch A.What welfare? On the definition and domain of consumer research and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materialism.In Mick D G,Pettigrew S,Pechmann C C,and Ozanne J L(Eds.),Transformative consumer research for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well-being.New York:Routledge,2011:249-266.
12 讓·鮑德里亞(Baudrillard,J.).消費社會 (劉成富,全志鋼 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3 Csikszentmihalyi M,Rochberg-Halton E.Reflections on materi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1978,70(3):6-15.
14 Steele C M.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8,21:261-302.
15 Deci E L,Ryan R M.The“what”and“why”of goal pursuits: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Psychological Inquiry,2000,11(4):227-268.
16 Baumeister R F,Leary M R.The need to belong: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Bulletin, 1995,117(3):497-529.
17 Williams K D.Ostracism.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7,58(1):425-452.
18 Kasser T,Ryan R M,Zax M,et al.The relations of mater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o late adolescents’materialistic and prosocial value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5,31(6):907-914.
19 Flouri E.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and fathers’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materialist value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4,25(6):743-752.
20 Richins M L,Chaplin L N.Material parenting:How the use of goods in parenting fosters materialism in the next gener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5,41(6):1333-1357.
21 Chan K,Prendergast G.Materialism and social comparison among adolescents.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07,35(2):213-228.
22 Gerbner G,Gross L,Morgan M,et al.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Cultivation processes.In BryantJ,Zillmann D,and Oliver M B (Eds.),Media effects: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Mahwah,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2002:43-67.
23 Shrum L J,Burroughs J E,Rindfleish A.Televison’s cultivation of material valu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5,32:473-479.
24 Swann W B,Bosson J.Self and identity.In S T Fiske,D T Gilbert& G Lindzey (Eds.),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McGraw-Hill,2010.
25 Belk R W.Possessions and the extended self.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88,15(2):139-168.
26 Kim S,Gal D.From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to adaptive consumption:The role of self-acceptance in resolving self-deficit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4,41(2):526-542.
27 Kim S,Rucker D D.Bracing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orm: Proactive versus reactive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2,39(4):815-830.
28 Lee J,Shrum L J.Self threat and consumption.In Belk&Ruvio(Eds.),Identity and Consumption.New York:Routledge,2013:216-224.
29 Lisjak M,Bonezzi A,Kim S.Perils of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Within-domain compensation undermines subsequent self-regul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5,41(5):1186-1203.
30 Rucker D D,Galinsky A D.Compensatory consumption.In Ruvio A A&Belk R W (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identity and consumption.NewYork,NY:Routledge,2013:207-215.
31 Rucker D D,Galinsky A D.Desire to acquire:Powerlessness and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8,35(2):257-267.
32 Sivanathan N,Pettit N C.Protecting the self through consumption:Status goods as affirmational commoditie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46(3):564-570.
33 Lee J,Shrum L J.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ersus charitabl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A differential needs explan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2,39(3):530-544.
34 Dhar R,Wertenbroch K.Self-signaling an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emptation in consumer choice.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2,49(1):15-25.
35 Richins M L.Materialism,transformation expectations,and spending:Implications for credit use.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2011,30(2):141-156.
36 李靜,郭永玉.物質主義及其相關研究.心理科學進展,2008,16(4):637-643.
37 Burroughs J E,Rindfleisch A.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conflicting valuesperspective.Journalof Consumer Research,2002,29(3):348-370.
38 Roberts J A,Clement A.Materialism and satisfaction with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nd eight life domain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7,82(1):79-92.
39 Dittmar H.Compulsive buying-a growing concern?An examination of gender,age,and endorsement of materialistic valuesaspredictors.British Journalof Psychology,2005,96(4):467-491.
40 Gao L S,Wheeler S C,Shiv B.The “shaken self”:Product choices as a means of restoring self view confidence.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9,36(1):29-38.
Materialism as a Tool of Constructing the Self:The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Zheng Xiaoying1,Ruan Chenhan2,Peng Siqing2
(1 Business School,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Traditional research often takes materialism as a relatively stabl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people place on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wealth,which poses detrimental effects on personal and societal well-beings.Recently,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definition and redefine it as a way to express psychological needs.They emphasized its role in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self-identity,and thus broaden the representation form and scope of materialism research.By summarizing and comparing between the aforementioned two research orientations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anings of materialism,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this review is to provide an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dimensions and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for understanding materialism.
materialism;values;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psychological needs;self
鄭曉瑩,女,講師。Email:xiaoying.zheng@nankai.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