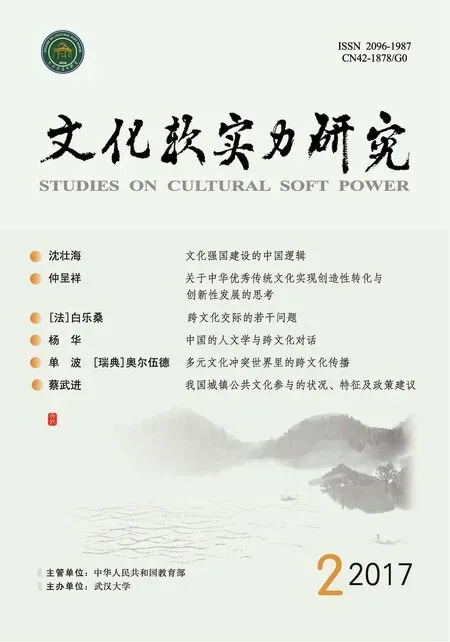跨文化交際的若干問題*
——以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為例
[法]白樂桑
?
跨文化交際的若干問題*
——以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為例
[法]白樂桑
語言的跨文化傳播,不僅是語言的接觸,也是思維方式的接觸,還是文化的接觸。在跨文化交際中,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缺乏認識,且教育傳統和思維方式存在不同,往往會產生一些障礙,導致交際不得要領或失誤,引起誤解甚至沖突。因此,語言傳播要有好的效果,必須了解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不同的思維方式,注意換位思考,重視多元語言文化意識的培養。
語言傳播 跨文化交際 中國語言文化 語言距離 換位思考
我們知道,語言是一個非常豐富的現象和人所特有的一種能力。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是錯綜復雜的。目前,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促使國際交往日趨頻繁,而且更加重要,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缺乏認識,由于教育傳統和思維方式的不同,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會產生一些障礙,導致交際不得要領或失誤,引起誤解甚至沖突。我們將主要以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為例來具體分析幾個重要問題,并提出一些克服跨文化交際失誤和沖突的策略。
簡要地說語言和文化傳播包括學習、教學的意義,我覺得如果從溝通交流方面說,可能我們要關注的是所謂的交際能力。可是,任何一門語言、任何一種文字跟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有非常微妙的關系,所以我提出的第二點,就是思維方式的接觸,跟所謂的思維能力是有密切的關系的。第三,除了語言的接觸,除了思維方式的接觸,還有一個文化的接觸。文化的接觸,換成能力來講,就是我們現在經常探討的跨文化能力問題。換句話說,我覺得很重要,其實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同時也是會產生最大的障礙的一點,就是換位思考的能力到底如何。這三個層面就構成現在和今后文化傳播也好、教學也好都需要重視的問題,也就是要關注多元語言文化意識的培養問題。
一
我在法國上大學的時候,先主修的是哲學,然后,所謂的偶然性使我走上了漢語之路。因為快上哲學系二年級的時候,巴黎來了一場高等教育改革,以我們學校為試點。這場改革的核心內容在于今后學生要主修兩個專業,這是20世紀70年代初的事了。我就自然而然地提出外語行不行。所以我剛才說偶然性是不存在的,偶然中有必然,本人的個人特征使我想到外語的選擇。我當時自發地問外語,對方說沒問題,外語也行,經濟學也行,社會學也行。我除了哲學,想主修的另一個專業是外語。我就自然而然地去西班牙語系,注冊好了以后開始上課,在西班牙語系上了2~3個星期的課,放棄了。放棄學西班牙語后,我換成了中文專業。具體情況是,我發現經常路過一個系,這個系秘書處門上有三個漢字,我當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好奇,所以我在放棄西班牙語后馬上去中文系。我本來不知道這三個字就是“中文系”,幸好上面有法語,所以我就敲門說我想學一點點漢語行不行,作為我的第二個專業。他們說沒問題,因為剛上一年級的有6名學生,加上我就7個,問題不大。到中文系之后,沒想到我很快就入迷了。
我當時學習的這門語言你們應該意識到——像我習慣說的——就跟月球語言一樣。所謂的月球語言,也就是說距離遙遠的語言。有近距型語言,有遠距型語言。對法文母語者而言,近距型語言有: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這叫做羅曼語系。遠距的有: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日語、漢語。漢語在詞匯、語法、文字、文化這些方面都是遠距離的。我當時不知道的是,正因為是遠距型語言,所以我愿意去學。我當時也沒有太明確的意識,沒有完全意識到我放棄西班牙語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它是近距型語言,可能我同時主修哲學,因為哲學是教我們跟任何現象保持距離的,包括漢語。進了中文系,漢語我們每天都離不開,就是增加要認識的字,接觸現代漢語、古文、中國古代思想、中國現代歷史、文學等等。所以在立場上是很難跟這么大這么豐富的學問保持距離的,但是可能因為修的是哲學,我從那個年代到現在還是基本上能保持距離,既參與,又觀察。所以我也經常傾向于綜合概括。
西方文明、歐洲文明,是邏各斯型文明,我當時也沒有意識到。可是我越來越清楚的是,我當時走上的漢學之路,使我意識到中國文明在進程上是一種視覺型文明,正好中西兩種文明有一點互補。以具體的例子來說,古希臘尤其是古羅馬,把口才放在非常高的位置,口才當時接近于一門藝術,被視為一個人非常突出的優點,所以口才藝術傳統在西方文化的地位是相當高的。第二,我作為修過哲學的,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作為西方哲學很重要的一點——主客關系。主客相對的分隔,有差距,又重邏輯分析,這個重邏輯分析,還有重邏輯連接,跟古希臘語、古拉丁語還有我本人母語法語的凸顯特征,我覺得是分不開的。我從事漢學研究多年以后,有一天,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感到中國文化史上沒有相當于口才藝術的——我發現中國那么豐富的文化,口才好像是比較淡化的,甚至可能沒有,而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口才藝術和演說藝術是首要藝術之一。我認為應該意識到的是所謂的書法——更確切地說,書道是西方文明所沒有的一門藝術。希臘字母或拉丁字母,有時候偶爾能見到一些美觀的效果,可是把字母加上一些美觀的修飾,這說不上是藝術,而書法在絕對嚴格意義上是西方所沒有的一門藝術。我最后得到的一個初步的結論就是,書法是中國的“筆才”,相當于“口才”。一方有口才,一方是筆才。我們沒有筆才,有口才。中國可能沒有口才,作為一個傳統,作為接近于藝術的,有筆才,就是書法。另外,主客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尤其是古代思想形成一種主客交融,包括從美學的角度可能意識到天人合一,重感悟、重并列。重并列是從我們的視角來講的,是漢語的重大特征之一。
二
我接著講語言和文化這種特殊而微妙的關系。請大家思考一下這兩位:一位是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一位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第一位說語言是人類上演的最精彩的節目:“Speech is the best show the man puts on.”第二位說:“語言是存在之家。”如果概括起來,什么意義呢?語言是存在之家,那毫無疑問其中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語言不只是工具而已,是家,這是說的第一點;上面的沃爾夫(Whorf)的那句話,也是說語言不光是工具,而是相當于一種表演,像一出戲那樣。一出戲的內容,包括它的表演形式,包括它的布景,我們知道是相當豐富的,是一種表達形式,也是帶有文化色彩的一種表達形式。這兩句名言提醒我們語言不只是工具。而如果把語言當成工具,我經常說我們會使用一個統一的語言就是“世界語”。“世界語”失敗的主因在于它的起點錯了,認為語言就是一個工具而已,只要能造出一個好使的工具,那么大家都會使用。結果呢,我們都知道。
我以前很感興趣的一個美國學者的研究,有一個結論:任何特定的母語訓練及使用者在講述事件和經驗時,以特定的注意方式去觀察事件。這說明語言不只是工具,而且認為語言影響著思維,語言影響著我們觀察周圍、分析周圍。我再加兩點:第一,不僅語言,文字可能也影響著思維;第二,剛才說的那個結論,不是Slobin第一個提出來的,在他之前,20世紀中葉,由一位美國語言學家提出來,可是受到語言學界的批判,Slobin是以實證,通過一個實驗,證明了語言對思維,對觀察、實踐是有影響的,這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一個實驗。簡單地說,他基于一定的語言學理論,讓幾十個英語母語六歲的孩子,看一個圖畫故事,讓這些孩子講述這個故事,接著讓幾十個英語母語的孩子重新講述這個故事,然后,他讓幾十個西班牙語六歲的孩子看同一個圖畫故事,這個圖畫故事現在很有名,因為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方法論,叫做“Frog, where are you?”(青蛙,你在哪里?)。他讓這些西班牙語六歲的孩子一樣講述這個故事,然后讓漢語母語、法語母語、日語母語等等六歲的孩子,重復同樣的實驗。結果就我所知,應該說第一次能初步地得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語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塑造思維方式的。
以Dan Slobin和Leonard Talmy 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為依據,以這種實驗為基礎得出的結論,其中一個是說無論是哪個語系的語言,有的語言是衛星框架語,有的語言是動詞框架語。漢語屬于第一類,英語也屬于第一類,本人母語屬于第二類。難怪我在接觸了解這個研究之前,已經意識到而且提出,英語學習者在學習漢語的時候占便宜。對他們來講,以文字為標準,漢語當然絕對是遠距離語言,跟我們一樣;詞匯跟我們一樣,是遠距離語言。可是我早就意識到在語法上,英語和漢語比較相似,尤其是在表達動作、移動方面,顯然跟漢語差不多,甚至是一模一樣的。而法語這方面跟英語的差距是很大的,跟漢語在這方面的差距也是很大的,所以法語學習者學習漢語的距離要比英語學習者的長。舉例來說,漢語的趨向補語跟英語的“postposition”(后置詞),就是動詞后的表達方向和移動的成分很相似,而法語這方面是更加中立、更加抽象的,不太照顧空間,不太照顧方向和移動。法語的表達方式,比如說“拿”,沒有“拿來”“拿起來”“拿過來”;有“進”有“出”,沒有“進來”“進去”“出來”“出去”,更沒有“走過來”“爬上去”等等,所以我們學習漢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困難,不在于理解“跑出來”,理解問題不大,可是在自然會話中,輸出一個“跑出來”,這是難度太高甚至恐怖的。為什么?因為思維的不同。
現在講第二點,雖然都是語言和文化,你們會發現我會越來越具體,會發現跟我今天的主題是什么關系。一位20世紀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了這么一句名言:“我的語言所及之界便是我的眼界所達之境。”他又提出了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大家可能有所領會,這可能是正統語言學家會持保留態度,至少可以說會有所保留的一種觀點,難怪這又是一位哲學家提出來的。
法國漢學泰斗之一謝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現在近90歲,曾寫過一部專著講中國與基督教的傳播,或者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這位先生是個大家,精通漢語古文、書面語,所以他第一次去研究的主題不是傳教士怎樣看待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這有的是,而是相反,他去找第一手資料,就是中國當時的資料,讓大家了解中國人當時是怎樣看待傳教士的,這是極少見的一個研究視角。謝和耐先生在這部書的最后幾頁提出的觀點,說實話是我剛剛開始教中文的時候,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非常關注的幾句話。他敢于說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系,而且對正統的觀點有所保留。他提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沖突,歸結到底根本差異不僅在于不同知識傳統的差異,而且更是不同思維方式和不同觀念類型的差異,其中突出了漢語本身在接受基督教的某些概念時會產生的障礙。
我們現在離開基督教,去看看北歐。我的兒子是學醫的,他在四年級時主動申請歐洲學生交流項目,去另一個國家讀半年或者一年的專業課,法國認可學分。他決定去芬蘭讀他的醫學四年級,在那邊是英文授課,芬蘭語對我們來講是遠距離語言,因為跟我們歐洲語言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只跟匈牙利語有一點關系。他走的時候,我讓他完成一個任務:“你去找一些芬蘭教授,給我列芬蘭語中指雪的一個簡單的名單。”他沒有多久給我發郵件,我舉幾個例子:“雪”這個詞比較中性的說法是“lumi”。還有“融化的雪”,你們看中文必須得加一個“融化”,法文要加一個“fondue”相當于“融化”來形容,可是芬蘭語就一個詞“r?nt?”,而這個詞跟剛才提到的第一個詞沒有任何關系,詞根也不一樣。“鮮雪”,剛下的雪,叫“viti”,“viti”跟第一個詞連詞根也沒有任何關系。還有“hyyhm?”,“可融化的雪”,法文會翻譯成“neige fondante”,我們得加一個詞,才相當于“可融化的雪”,跟剛才說的已經融化的雪不一樣,跟第三個不一樣,表達的意思不一樣,而且第三個詞和最后一個詞的詞根、詞綴也沒有任何關系。芬蘭語在這方面非常豐富。其中一個問題當然是詞匯量,這方面的詞匯比較豐富,而漢語、法語基本上就一個。問題在于,這對我們觀察周圍的事物,包括思想、思維是不是有一點影響?我們分析周圍環境的信息是不是會導致一些不一樣的結論?我們是不是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芬蘭人在看“鮮雪”和在看“已經融化的雪”的時候,他到底是在看同一個東西,還是不同的東西?這樣的例子我們還知道很多。由此我們可以提出這個假設:語言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都與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也不只是自然環境,還有意識形態環境、文化環境、一個特定民族的社會密不可分。
我還是強調語言不只是工具,通用的工具。再舉幾個例子:“fleuve”和“rivière”這兩個詞,其中第一個指的是“入海的江河”,第二個是“入fleuve的江河”,法文明確區分。這不是專業用語,這不是書面語、文學語言,這是最普通的說法,明確區分。一個法語母語者一看到一條河,他會說這是“fleuve”,是入海的,像塞納河,盧瓦河等等;也許看到另一條河,他會明確說這是“rivière”。據我所知,相當多的語言,甚至大部分語言沒有這種區分。第三個例子,“galant”是一個法語形容詞,它指的是什么?一般指的是男性,一個男人如果說很“galant”,意思是說他對女性特別禮貌,不是對一般人禮貌,這個形容詞指的是男性對女性的禮貌行為。有意思的是,這個詞法文很早就有,來自于中世紀的一些民間詩人的傳統,后來產生了這么一個詞,它當然也是多義的,可是最流行的意思,是我剛才說的那一個。沒有發現其他語言有這樣的詞,這個跟“gentleman”不是一個意思。
現在我們談一談漢語方面的“calligraphy”,英語“calligraphy”就是書法。因為西方沒有這門藝術,所以我們用詞方面有一些講究。瑞士日內瓦大學中文系有一位漢學家寫過一本書,據我所知是第一部從美學的角度介紹分析書法的著作,很遺憾,到現在沒有翻譯成法文。據我所知,可能真正從美學的角度介紹研究中國書法的,就這么一部。那位先生的中文名字叫畢來德(Billeter),他的母語是法語,我認識那位先生。他的書名沒有采用“calligraphy”,因為他說會產生誤解,他翻譯為“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為什么這么長呢?因為他意識到“calligraphy”,法文“calligraphie”,其實包括阿拉伯字母的那種美觀效果也用“calligraphy”,有時候拉丁字母偶爾加一些美觀的修飾,那就是“calligraphie”。他認為中文不一樣,不是一個層面,中文書法是一門真正的藝術,這是大家應該公認的。所以他在用詞方面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他的那本書書名翻譯成中文的話,應該是“中國書寫藝術”,反正要突出藝術這個意思。
還有我們在對外漢語方面經常接觸的“形容詞”一詞,最早借用西文、法文來造個語法術語,其實不是直譯的,現在用的形容詞,不是法語術語的對應詞。法語所說的類似于“形容附詞”,所以這就反映了語言之間有時候也不能百分之百地反映一個意思。包括中文所說的“語文”,我覺得這個詞很妙。語文,顧名思義既包括語言,也包括文字。我們翻譯“語文”這個詞翻譯不出來。為什么翻譯不出來?因為西文的文字只是為語言服務,只是記錄語言而已。中文,能不能說漢字只是記錄漢語而已呢?我覺得不能只是說是記錄。漢字當然是記錄漢語的。可是剛才提到的書法呢?書法也是文字的一部分,不能簡單地說只是記錄語言,所以難怪“語文”這個詞在中文里很重要。
三
下面我要講的是,我這三年來主要在法國,也有在意大利羅馬進行的培訓,培訓近70個當地的漢語老師,相當部分是漢語母語者。我在中國也培訓了一些國外教育機構的對外漢語的老師,都是漢語母語者,培訓的內容是“中國文化教學”。我為什么三年以前就認為在培訓方面這是個很重要的話題呢?因為我在法國一年當中能聽上百個課,在中等教育,因為法國漢語教學在中等教育作為一個正規科目,規模是最大的,所以在法國各地的初中、高中,我一年當中可能聽上百次的課。我分析、觀察、總結,發現在文化傳播中存在一些比較大的,甚至比較嚴重的問題。在哪些方面呢?在效果、方法上,我發現這些漢語母語者老師有規律性的特征,當然說的是那些需要糾正的。他們大部分是非常投入的,包括優秀的老師,可是在文化教學方面,有太大的障礙——我說的太大的障礙不是知識的不足,他們的知識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一個是中國文化教學偏向于實用層面,動手做的傾向比較突出,也就是說讓外國學習者動手制作或者親身體驗,好像是一種自然的傾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一個話題——“吃文化”,中國飲食文化。中國飲食文化在法國學界,不光是中國的,飲食文化在法國學界早已被列入學術范圍,沒有人對此有疑義,有這方面的專家。有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我的一個同學,跟我一樣,20世紀70年代在北京留學,后來回國后就走上漢學之路。他也當上了博士生導師,可是他的專業不是現代漢語教學,不是漢語語言學,不是中國佛學、中醫、文學,也不是古文,他是中國食文化博士生導師。我也知道有其他的專家學者,他們是研究食文化,但不一定是中國的。在這種背景下,漢語母語老師明顯有一個傾向,在講食文化或者在回答學生有關中國食文化的問題時,大部分的情況是講了幾句之后,說:“好,我們約一個時間,大家一起包餃子。”這就是我說的動手做的傾向。我剛才說的是初中、高中,可是成年人也不例外,成年人我有這方面的體會。法國人特別愿意聽中國文化,無論道家也好,中醫也好,還是中國電影也好,也很愿意聽關于中國食文化的知識。可是如果跟大家說,今天就包餃子吧,我估計相當一部分人說不定就會走了。因為對西方人來講,這是兩回事,動手是有親身體驗的,跟了解一種文化、接觸這些知識是兩回事。我可能對第一個感興趣,對第二個不感興趣,或者相反。
還有一個自我中心論的傾向,下面還是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什么叫文化?在傳播或是教學中,無論傳播還是教學,我覺得應該明確區分幾個層面:一是詞語文化,也就是說詞里面所涵蓋、藏著的一些文化。二是文字文化,我說的文字文化當然主要是漢字方面的文化。可是不只要明確區分這幾個層面,如果在傳播的過程中就限制在詞語文化,肯定會產生很大的不足,或者限制在漢字文化,肯定也會產生很大的不足。三是習俗文化,比如說傳統節日、謝謝文化,中國人在哪種條件下說謝謝等等。我發現相當一部分的老師有時候限制在這種習俗文化,就是講謝謝,當然很有意思,西方人也很愿意聽,可是我覺得問題在于只是局限于這種情況,或者局限于動手做的那種文化,會產生比較負面的結果。還有公益活動,在國外的中國文化傳播,說不定公益活動是主要的傳播方式,至少在法國我敢肯定。今天我們要思考的是,中國文化傳播,為什么自然而然地走向這種動手做、公益活動或者剪紙或者包餃子或者編中國結等方式呢?其他內容和方式呢?我下面要說的是,這種傳播方式,使得知識文化邊緣化了,文化點邊緣化了,文化話題邊緣化了。
我現在說一點可能是大家期待的,因為剛才說過會越來越具體。以下實例來自法國、意大利,其實我剛才講的,包括我在培訓期間發現的,也包括做調查的結果。
(1)孔子。這當然不是全部的調查內容,我挑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絕對是有代表性的,其實有普遍性,是有普遍規律的東西。對于孔子,我在培訓期間,無論在法國各地,或者在羅馬,還是前年在中國蘇州,我的指令是什么,這是很重要的。我說孔子作為一個文化點,請大家概括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三大特征,“特”的意思是指所特有的。請允許我簡單地評論一下,93%的說孔子第一是什么什么,當然要有一些形容詞,重要的、偉大的什么教育家。這已經出問題了,可能在場的我估計不一定能意識到問題在哪,這也是我今天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教育家翻譯成法文,或者英文,第一會產生誤解,第二是這些絕大多數的漢語母語老師,他們不知道西方、歐洲,我當然最敢肯定的是法國的情況,無論是在哪個國家,不一定是學術界,包括普通民眾,大家都知道孔子,幾乎從來不提孔子是教育家。我現在的意思不是說這方對,那方錯,我覺得在傳播方面,其中一個起點是不是先得了解對方對我要傳播的內容的認識?這個在認識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孔子在西方一般被視為思想家,如果要突出概括孔子的身份,“思想家”甚至可以查到說是“哲學家”。我調查的是上千個漢語母語老師,絕大多數——90%以上的說“教育家”,至少可以說視角不同。可是我覺得不光是視角的問題,到底孔子是思想家還是教育家?《論語》重教育是不成問題的,當然重教育,有一種教育觀,可是重教育、有教育觀,也不一定是教育家。說他是教育家,也就是說在傳播的過程中最后對孔子的認識是教育家,翻譯成西文更會產生誤解。還有一種回答是“第一個老師”。這當然和教育家不是沒有關系的,那就是說一個學生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如果要回憶孔子,或者如果要跟別人講孔子,他說我記得是一個老師。這可能是同樣的問題。回到前面,你們記得我的指令是概括綜合特征。有的說一個特征是“仁、義、禮、智、信”。我認為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一種特別的傾向,是走向細節。在一定程度上,“仁、義、禮”已經是細節了,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下面談“古代”,對孔子的第二大特征的概括是“古代”,這顯然不能接受,因為“古代”不是孔子所特有的一個特征。“智慧”也不是。
(2)“中國”。中國是最具一般性的文化點,任何一個人在國外傳播中國文化,就必須簡單地介紹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點。中國,我沒說中國地圖,我沒說中國地理,我沒說中國歷史,就說中國,要簡單概括綜合中國。我個人覺得問題比較大,比如說多民族國家。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就不對,問題在于,如果在法國說中國的主要特征是多民族國家,可是法國也是多民族國家,大部分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并不是只有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這個概括可能傳播的效果是有問題的。請注意我的指令是要概括三大特征,也就是要讓學生或者對方記住最重要的東西。如果你記住的其實是比較一般性的特征,那么傳播的效果會怎么樣呢?這反映了沒有換位思考問題,如果換位思考問題,先要了解我現在是在法國做這方面的傳播,或這方面的教學,法國是單一民族嗎?不是,是多民族,我就不能先突出“多民族”這個特征。再比如有人概括中國的特征是:南北差異、歷史悠久。那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其他國家南北共性多,歷史可能不悠久。我比較熟悉的歐洲國家南北差異非常大的也不少,法國的南北差異就非常大,不只有一點點差異,包括食文化不一樣,口音不一樣,氣候不一樣,人也不一樣,所以把南北差異作為中國所特有的,顯然是不合適的,先要換位思考。“歷史悠久”可能也是一個問題。還有這樣的回答:歷史地理文化。這種回答不少,其實可能只是傳播者的一個提綱,而不是對中國特征的概括。
(3)“中國食文化”。我們先評論第一個。有這樣的回答:第一大特征是“八大菜系”,第二大特征是“蒸煮炒炸煎”。剛才記得嗎?關于孔子,也是走向了一些比較具體的概括。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些現象是不是具有規律性的,而且這些規律性的東西是不是跟一種思維方式,或者教育傳統,或者語言文字有一點關系呢?我先評論“八大菜系”。在第一次傳播時,講中國飲食文化,是不是要突出菜系?我覺得毫無疑問應該突出,問題在于怎么說。因為傳播很重要的是方式,而我對“八大菜系”一說有比較大的保留意見。我當然同樣也會突出中國食文化的多樣性,也許我的選擇是有極大的多樣性,這個我敢肯定,因為和其他絕大部分民族的食文化相比,這是中國所特有的,所以我會突出。但是“八大菜系”有個問題,我們在傳播方面,第一次傳播要經濟,我覺得“八大菜系”不如“四大菜系”經濟,因為有“四大菜系”一說,“八大菜系”一說,也有“十二大菜系”一說,如果先讓大家接觸中國食文化,毫無疑問要先以最經濟的方式說“四大菜系”。為什么?換位思考。傳播的主要任務是要讓人接受這些知識,看半年以后,一年以后能否記得,效果是最重要的。一般人半年以后能記得這“八大菜系”的名字和特征嗎?可能還不如先教“四大菜系”:魯菜、淮揚菜、川菜、粵菜,這都知道。還有人概括的是:菜系。這個我贊同,可是說法不太合適。然后,又有人概括為“舌尖上的中國”,顯然不符合我最早的指令。還有一些說法,同樣具有那種規律性,就是我剛才說的,走向細節而沒有綜合概括。最后一種說法是“烹飪方法”,可是沒有形容什么樣的烹飪方法。我們知道,全世界各民族的食文化都有烹飪方法,要說出它的特征。炒面、餃子、米飯,典型的,非常典型的。所以我有責任跟各位分享有規律性的特征:炒面、餃子、米飯。
(4)“中文”。可能除了“中國”這個文化點以外,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文化點,是要傳播的。有人概括說“詞匯豐富”,這顯然是自我中心的。為什么?這就意味著法語、英語、意大利語詞匯貧乏,只能產生這種效果。還有“形聲義結合、漢字美、文化內涵”。我會理解為其他語言沒有文化內涵,“漢字美”我覺得是可取的,可是書法是否最合適?我們當然可以討論。“形聲義結合”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作為第一個突出特征,可能有些專業了。還有人說是“拼音”,我沒有問到底是什么意思,這至少在傳播方式上有問題。說“漢字”,也沒突出形容漢字是什么,當然大體上是可取的。還有“語義結合、聲調、SOV”,這些當然語言學界都知道,可是在大眾傳播方面是有問題的。
四
我在自我介紹的時候說我是漢語學習者,當然是漢化程度不低的一個學習者,可是畢竟像我習慣說的:“我不是廬山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最早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廬山,也不知道有這么一個中國文化,慢慢地走上漢語言文化之路,越來越清楚。我從遠處看到了中國文化的一些特征,可是我畢竟開始的時候“不是廬山人”,所以跟大家分享的視角是本人的視角。
比如“孔子”。如果問我,作為一個傳播者,我怎么介紹孔子?我當然要謹慎,因為要盡可能回避剛才所提到的一些問題。我的第一個選擇,你們已經意識到,我不會說孔子是一個老師。我會這么說:孔子是中國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思想家。我毫無疑問傾向于說思想家。我加一個細節,年代,為什么?因為遠距離文化的人不一定知道孔子,孔子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不一定知道,知道是古代,是公元前,還是公元后?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加一個。最后對比,我發現調查中一個很大的不足,就是缺乏這種對比視角,所以我加了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當然跟孔子不一樣,可是大體上年代差不多,還有影響也差不多,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這樣能保證傳播效果。第二,我所調查的上千個漢語母語老師,可能只有幾個,不超過五個想到了,就是要概括。說孔子是思想家,可是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沒有采用什么仁、禮、智,我用的是“非宗教的人文主義道德”。你們會覺得有點長,為什么那么繁瑣呢?我第一要突出的是道德,你們看,這跟我的第一個選擇“思想家”合乎邏輯,跟教育、教學、所謂的老師沒有太大的關系。突出道德,因為他主要是講道德的,問題在于我為什么加了一個人文主義,或者按中國的說法以人為本呢?為什么又加了一個“非宗教的”?因為我也要換位思考,作為一個傳播者,我要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對方是西方人,他們把道德和什么結合在一起呢?無論信還是不信宗教,一個西方人一聽到道德,顯然就跟《舊約》《新約》結合在一起。我說包括不信的,大部分人可能是不信的,可是會聯想到西方道德的基石就是《圣經》,《圣經》跟宗教有關,所以,為了避免誤解,我會加一個“以人為本的”,不是以上帝為主,或者不是宗教的,是“非宗教的”,我考慮了對方。然后形象方面采用什么呢?我沒有采用圖片,而是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話,因為學習者聽我關于孔子的演講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他們至少要知道一些關于孔子比較具體的內容,我選擇的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等等。我對這個選擇比較滿意,為什么?因為講的是人。提醒你們,公元前的大思想家講的是人,講的不是上帝,講的不是其他什么。從我讀中文系的時候,一直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敬而遠之”的說法,這可能是從普通西方人的角度。為什么?因為西方背景下,應該是“敬而近之”,因為我們要敬誰?我們要敬上帝,上帝不能遠之啊,應該每天從早到晚做禮拜,去教堂等等。第三,我調查的上千個教師沒有一個想到,有的走近了,可是不很明確。有的說影響很大,可是沒說得太具體。這個跟孔子就是儒家觀念有直接關系。所以我的第三個選擇是要突出漢化圈,說儒家思想是重要的價值基石。有一年我有幸第一次去訪問韓國,韓國各方面顯然深受儒家觀念的影響,我覺得傳播孔子,這一點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說對孔子,當然要關注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反響怎么樣?直到現在,他的影響不只是在中國,而是超越了中國,影響日本、韓國等等。
關于“京劇”,要概括綜合出三大最需要知道的東西,這種實驗很有意思。我的一個選擇,上千個教師中沒有一個想到。當然不是說我一定對,請大家判斷。對我來說,是一定要加進去的三大特征之一。“京劇”概括起來,第一,我覺得要突出它的綜合性,是一門綜合藝術,法文所說的“un art total”。這不是我說的,這是名戲劇家布雷希特 (Brecht) 20世紀初在評論“京劇”時說的。對西方人來講,“京劇”是綜合藝術。法國有沒有戲劇?當然有,古典的、現代的、當代的都有。可是我對“京劇”很好奇,好奇的主因可能是因為它好像是由不同的藝術合起來形成的一種藝術,包括武術等等。第二,程式化。請大家注意,怎樣傳播,用詞很重要,我沒有說有以下這幾個角色,然后列出什么花旦,什么丑。不,我就說程式化,下面當然要舉例子,不過是以比較高的視角去概括綜合。我發現大部分的漢語背景的老師沒有做到,他們把例子放在前面。第三,我覺得不可缺少的一個很大的特征,是該文化點所特有的,京劇所特有的。從哪個視角?當然是從對方的視角,從西方人的視角,從接受傳播的視角,就是“音樂”。京劇不是有音樂嗎?音樂的功能基本上為舞臺服務。大家看過京劇,什么《孫悟空》,什么《三岔口》,作曲家是誰,不知道。《卡門》是西方歌劇,法國古典歌劇,作曲家大家都知道,Bizet(比才)。法國歌劇《卡門》我經常聽,開車聽,有時候家里也聽,不是看,是聽,聽什么?聽音樂。西方歌劇音樂不是為舞臺服務的。京劇樂隊在哪里?好像有幾個演奏者,一般不超過十個,就在舞臺的右手邊。西方歌劇的樂隊在哪兒?就在中心位置,還有什么?有指揮。京劇沒有指揮,等等,都是高等藝術。中國戲劇傳統非常豐富,具有很大的獨特性。法國漢學家中,有的是專門研究中國戲曲的,有相關的書。西方有它的傳統古典歌劇,所以這肯定應該對比,因為一提到“opera”,英文法文一樣,“opera”使我們聯想到西方歌劇,所以更需要換位思考,要突出音樂的地位、功能,完全對立。任何一個西方歌劇,首先要提出的是作曲家是誰,作品就是音樂本身,而《三岔口》的作曲家是誰,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一定程度上,這么一個對立的情況,反映了中國是視覺文化,而西方是聽覺文化。
Several Issu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akingtheInternationalDiffusionof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asanExample
Jo?lBellassen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Paris,France)
The cross-cultural diffusion of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contact of languages,but also the contact of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 and cultur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arious cultures,together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tradition and thinking modes,usually leads to misunderstanding,so far as to conflict. Therefore,in order to obtain good effect of communication,we should know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different thinking modes,pay attention to transpositional consideration,cultivate multi-language and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Diffusion of Language;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Language Distance;Transpositional Consideration
10.19468/j.cnki.2096-1987.2017.02.005
白樂桑(Jo?l Bellassen),法國國民教育部原漢語總督學,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歐洲漢語教學協會主席,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法國漢語教師協會名譽會長,主要研究漢語教學和現代漢語語法。
*本文據白樂桑(Jo?l Bellassen)201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珞珈講壇上的講演錄音整理而成,并經作者審訂。